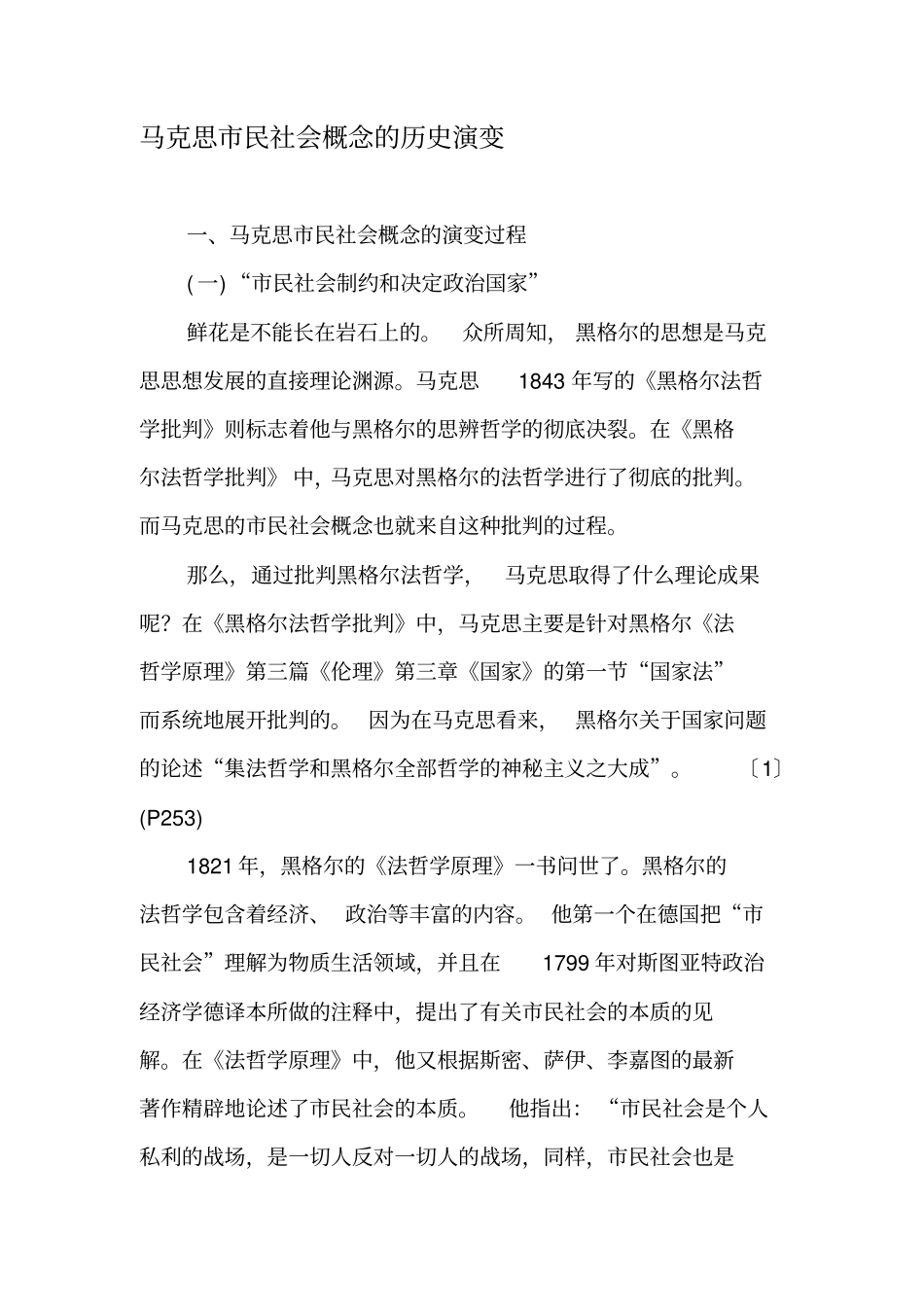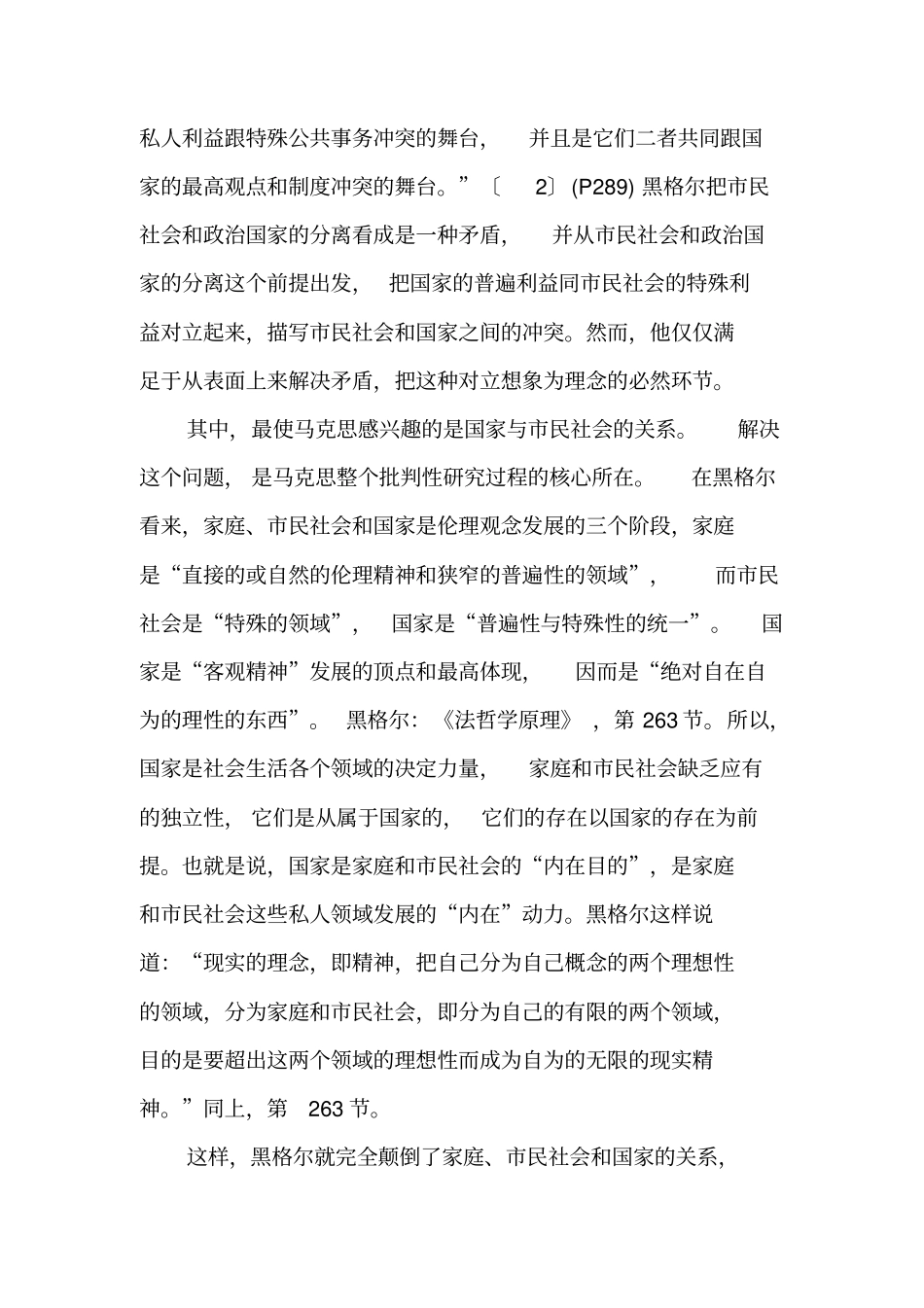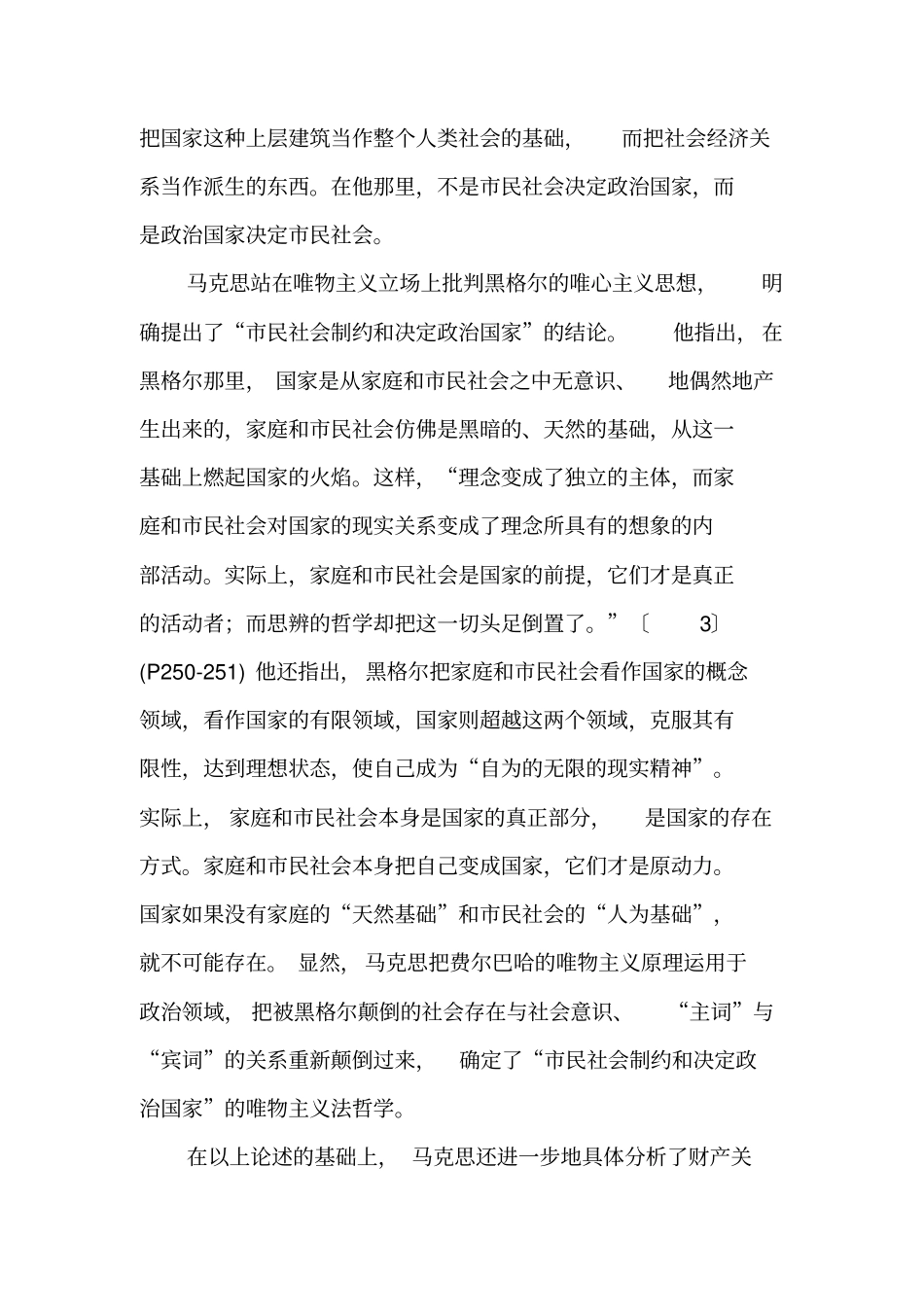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演变过程( 一)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鲜花是不能长在岩石上的。众所周知, 黑格尔的思想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直接理论渊源。马克思1843 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则标志着他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彻底决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也就来自这种批判的过程。那么,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取得了什么理论成果呢?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主要是针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三篇《伦理》第三章《国家》的第一节“国家法”而系统地展开批判的。 因为在马克思看来, 黑格尔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集法哲学和黑格尔全部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1〕(P253) 1821 年,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问世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包含着经济、 政治等丰富的内容。 他第一个在德国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物质生活领域,并且在1799 年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德译本所做的注释中,提出了有关市民社会的本质的见解。在《法哲学原理》中,他又根据斯密、萨伊、李嘉图的最新著作精辟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他指出: “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2〕(P289)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看成是一种矛盾,并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这个前提出发, 把国家的普遍利益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对立起来,描写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然而,他仅仅满足于从表面上来解决矛盾,把这种对立想象为理念的必然环节。其中,最使马克思感兴趣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解决这个问题, 是马克思整个批判性研究过程的核心所在。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和狭窄的普遍性的领域”,而市民社会是“特殊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国家是“客观精神”发展的顶点和最高体现,因而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 ,第 263 节。所以,国家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决定力量,家庭和市民社会缺乏应有的独立性, 它们是从属于国家的,它们的存在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是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些私人领域发展的“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