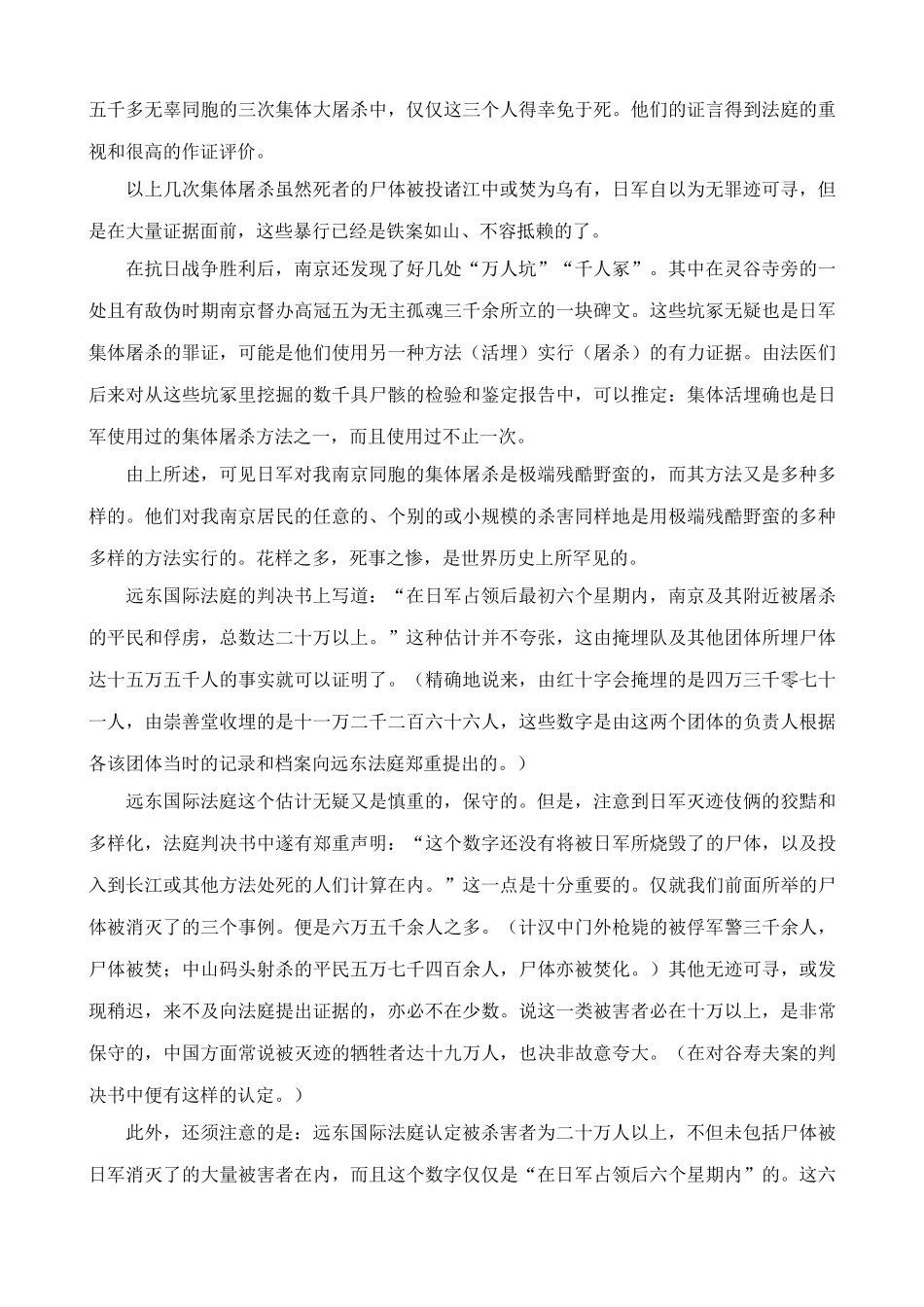“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备课资料蒋介石序山谈话第三,万一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中,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宗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域,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惟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传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四、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课时)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说:“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道理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一个人一动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一万二千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的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12月15日(即占领的第三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三千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16日(即占领的第四天),縻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亦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企图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仅白增英、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梁廷芳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