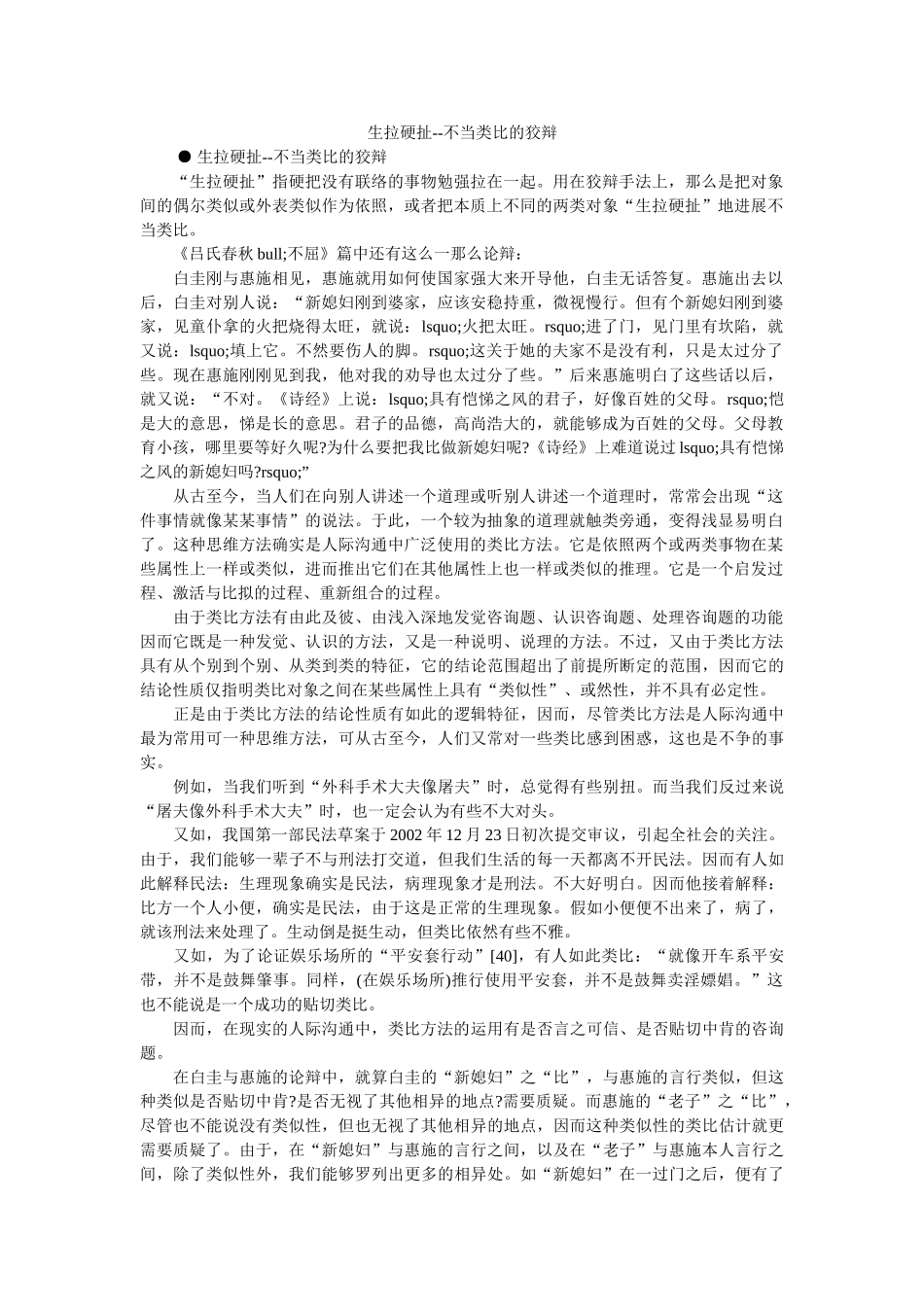生拉硬扯--不当类比的狡辩●生拉硬扯--不当类比的狡辩“生拉硬扯”指硬把没有联络的事物勉强拉在一起。用在狡辩手法上,那么是把对象间的偶尔类似或外表类似作为依照,或者把本质上不同的两类对象“生拉硬扯”地进展不当类比。《吕氏春秋bull;不屈》篇中还有这么一那么论辩:白圭刚与惠施相见,惠施就用如何使国家强大来开导他,白圭无话答复。惠施出去以后,白圭对别人说:“新媳妇刚到婆家,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但有个新媳妇刚到婆家,见童仆拿的火把烧得太旺,就说:lsquo;火把太旺。rsquo;进了门,见门里有坎陷,就又说:lsquo;填上它。不然要伤人的脚。rsquo;这关于她的夫家不是没有利,只是太过分了些。现在惠施刚刚见到我,他对我的劝导也太过分了些。”后来惠施明白了这些话以后,就又说:“不对。《诗经》上说:lsquo;具有恺悌之风的君子,好像百姓的父母。rsquo;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浩大的,就能够成为百姓的父母。父母教育小孩,哪里要等好久呢?为什么要把我比做新媳妇呢?《诗经》上难道说过lsquo;具有恺悌之风的新媳妇吗?rsquo;”从古至今,当人们在向别人讲述一个道理或听别人讲述一个道理时,常常会出现“这件事情就像某某事情”的说法。于此,一个较为抽象的道理就触类旁通,变得浅显易明白了。这种思维方法确实是人际沟通中广泛使用的类比方法。它是依照两个或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一样或类似,进而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一样或类似的推理。它是一个启发过程、激活与比拟的过程、重新组合的过程。由于类比方法有由此及彼、由浅入深地发觉咨询题、认识咨询题、处理咨询题的功能因而它既是一种发觉、认识的方法,又是一种说明、说理的方法。不过,又由于类比方法具有从个别到个别、从类到类的特征,它的结论范围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它的结论性质仅指明类比对象之间在某些属性上具有“类似性”、或然性,并不具有必定性。正是由于类比方法的结论性质有如此的逻辑特征,因而,尽管类比方法是人际沟通中最为常用可一种思维方法,可从古至今,人们又常对一些类比感到困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当我们听到“外科手术大夫像屠夫”时,总觉得有些别扭。而当我们反过来说“屠夫像外科手术大夫”时,也一定会认为有些不大对头。又如,我国第一部民法草案于2002年12月23日初次提交审议,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由于,我们能够一辈子不与刑法打交道,但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离不开民法。因而有人如此解释民法:生理现象确实是民法,病理现象才是刑法。不大好明白。因而他接着解释:比方一个人小便,确实是民法,由于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假如小便便不出来了,病了,就该刑法来处理了。生动倒是挺生动,但类比依然有些不雅。又如,为了论证娱乐场所的“平安套行动”[40],有人如此类比:“就像开车系平安带,并不是鼓舞肇事。同样,(在娱乐场所)推行使用平安套,并不是鼓舞卖淫嫖娼。”这也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贴切类比。因而,在现实的人际沟通中,类比方法的运用有是否言之可信、是否贴切中肯的咨询题。在白圭与惠施的论辩中,就算白圭的“新媳妇”之“比”,与惠施的言行类似,但这种类似是否贴切中肯?是否无视了其他相异的地点?需要质疑。而惠施的“老子”之“比”,尽管也不能说没有类似性,但也无视了其他相异的地点,因而这种类似性的类比估计就更需要质疑了。由于,在“新媳妇”与惠施的言行之间,以及在“老子”与惠施本人言行之间,除了类似性外,我们能够罗列出更多的相异处。如“新媳妇”在一过门之后,便有了居家过日子的责任了;而在古代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下,“老子”与“儿子”事实上存在着不平等。无视这些相异性,一味寻求类似性,就算类比成立也只能使谁也不愉快。因而,难怪后人评价白圭与惠施的论辩,是“用污秽责难污秽,用邪僻责难邪僻,这就使责难的人与被责难的人一样了”。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某种类似点。尽管类似性是类比的生命,但有了类似点却并不意味着两个事物之间就必定能够类比。类比的过程是一个整合多重信息源以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类比的逻辑依照只是“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