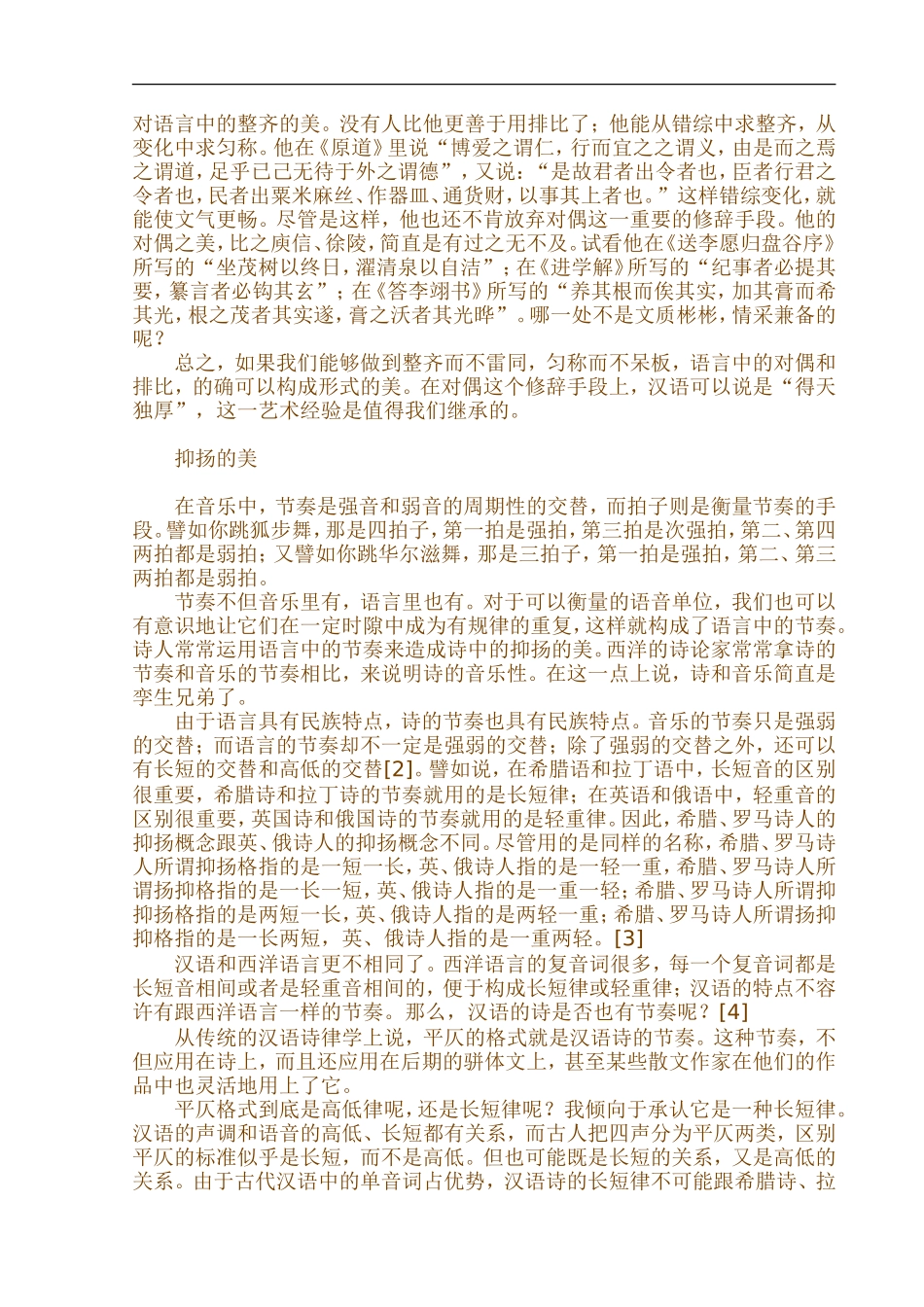略论语言形式美王力语言的形式之所以能是美的,因为它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回环的美。这些美都是音乐所具备的,所以语言的形式美也可以说是语言的音乐美。在音乐理论中,有所谓“音乐的语言”;在语言形式美的理论中,也应该有所谓“语言的音乐”。音乐和语言不是一回事,但是二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音乐和语言都是靠声音来表现的,声音和谐了就美,不和谐就不美。整齐、抑扬、回环,都是为了达到和谐的美。在这一点上,语言和音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语言形式的美不限于诗的语言;散文里同样可以有整齐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从前有人说,诗是从声律最优美的散文中洗炼出来的;也有人意识到,具有语言形式美的散文却又正是从诗脱胎出来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没有意义的;只要是语言,就可能有语言形式美存在,而诗不过是语言形式美的集中表现罢了。整齐的美在音乐上,两个乐句构成一个乐段。最整齐匀称的乐段是由长短相等的两个乐句配合而成的,当乐段成为平行结构的时候,两个乐句的旋律基本上相同,只是以不同的终止来结束。这样就形成了整齐的美。同样的道理应用在语言上,就形成了语言的对偶和排比。对偶是平行的、长短相等的两句话;排比则是平行的、但是长短不相等的两句话,或者是两句以上的、平行的、长短相等的或不相等的话。远在2世纪,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以善用排比的语句为人们所称道。直到现在,语言的排比仍然被认为是修辞学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排比作为修辞手段虽然是人类所共有的,对偶作为修辞手段却是汉语的特点所决定的[1]。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虽然双音词颇多,但是这些双音词大多数都是以古代单音词作为词素的,各个词素仍旧有它的独立性。这样就很适宜于构成音节数量相等的对偶。对偶在文艺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骈体文和诗歌中的偶句。骈偶的来源很古。《易·乾卦·文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左传》信公三十三年说:“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诗·召南·草虫》说:“喓喓草虫,趯趯阜螽。”,《邶风·柏舟》说:“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小雅·采薇》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例子可以举得很多。六朝的骈体文并不是突然产生的,也不是由谁规定的,而是历代文人的艺术经验的积累。秦汉以后,文章逐渐向骈俪的方向发展。例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说:“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又说:“节同时异,物是人非。”这是正向着骈体文过渡的一个证据。从骈散兼行到全部骈俪,就变成了正式的骈体文。对偶既然是艺术经验的积累,为什么骈体文又受韩愈等人排斥呢?骈体文自从变成一种文体以后,就成为一种僵化的形式,缺乏灵活性,从而损害了语言的自然。骈体文的致命伤还在于缺乏内容,言之无物。作者只知道堆砌陈词滥调,立论时既没有精辟的见解,抒情时也没有真实的感情。韩愈所反对的也只是这些,而不是对偶和排比。他在《答李翊书》里说“惟陈言之务去”,又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里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他并没有反对语言中的整齐的美。没有人比他更善于用排比了;他能从错综中求整齐,从变化中求匀称。他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样错综变化,就能使文气更畅。尽管是这样,他也还不肯放弃对偶这一重要的修辞手段。他的对偶之美,比之庾信、徐陵,简直是有过之无不及。试看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所写的“坐茂树以终日,濯清泉以自洁”;在《进学解》所写的“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在《答李翊书》所写的“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哪一处不是文质彬彬,情采兼备的呢?总之,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整齐而不雷同,匀称而不呆板,语言中的对偶和排比,的确可以构成形式的美。在对偶这个修辞手段上,汉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这一艺术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的。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