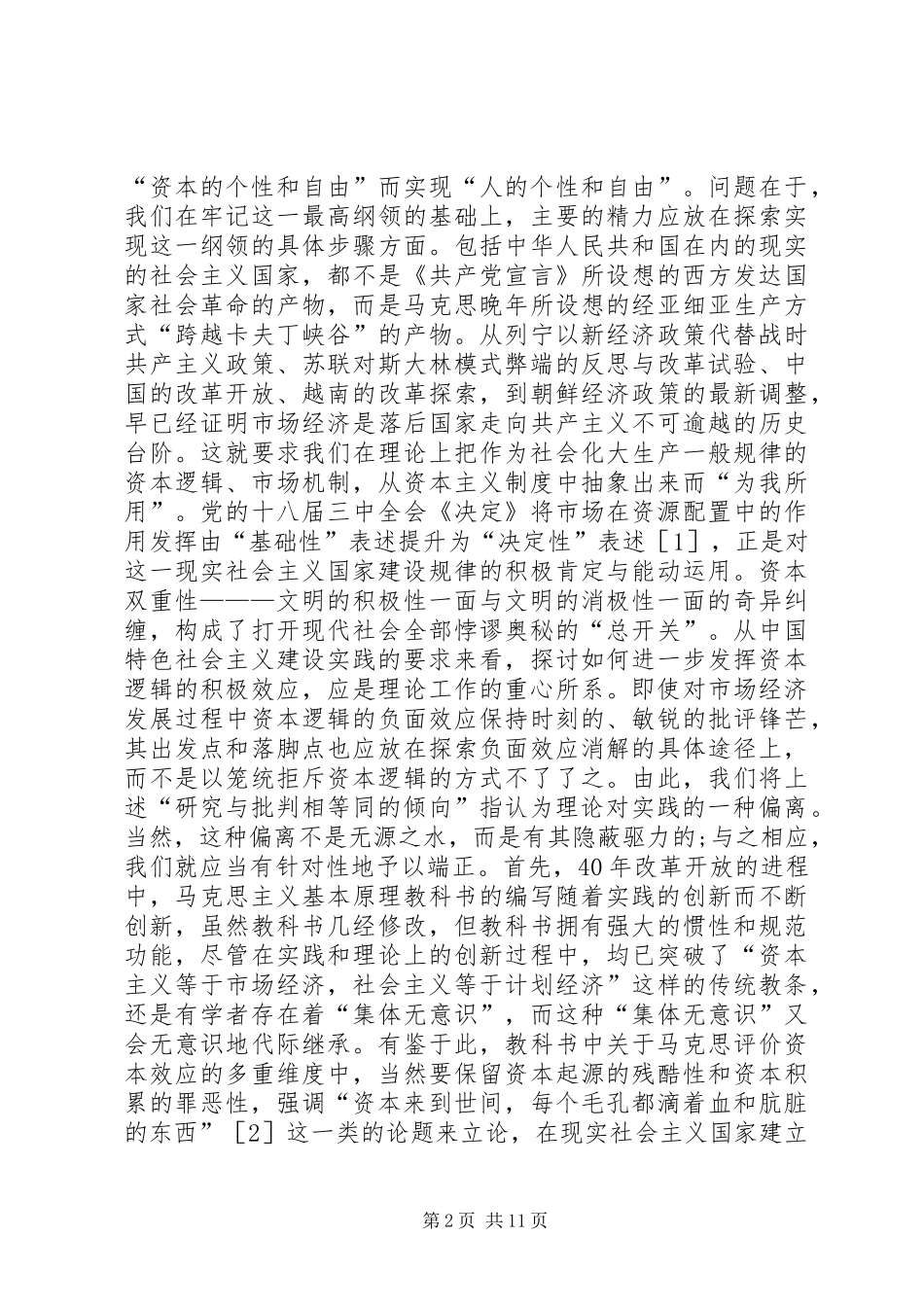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分析近年来,“资本逻辑”(capitallogic)成为我国学术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在充分肯定学界既有成果(立足其特定理论向度意义上的)学术价值的同时,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应予重新审视的倾向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其理论探索难以充分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要求。本文择取最为主要、与实践的关联最为密切的三种倾向进行批评性分析,以期更好地实现资本逻辑研究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对“资本逻辑研究等同于资本逻辑批判”倾向的审视第一种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即把“资本逻辑研究”完全等同于“资本逻辑批判”;尽管相关论者会原则性地提及资本在建构现代社会中的历史作用,但话语中心在于否定性地评判资本逻辑,在于把资本逻辑划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的“对立面”。例如,在资本对于物质资料生产的意义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以生产逻辑取代资本逻辑的终极目标,认为“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二律背反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对于精神文化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资本逻辑乃是造成虚无主义泛滥的罪魁,认为它“吞噬人的精神家园”。在资本对于科学技术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现代科技的使用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认为“资本逻辑是科技异化的根本原因”。在资本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工业文明对人类实践平衡的严重破坏,认为“资本逻辑的统治是‘高危时代’的根源”。在资本对于世界文明的影响研究方面,有学者重在强调资本具有分裂世界的“中心—边缘”机制,认为资本逻辑造成了“‘全球混沌’的无序状态等一系列恶果”等。这些命题指认了资本消极影响的当代表现,极具警示意义。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和党的十八大报告,都将“市场经济考验”列为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之一,这也突出地体现了党对于资本逻辑消极效应的高度警觉。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对资本逻辑保持批判的根本立场,按照《共产党宣言》的经典表述,人类解放就是要取消第1页共11页“资本的个性和自由”而实现“人的个性和自由”。问题在于,我们在牢记这一最高纲领的基础上,主要的精力应放在探索实现这一纲领的具体步骤方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共产党宣言》所设想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革命的产物,而是马克思晚年所设想的经亚细亚生产方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产物。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苏联对斯大林模式弊端的反思与改革试验、中国的改革开放、越南的改革探索,到朝鲜经济政策的最新调整,早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是落后国家走向共产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台阶。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把作为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资本逻辑、市场机制,从资本主义制度中抽象出来而“为我所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由“基础性”表述提升为“决定性”表述[1],正是对这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律的积极肯定与能动运用。资本双重性———文明的积极性一面与文明的消极性一面的奇异纠缠,构成了打开现代社会全部悖谬奥秘的“总开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要求来看,探讨如何进一步发挥资本逻辑的积极效应,应是理论工作的重心所系。即使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保持时刻的、敏锐的批评锋芒,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应放在探索负面效应消解的具体途径上,而不是以笼统拒斥资本逻辑的方式不了了之。由此,我们将上述“研究与批判相等同的倾向”指认为理论对实践的一种偏离。当然,这种偏离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其隐蔽驱力的;与之相应,我们就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端正。首先,40年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的编写随着实践的创新而不断创新,虽然教科书几经修改,但教科书拥有强大的惯性和规范功能,尽管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过程中,均已突破了“资本主义等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这样的传统教条,还是有学者存在着“集体无意识”,而这种“集体无意识”又会无意识地代际继承。有鉴于此,教科书中关于马克思评价资本效应的多重维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