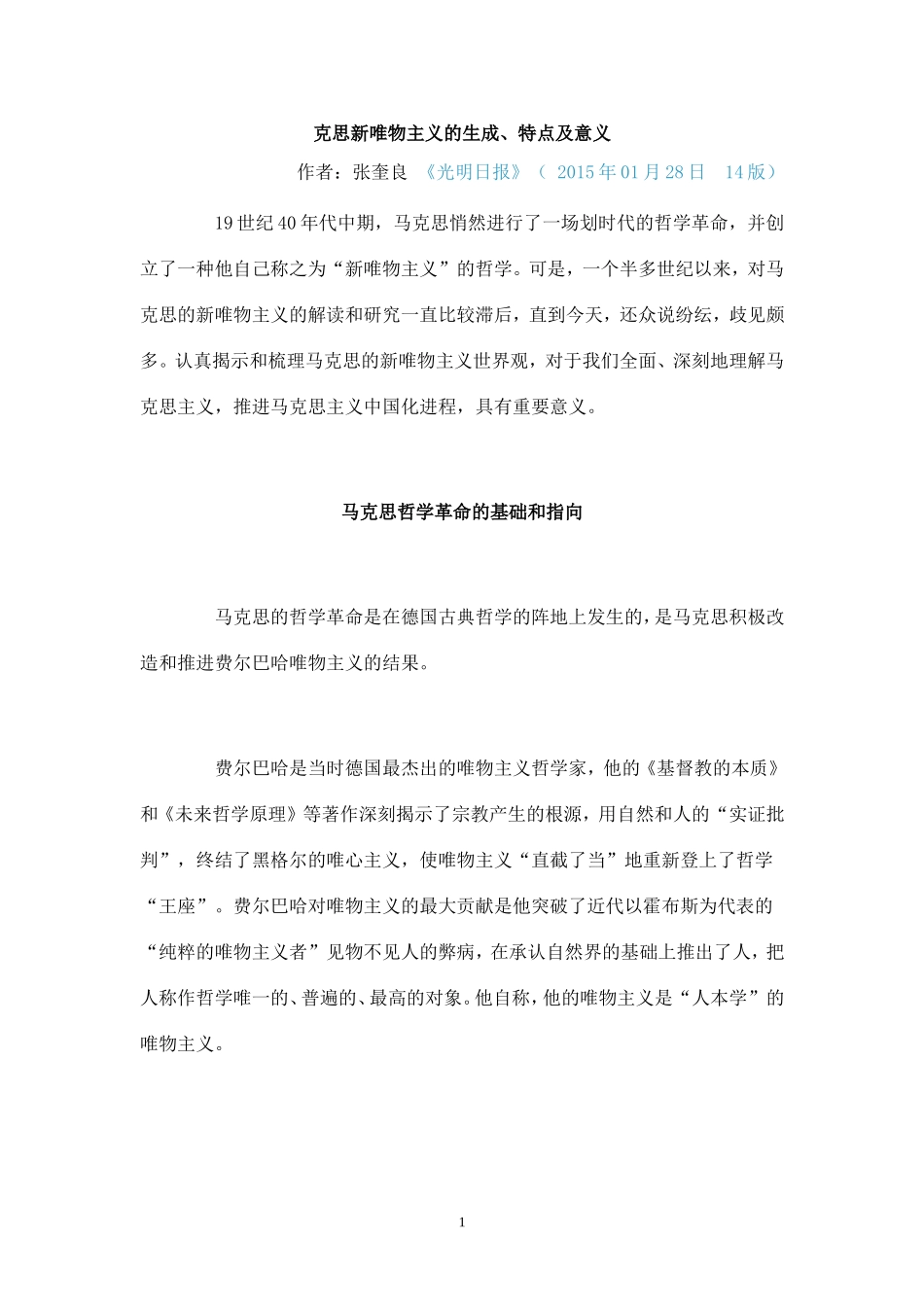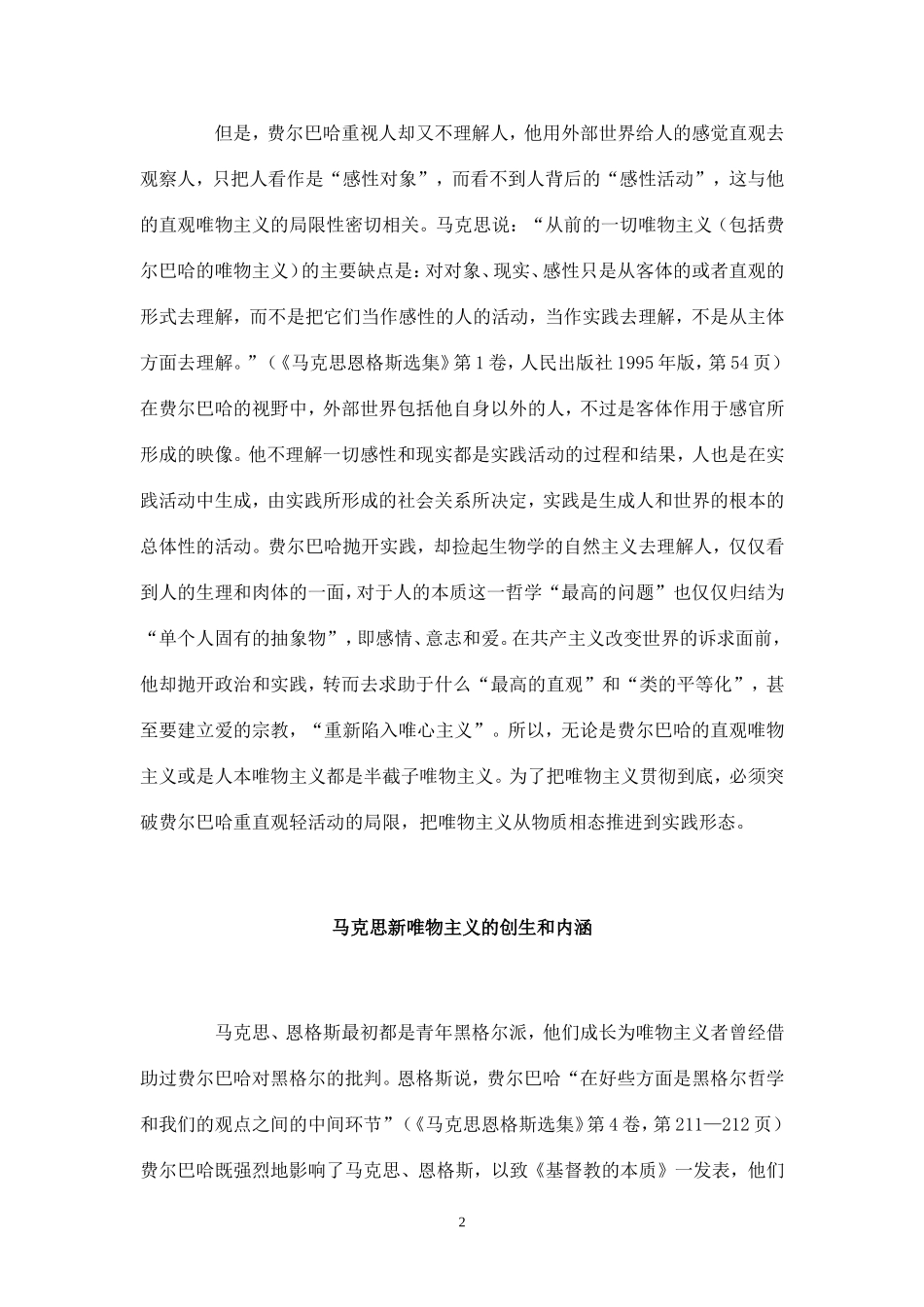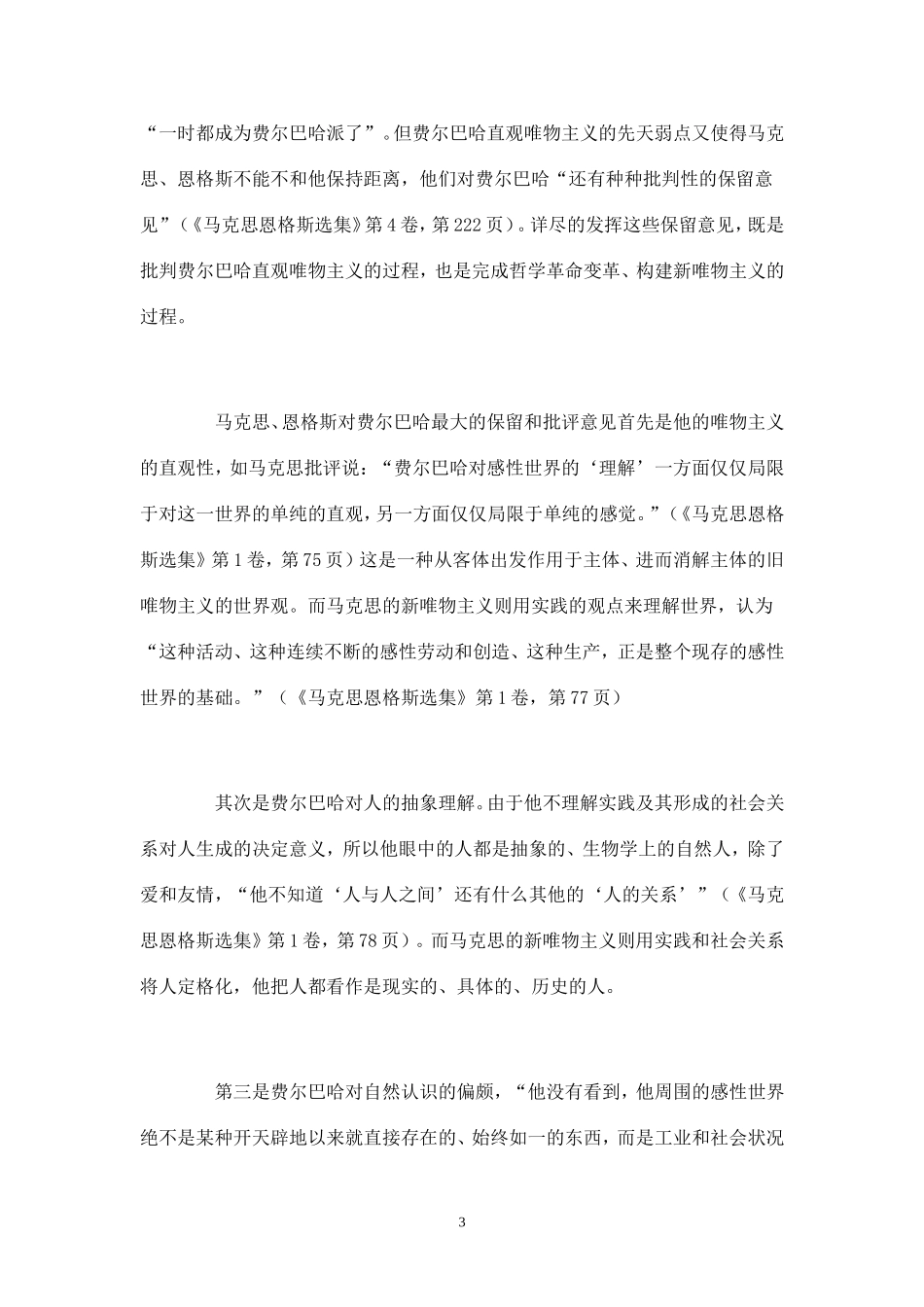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生成、特点及意义作者:张奎良《光明日报》(2015年01月28日14版)19世纪40年代中期,马克思悄然进行了一场划时代的哲学革命,并创立了一种他自己称之为“新唯物主义”的哲学。可是,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对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解读和研究一直比较滞后,直到今天,还众说纷纭,歧见颇多。认真揭示和梳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础和指向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阵地上发生的,是马克思积极改造和推进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结果。费尔巴哈是当时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基督教的本质》和《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深刻揭示了宗教产生的根源,用自然和人的“实证批判”,终结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使唯物主义“直截了当”地重新登上了哲学“王座”。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突破了近代以霍布斯为代表的“纯粹的唯物主义者”见物不见人的弊病,在承认自然界的基础上推出了人,把人称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他自称,他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的唯物主义。1但是,费尔巴哈重视人却又不理解人,他用外部世界给人的感觉直观去观察人,只把人看作是“感性对象”,而看不到人背后的“感性活动”,这与他的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密切相关。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在费尔巴哈的视野中,外部世界包括他自身以外的人,不过是客体作用于感官所形成的映像。他不理解一切感性和现实都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人也是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由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实践是生成人和世界的根本的总体性的活动。费尔巴哈抛开实践,却捡起生物学的自然主义去理解人,仅仅看到人的生理和肉体的一面,对于人的本质这一哲学“最高的问题”也仅仅归结为“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即感情、意志和爱。在共产主义改变世界的诉求面前,他却抛开政治和实践,转而去求助于什么“最高的直观”和“类的平等化”,甚至要建立爱的宗教,“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所以,无论是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或是人本唯物主义都是半截子唯物主义。为了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必须突破费尔巴哈重直观轻活动的局限,把唯物主义从物质相态推进到实践形态。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生和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最初都是青年黑格尔派,他们成长为唯物主义者曾经借助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恩格斯说,费尔巴哈“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212页)费尔巴哈既强烈地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以致《基督教的本质》一发表,他们2“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先天弱点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能不和他保持距离,他们对费尔巴哈“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页)。详尽的发挥这些保留意见,既是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过程,也是完成哲学革命变革、构建新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最大的保留和批评意见首先是他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如马克思批评说:“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这是一种从客体出发作用于主体、进而消解主体的旧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则用实践的观点来理解世界,认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其次是费尔巴哈对人的抽象理解。由于他不理解实践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人生成的决定意义,所以他眼中的人都是抽象的、生物学上的自然人,除了爱和友情,“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