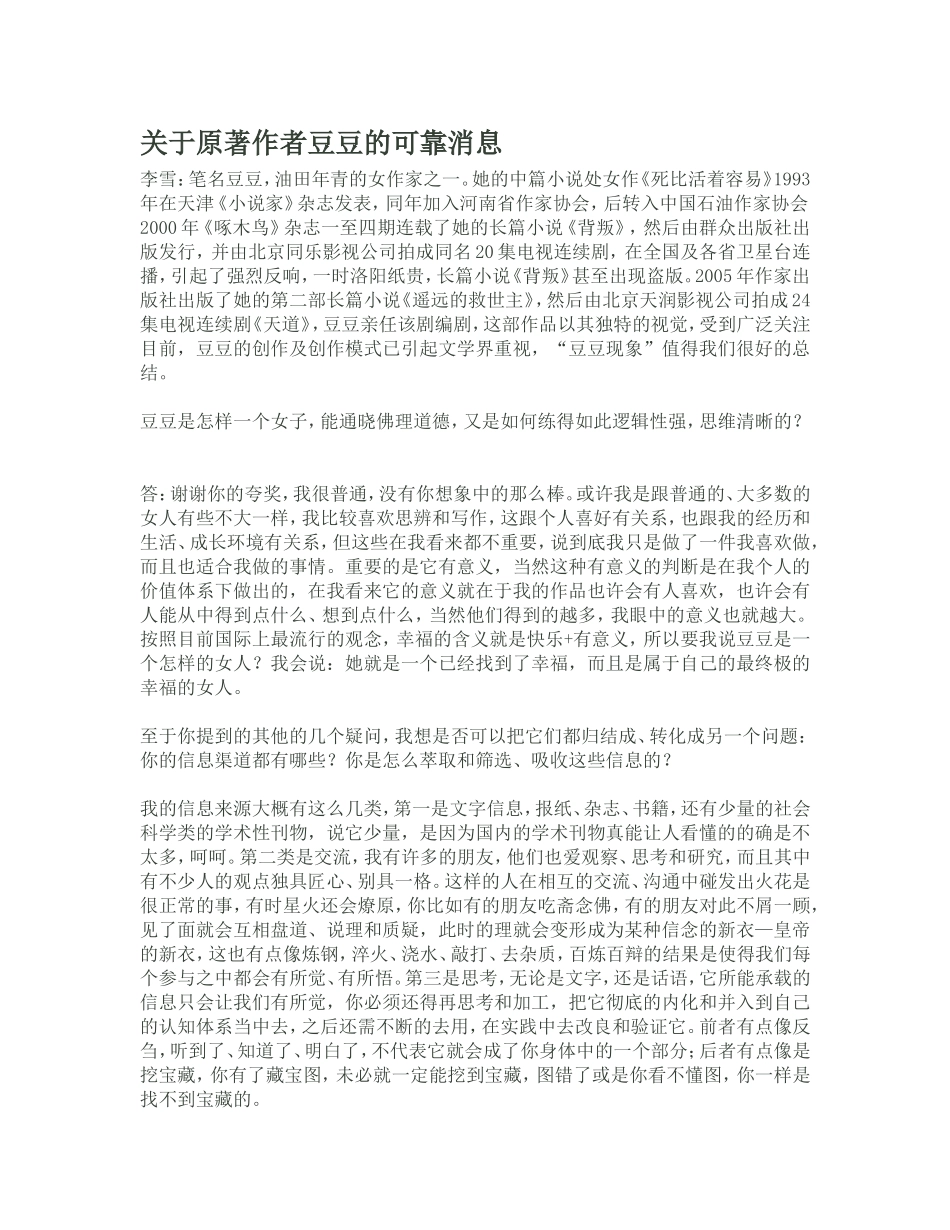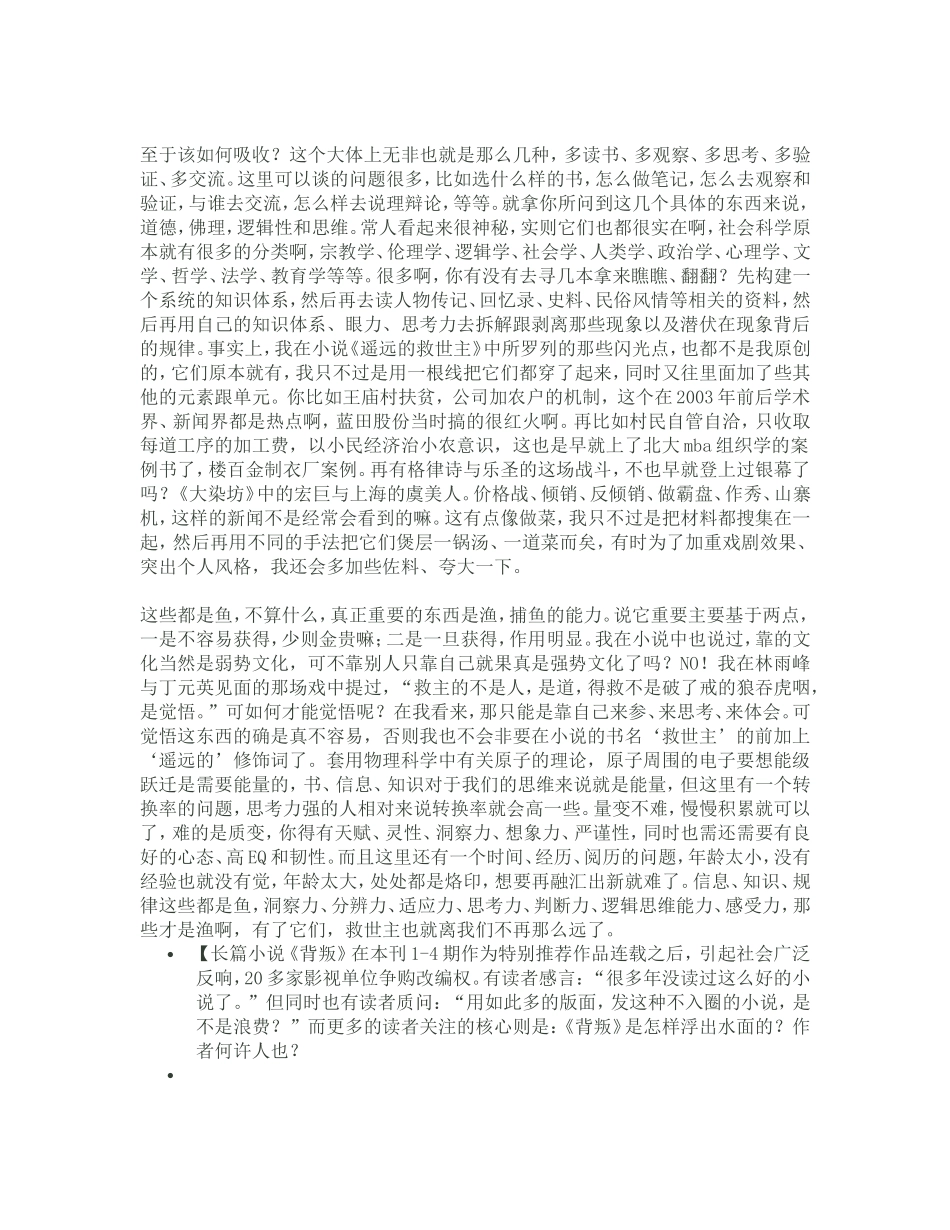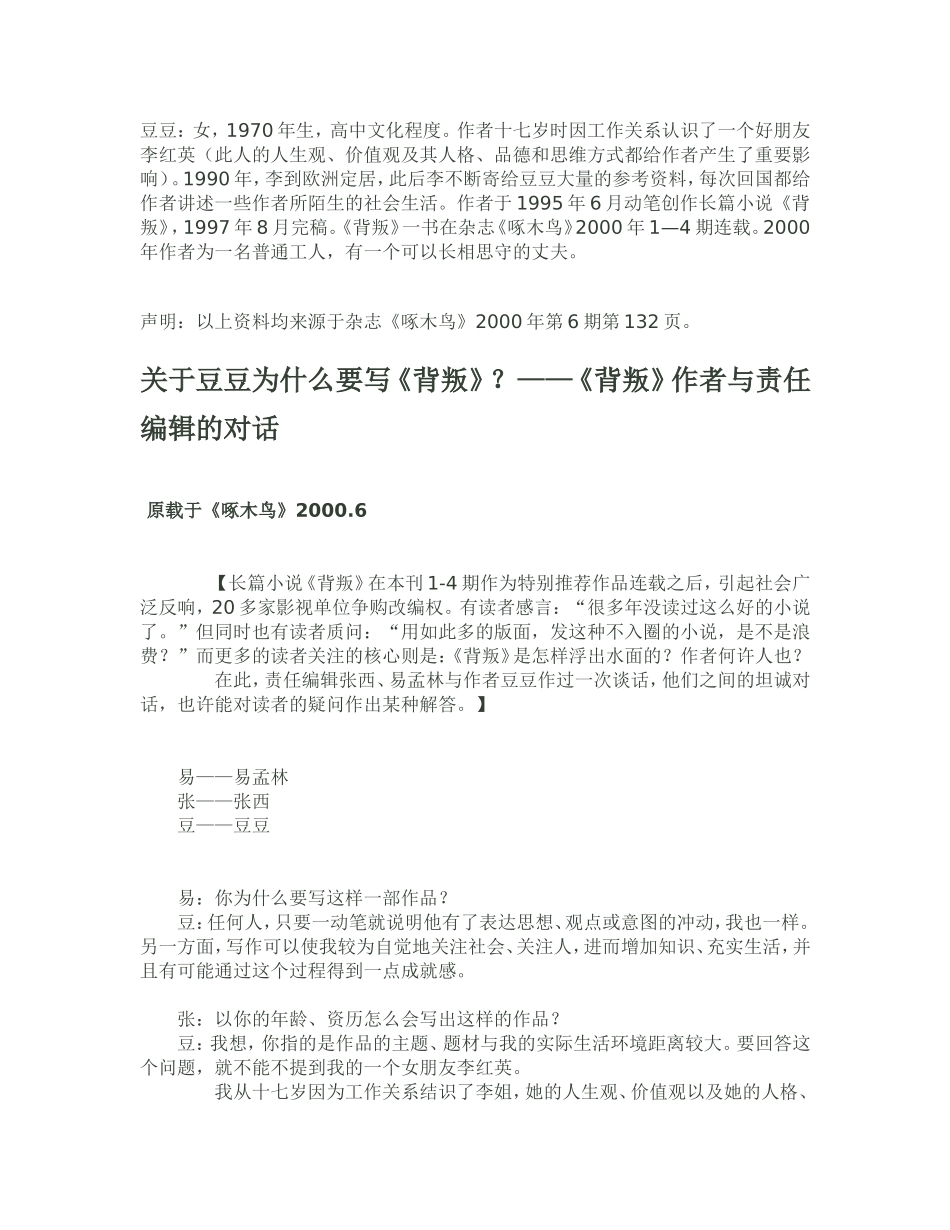关于原著作者豆豆的可靠消息李雪:笔名豆豆,油田年青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死比活着容易》1993年在天津《小说家》杂志发表,同年加入河南省作家协会,后转入中国石油作家协会2000年《啄木鸟》杂志一至四期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背叛》,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并由北京同乐影视公司拍成同名20集电视连续剧,在全国及各省卫星台连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长篇小说《背叛》甚至出现盗版。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遥远的救世主》,然后由北京天润影视公司拍成24集电视连续剧《天道》,豆豆亲任该剧编剧,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受到广泛关注目前,豆豆的创作及创作模式已引起文学界重视,“豆豆现象”值得我们很好的总结。豆豆是怎样一个女子,能通晓佛理道德,又是如何练得如此逻辑性强,思维清晰的?答:谢谢你的夸奖,我很普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棒。或许我是跟普通的、大多数的女人有些不大一样,我比较喜欢思辨和写作,这跟个人喜好有关系,也跟我的经历和生活、成长环境有关系,但这些在我看来都不重要,说到底我只是做了一件我喜欢做,而且也适合我做的事情。重要的是它有意义,当然这种有意义的判断是在我个人的价值体系下做出的,在我看来它的意义就在于我的作品也许会有人喜欢,也许会有人能从中得到点什么、想到点什么,当然他们得到的越多,我眼中的意义也就越大。按照目前国际上最流行的观念,幸福的含义就是快乐+有意义,所以要我说豆豆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我会说:她就是一个已经找到了幸福,而且是属于自己的最终极的幸福的女人。至于你提到的其他的几个疑问,我想是否可以把它们都归结成、转化成另一个问题:你的信息渠道都有哪些?你是怎么萃取和筛选、吸收这些信息的?我的信息来源大概有这么几类,第一是文字信息,报纸、杂志、书籍,还有少量的社会科学类的学术性刊物,说它少量,是因为国内的学术刊物真能让人看懂的的确是不太多,呵呵。第二类是交流,我有许多的朋友,他们也爱观察、思考和研究,而且其中有不少人的观点独具匠心、别具一格。这样的人在相互的交流、沟通中碰发出火花是很正常的事,有时星火还会燎原,你比如有的朋友吃斋念佛,有的朋友对此不屑一顾,见了面就会互相盘道、说理和质疑,此时的理就会变形成为某种信念的新衣—皇帝的新衣,这也有点像炼钢,淬火、浇水、敲打、去杂质,百炼百辩的结果是使得我们每个参与之中都会有所觉、有所悟。第三是思考,无论是文字,还是话语,它所能承载的信息只会让我们有所觉,你必须还得再思考和加工,把它彻底的内化和并入到自己的认知体系当中去,之后还需不断的去用,在实践中去改良和验证它。前者有点像反刍,听到了、知道了、明白了,不代表它就会成了你身体中的一个部分;后者有点像是挖宝藏,你有了藏宝图,未必就一定能挖到宝藏,图错了或是你看不懂图,你一样是找不到宝藏的。至于该如何吸收?这个大体上无非也就是那么几种,多读书、多观察、多思考、多验证、多交流。这里可以谈的问题很多,比如选什么样的书,怎么做笔记,怎么去观察和验证,与谁去交流,怎么样去说理辩论,等等。就拿你所问到这几个具体的东西来说,道德,佛理,逻辑性和思维。常人看起来很神秘,实则它们也都很实在啊,社会科学原本就有很多的分类啊,宗教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哲学、法学、教育学等等。很多啊,你有没有去寻几本拿来瞧瞧、翻翻?先构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然后再去读人物传记、回忆录、史料、民俗风情等相关的资料,然后再用自己的知识体系、眼力、思考力去拆解跟剥离那些现象以及潜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事实上,我在小说《遥远的救世主》中所罗列的那些闪光点,也都不是我原创的,它们原本就有,我只不过是用一根线把它们都穿了起来,同时又往里面加了些其他的元素跟单元。你比如王庙村扶贫,公司加农户的机制,这个在2003年前后学术界、新闻界都是热点啊,蓝田股份当时搞的很红火啊。再比如村民自管自洽,只收取每道工序的加工费,以小民经济治小农意识,这也是早就上了北大mba组织学的案例书了,楼百金制衣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