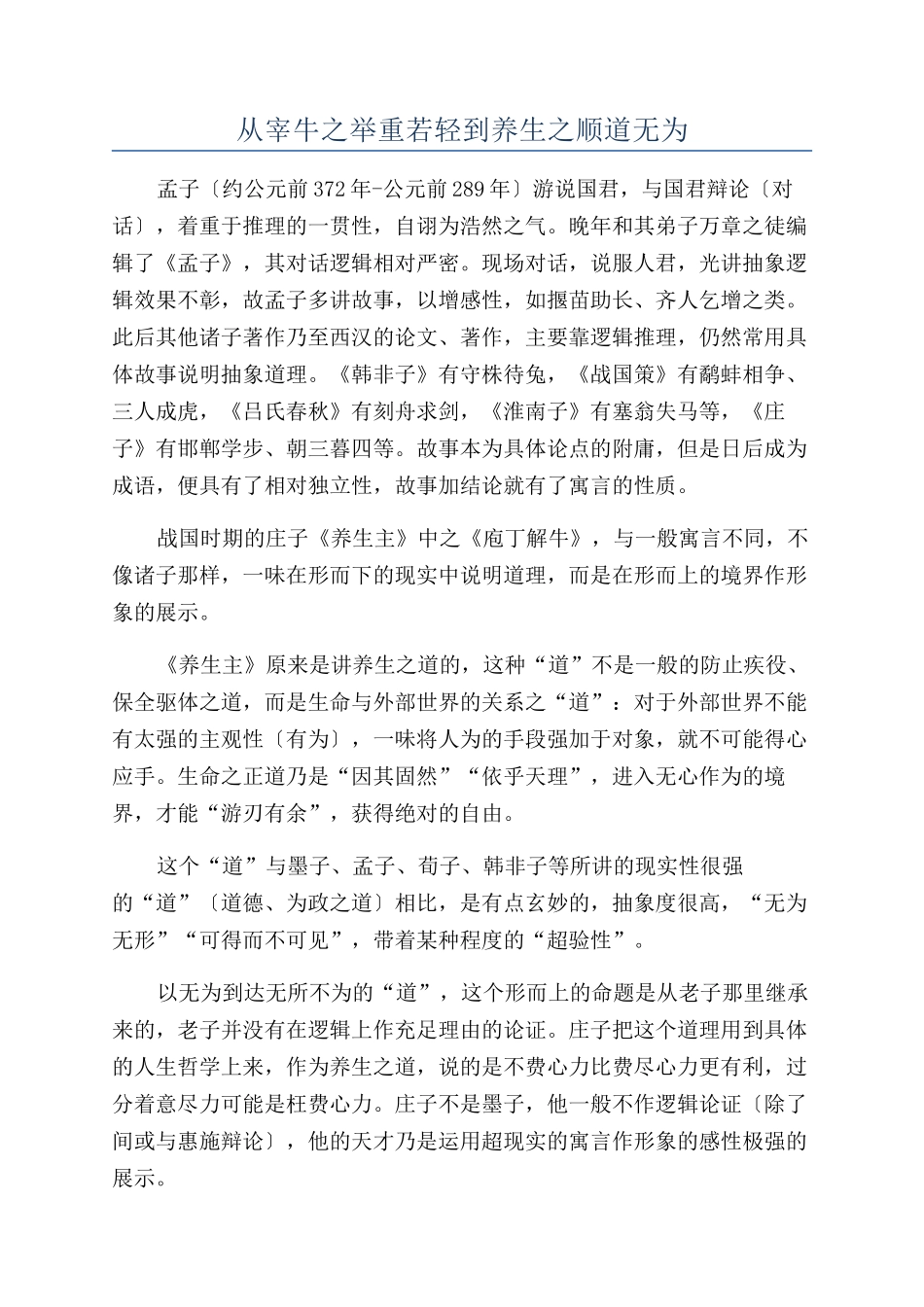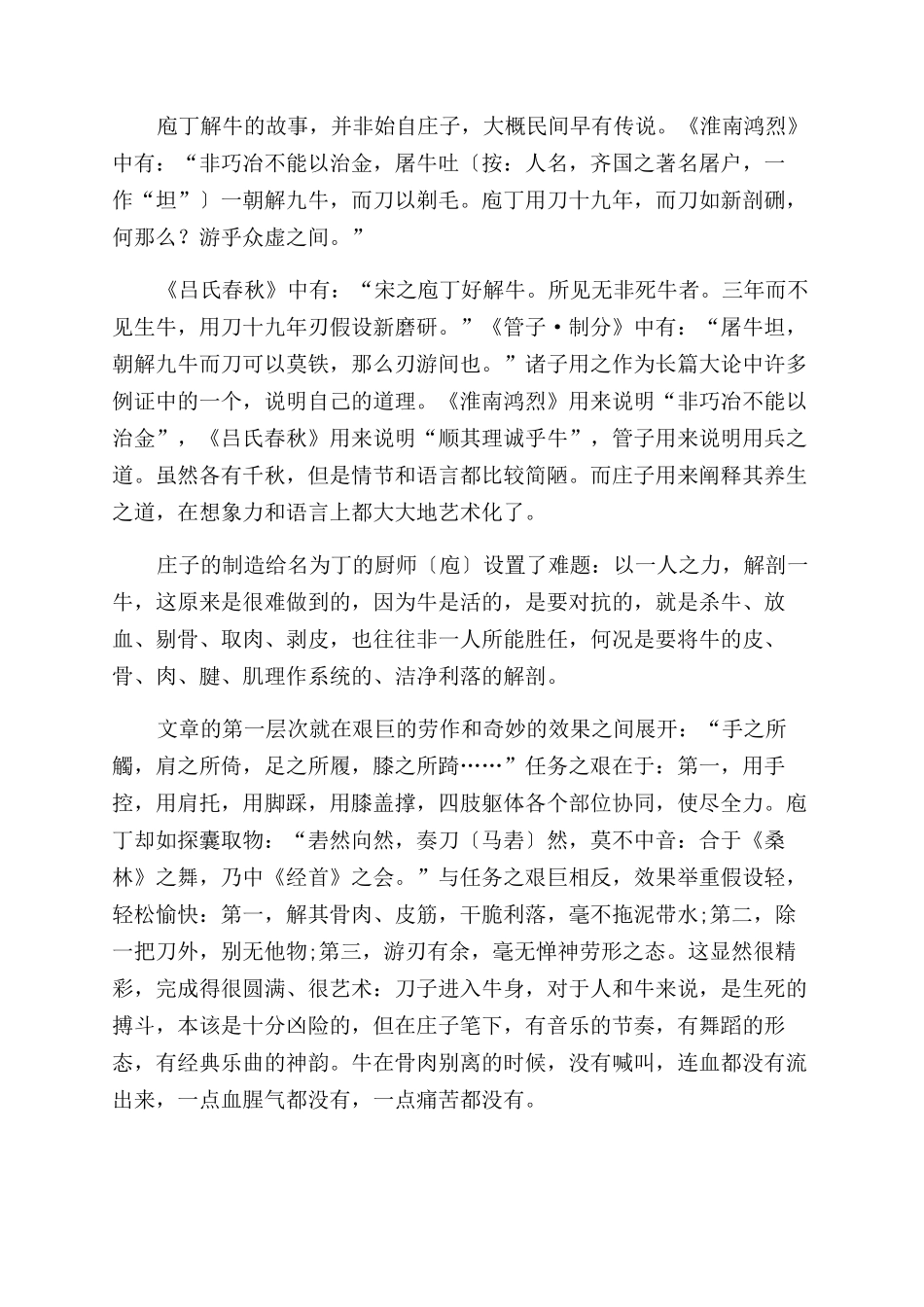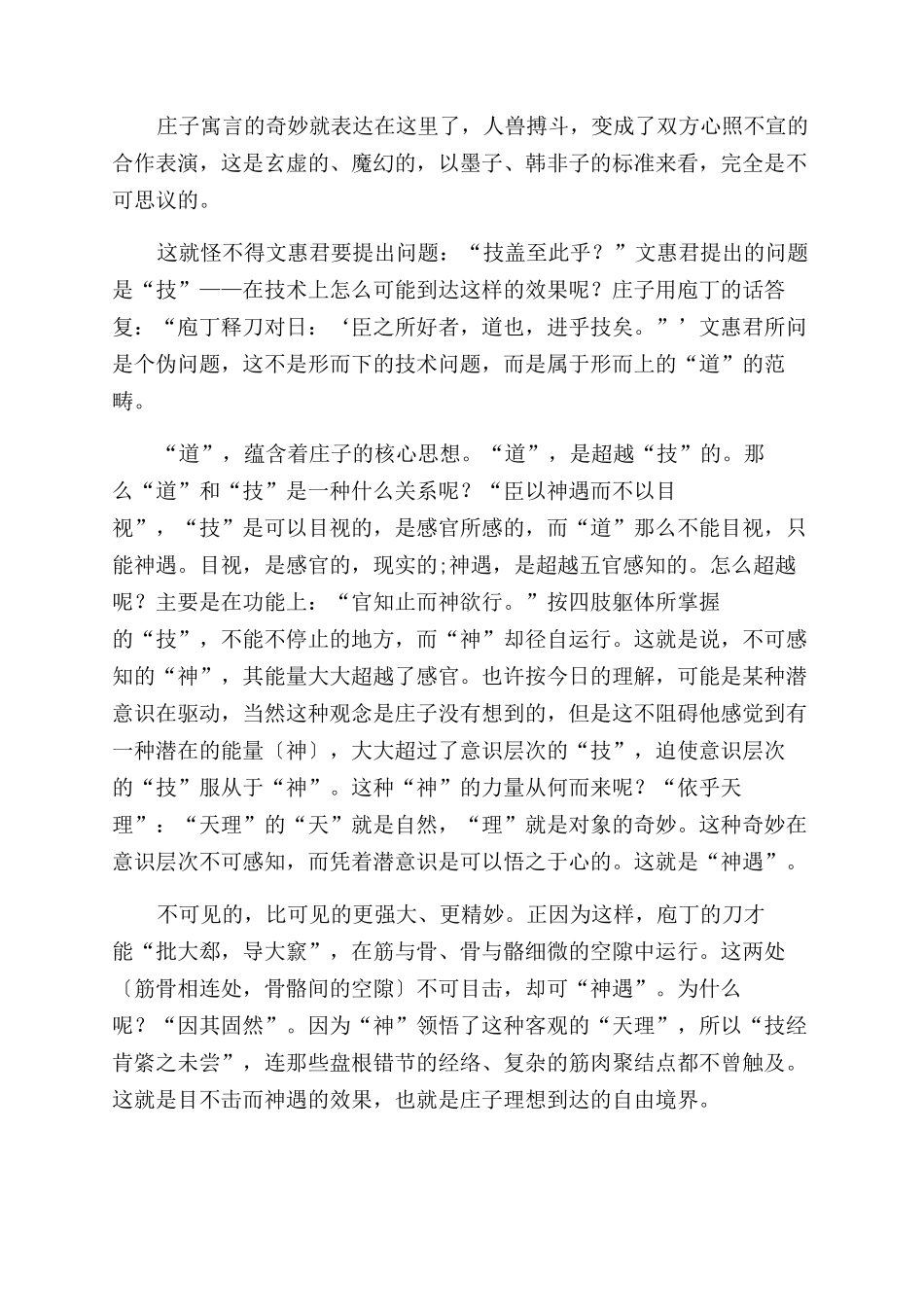从宰牛之举重若轻到养生之顺道无为孟子〔约公元前 372 年-公元前 289 年〕游说国君,与国君辩论〔对话〕,着重于推理的一贯性,自诩为浩然之气。晚年和其弟子万章之徒编辑了《孟子》,其对话逻辑相对严密。现场对话,说服人君,光讲抽象逻辑效果不彰,故孟子多讲故事,以增感性,如揠苗助长、齐人乞增之类。此后其他诸子著作乃至西汉的论文、著作,主要靠逻辑推理,仍然常用具体故事说明抽象道理。《韩非子》有守株待兔,《战国策》有鹬蚌相争、三人成虎,《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淮南子》有塞翁失马等,《庄子》有邯郸学步、朝三暮四等。故事本为具体论点的附庸,但是日后成为成语,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故事加结论就有了寓言的性质。战国时期的庄子《养生主》中之《庖丁解牛》,与一般寓言不同,不像诸子那样,一味在形而下的现实中说明道理,而是在形而上的境界作形象的展示。《养生主》原来是讲养生之道的,这种“道”不是一般的防止疾役、保全驱体之道,而是生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道”:对于外部世界不能有太强的主观性〔有为〕,一味将人为的手段强加于对象,就不可能得心应手。生命之正道乃是“因其固然”“依乎天理”,进入无心作为的境界,才能“游刃有余”,获得绝对的自由。这个“道”与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所讲的现实性很强的“道”〔道德、为政之道〕相比,是有点玄妙的,抽象度很高,“无为无形”“可得而不可见”,带着某种程度的“超验性”。以无为到达无所不为的“道”,这个形而上的命题是从老子那里继承来的,老子并没有在逻辑上作充足理由的论证。庄子把这个道理用到具体的人生哲学上来,作为养生之道,说的是不费心力比费尽心力更有利,过分着意尽力可能是枉费心力。庄子不是墨子,他一般不作逻辑论证〔除了间或与惠施辩论〕,他的天才乃是运用超现实的寓言作形象的感性极强的展示。庖丁解牛的故事,并非始自庄子,大概民间早有传说。《淮南鸿烈》中有:“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按:人名,齐国之著名屠户,一作“坦”〕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那么?游乎众虚之间。”《吕氏春秋》中有:“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假设新磨研。”《管子·制分》中有:“屠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莫铁,那么刃游间也。”诸子用之作为长篇大论中许多例证中的一个,说明自己的道理。《淮南鸿烈》用来说明“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吕氏春秋》用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