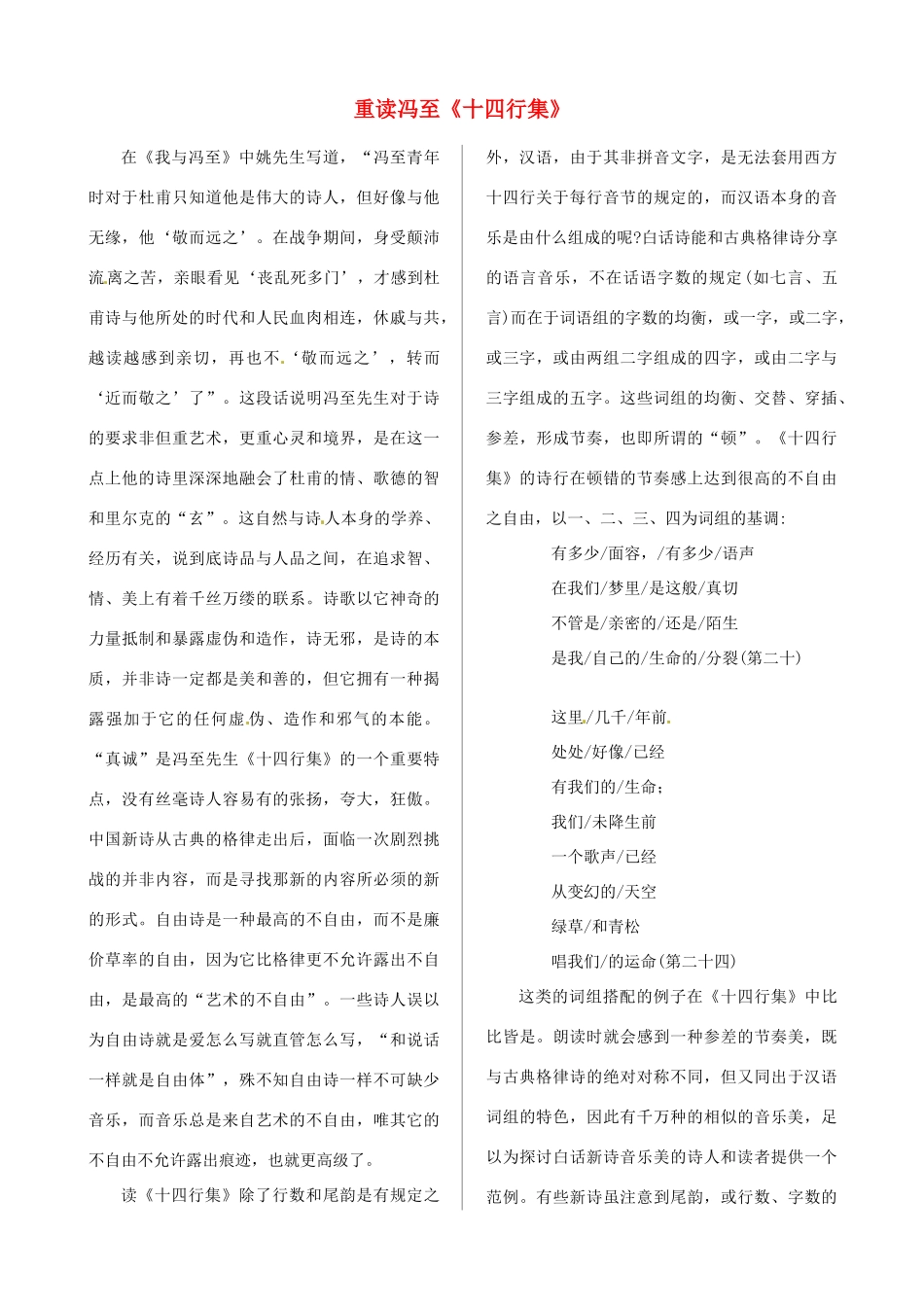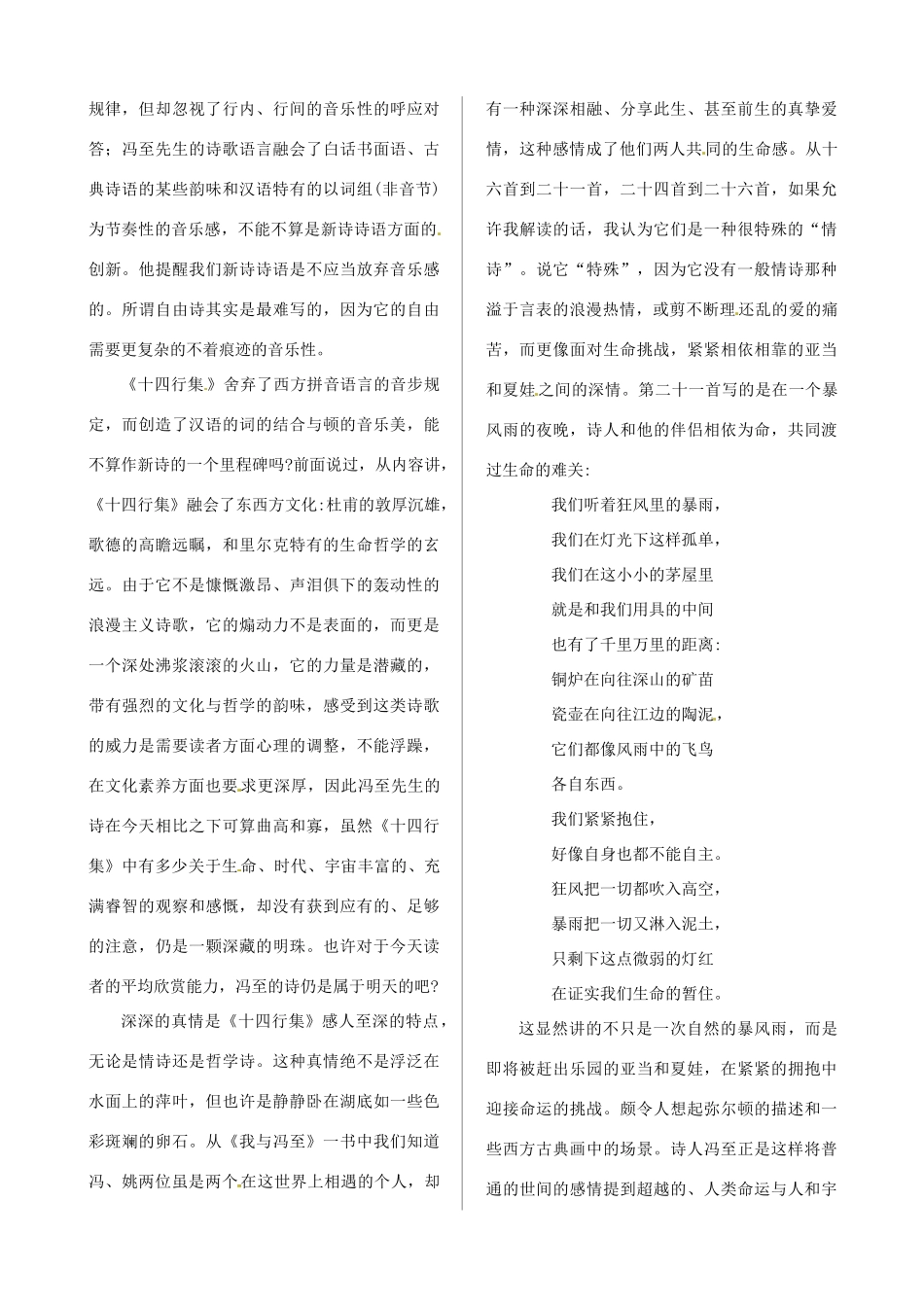重读冯至《十四行集》在《我与冯至》中姚先生写道,“冯至青年时对于杜甫只知道他是伟大的诗人,但好像与他无缘,他‘敬而远之’。在战争期间,身受颠沛流离之苦,亲眼看见‘丧乱死多门’,才感到杜甫诗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人民血肉相连,休戚与共,越读越感到亲切,再也不 ‘敬而远之’,转而‘近而敬之’了”。这段话说明冯至先生对于诗的要求非但重艺术,更重心灵和境界,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里深深地融会了杜甫的情、歌德的智和里尔克的“玄”。这自然与诗 人本身的学养、经历有关,说到底诗品与人品之间,在追求智、情、美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诗歌以它神奇的力量抵制和暴露虚伪和造作,诗无邪,是诗的本质,并非诗一定都是美和善的,但它拥有一种揭露强加于它的任何虚 伪、造作和邪气的本能。“真诚”是冯至先生《十四行集》的一个重要特点,没有丝毫诗人容易有的张扬,夸大,狂傲。中国新诗从古典的格律走出后,面临一次剧烈挑战的并非内容,而是寻找那新的内容所必须的新的形式。自由诗是一种最高的不自由,而不是廉价草率的自由,因为它比格律更不允许露出不自由,是最高的“艺术的不自由”。一些诗人误以为自由诗就是爱怎么写就直管怎么写,“和说话一样就是自由体”,殊不知自由诗一样不可缺少音乐,而音乐总是来自艺术的不自由,唯其它的不自由不允许露出痕迹,也就更高级了。读《十四行集》除了行数和尾韵是有规定之外,汉语,由于其非拼音文字,是无法套用西方十四行关于每行音节的规定的,而汉语本身的音乐是由什么组成的呢?白话诗能和古典格律诗分享的语言音乐,不在话语字数的规定(如七言、五言)而在于词语组的字数的均衡,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或由两组二字组成的四字,或由二字与三字组成的五字。这些词组的均衡、交替、穿插、参差,形成节奏,也即所谓的“顿”。《十四行集》的诗行在顿错的节奏感上达到很高的不自由之自由,以一、二、三、四为词组的基调: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 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 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 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第二十)这里/几千/年前 处处/好像/已经 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未降生前 一个歌声/已经 从变幻的/天空 绿草/和青松 唱我们/的运命(第二十四) 这类的词组搭配的例子在《十四行集》中比比皆是。朗读时就会感到一种参差的节奏美,既与古典格律诗的绝对对称不同,但又同出于汉语词组的特色,因此有千万种的相似的音乐美,足以为探讨白话新诗音乐美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