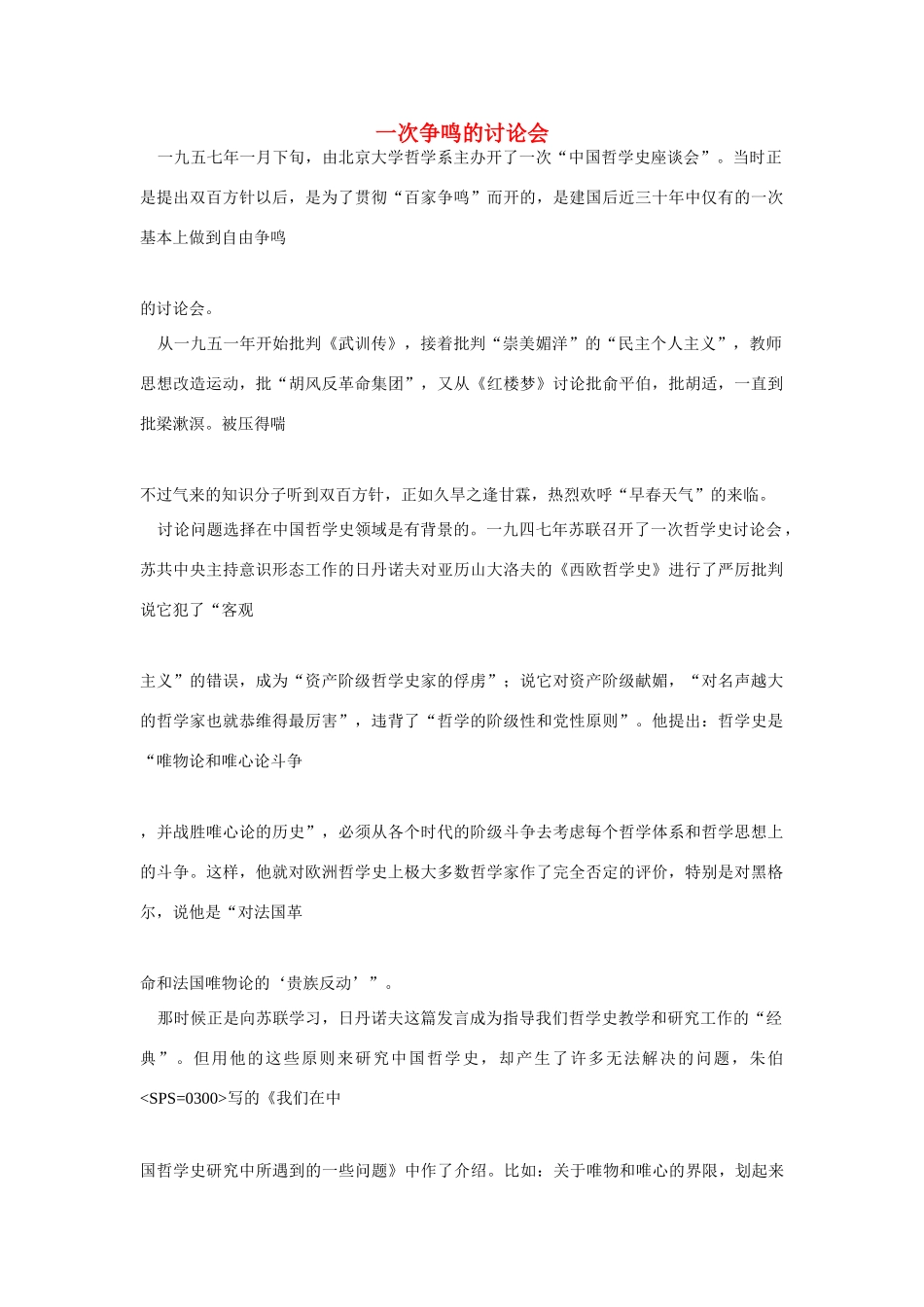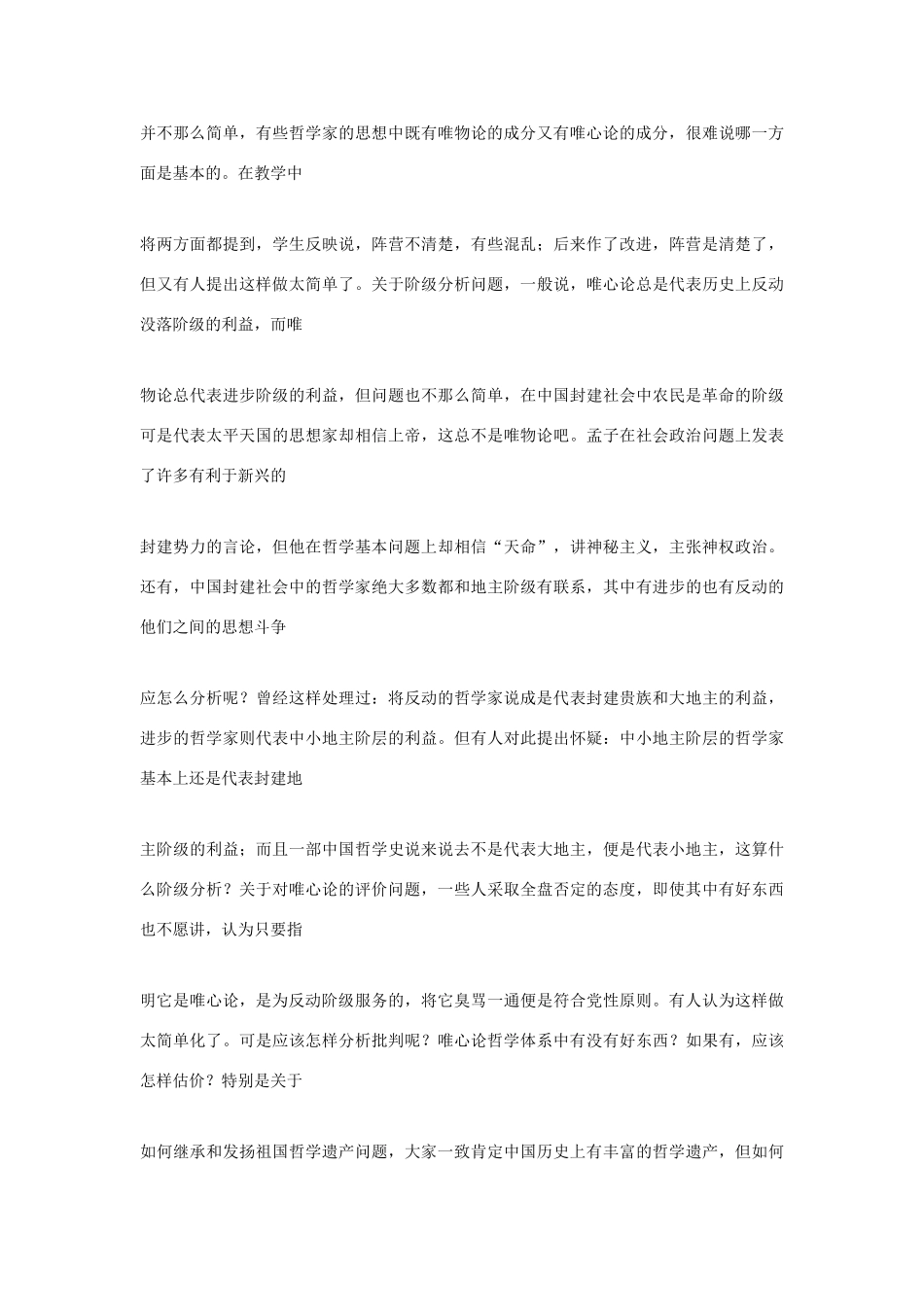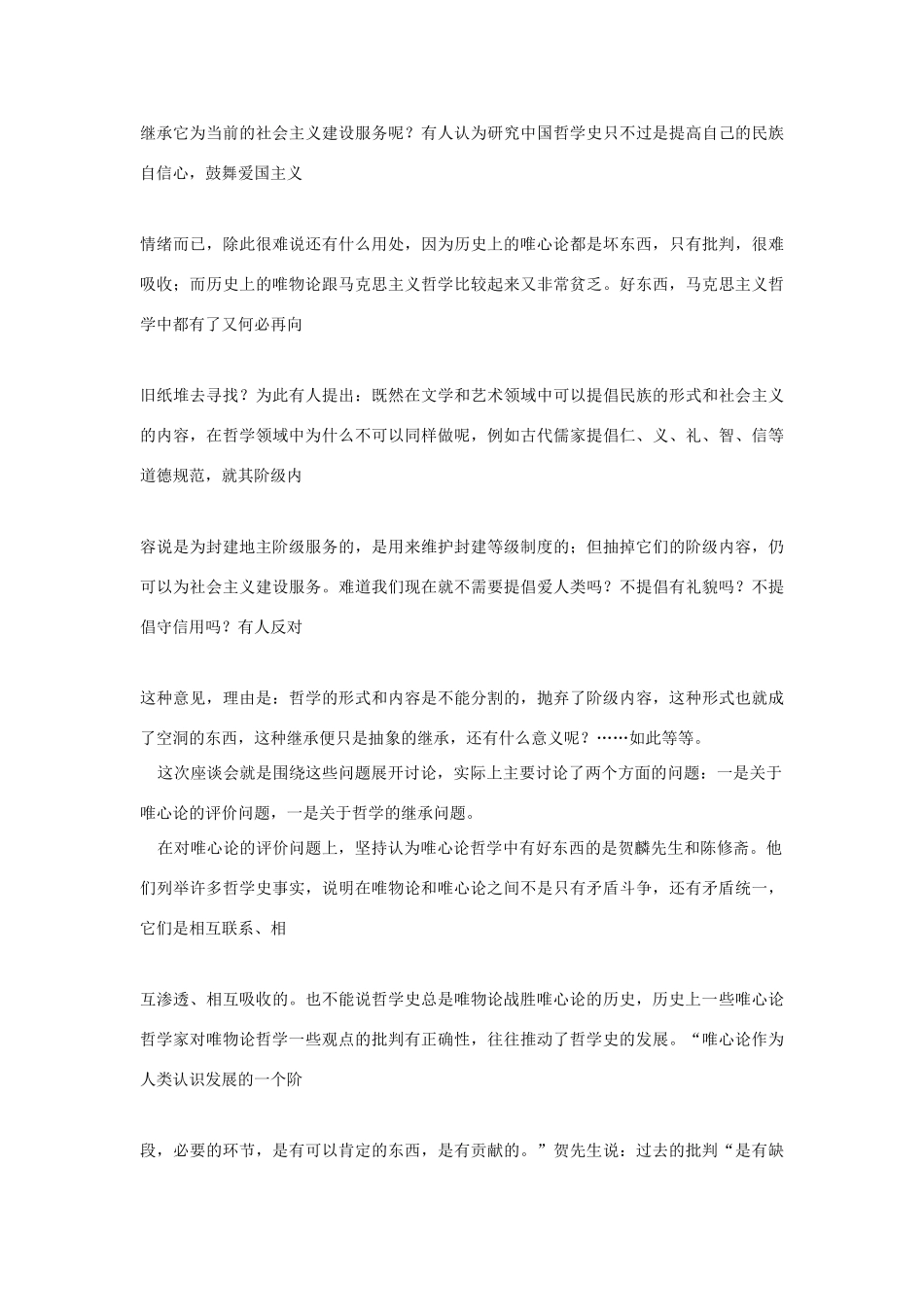一次争鸣的讨论会 一九五七年一月下旬,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开了一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当时正是提出双百方针以后,是为了贯彻“百家争鸣”而开的,是建国后近三十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批判《武训传》,接着批判“崇美媚洋”的“民主个人主义”,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又从《红楼梦》讨论批俞平伯,批胡适,一直到批梁漱溟。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知识分子听到双百方针,正如久旱之逢甘霖,热烈欢呼“早春天气”的来临。 讨论问题选择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是有背景的。一九四七年苏联召开了一次哲学史讨论会 ,苏共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进行了严厉批判说它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成为“资产阶级哲学史家的俘虏”;说它对资产阶级献媚,“对名声越大的哲学家也就恭维得最厉害”,违背了“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原则”。他提出: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并战胜唯心论的历史”,必须从各个时代的阶级斗争去考虑每个哲学体系和哲学思想上的斗争。这样,他就对欧洲哲学史上极大多数哲学家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特别是对黑格尔,说他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论的‘贵族反动’”。 那时候正是向苏联学习,日丹诺夫这篇发言成为指导我们哲学史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经典”。但用他的这些原则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却产生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朱伯写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中作了介绍。比如:关于唯物和唯心的界限,划起来并不那么简单,有些哲学家的思想中既有唯物论的成分又有唯心论的成分,很难说哪一方面是基本的。在教学中将两方面都提到,学生反映说,阵营不清楚,有些混乱;后来作了改进,阵营是清楚了,但又有人提出这样做太简单了。关于阶级分析问题,一般说,唯心论总是代表历史上反动没落阶级的利益,而唯物论总代表进步阶级的利益,但问题也不那么简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是革命的阶级可是代表太平天国的思想家却相信上帝,这总不是唯物论吧。孟子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发表了许多有利于新兴的封建势力的言论,但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却相信“天命”,讲神秘主义,主张神权政治。还有,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哲学家绝大多数都和地主阶级有联系,其中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他们之间的思想斗争应怎么分析呢?曾经这样处理过:将反动的哲学家说成是代表封建贵族和大地主的利益,进步的哲学家则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