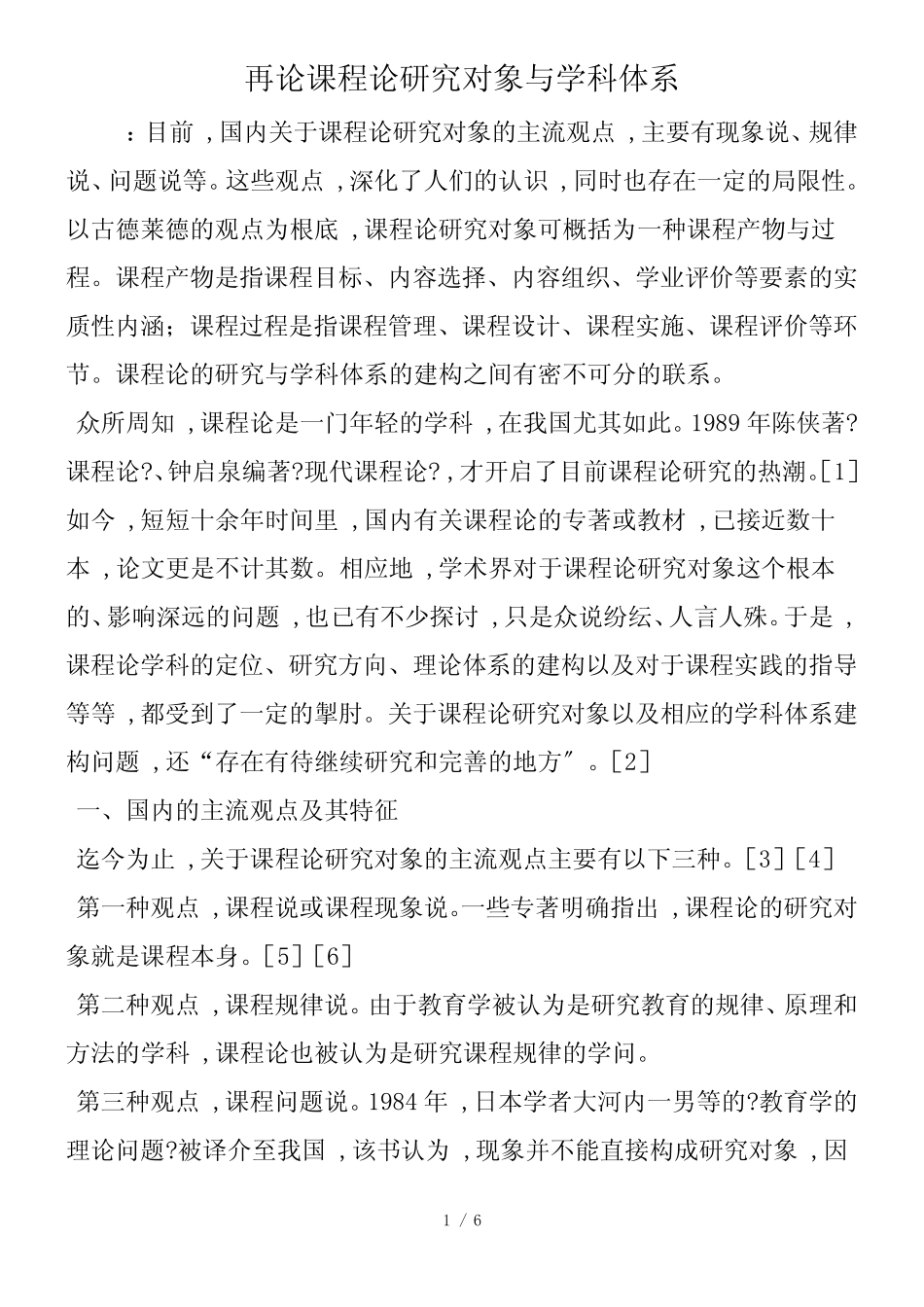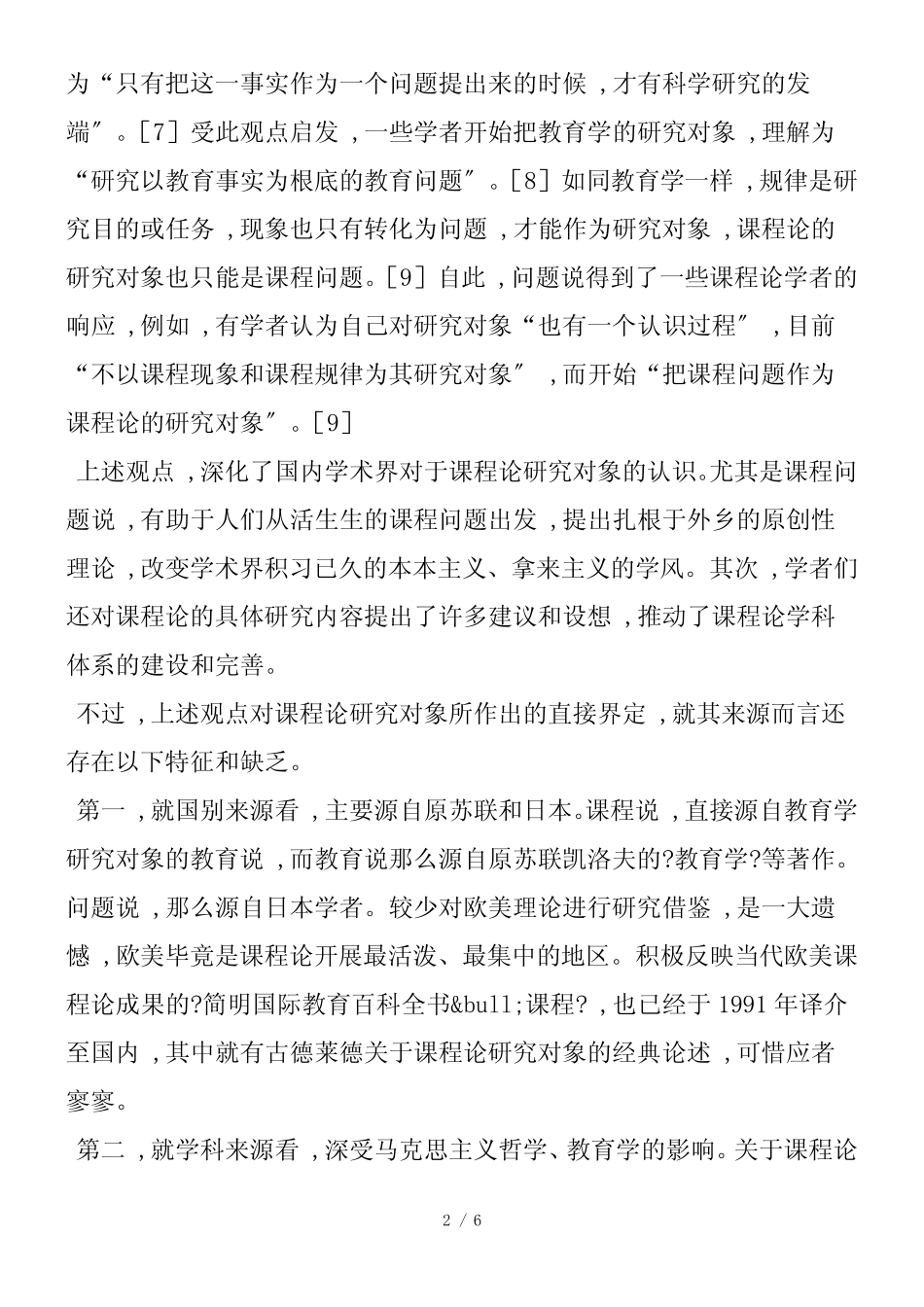1/6再论课程论研究对象与学科体系:目前,国内关于课程论研究对象的主流观点,主要有现象说、规律说、问题说等。这些观点,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古德莱德的观点为根底,课程论研究对象可概括为一种课程产物与过程。课程产物是指课程目标、内容选择、内容组织、学业评价等要素的实质性内涵;课程过程是指课程管理、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环节。课程论的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建构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众所周知,课程论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尤其如此。1989年陈侠著?课程论?、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才开启了目前课程论研究的热潮。[1]如今,短短十余年时间里,国内有关课程论的专著或教材,已接近数十本,论文更是不计其数。相应地,学术界对于课程论研究对象这个根本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也已有不少探讨,只是众说纷纭、人言人殊。于是,课程论学科的定位、研究方向、理论体系的建构以及对于课程实践的指导等等,都受到了一定的掣肘。关于课程论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学科体系建构问题,还“存在有待继续研究和完善的地方〞。[2]一、国内的主流观点及其特征迄今为止,关于课程论研究对象的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3][4]第一种观点,课程说或课程现象说。一些专著明确指出,课程论的研究对象就是课程本身。[5][6]第二种观点,课程规律说。由于教育学被认为是研究教育的规律、原理和方法的学科,课程论也被认为是研究课程规律的学问。第三种观点,课程问题说。1984年,日本学者大河内一男等的?教育学的理论问题?被译介至我国,该书认为,现象并不能直接构成研究对象,因2/6为“只有把这一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才有科学研究的发端〞。[7]受此观点启发,一些学者开始把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研究以教育事实为根底的教育问题〞。[8]如同教育学一样,规律是研究目的或任务,现象也只有转化为问题,才能作为研究对象,课程论的研究对象也只能是课程问题。[9]自此,问题说得到了一些课程论学者的响应,例如,有学者认为自己对研究对象“也有一个认识过程〞,目前“不以课程现象和课程规律为其研究对象〞,而开始“把课程问题作为课程论的研究对象〞。[9]上述观点,深化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课程论研究对象的认识。尤其是课程问题说,有助于人们从活生生的课程问题出发,提出扎根于外乡的原创性理论,改变学术界积习已久的本本主义、拿来主义的学风。其次,学者们还对课程论的具体研究内容提出了许多建议和设想,推动了课程论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过,上述观点对课程论研究对象所作出的直接界定,就其来源而言还存在以下特征和缺乏。第一,就国别来源看,主要源自原苏联和日本。课程说,直接源自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教育说,而教育说那么源自原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等著作。问题说,那么源自日本学者。较少对欧美理论进行研究借鉴,是一大遗憾,欧美毕竟是课程论开展最活泼、最集中的地区。积极反映当代欧美课程论成果的?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也已经于1991年译介至国内,其中就有古德莱德关于课程论研究对象的经典论述,可惜应者寥寥。第二,就学科来源看,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的影响。关于课程论3/6研究对象所使用的核心词汇,如现象、规律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词汇,均被搬用过来了。而且,在论证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也多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如认识论、矛盾论。教育学的影响就更加直接。有人考察了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类型,认为有教育说、教育现象或规律说、教育问题说等几类。[10]课程论研究对象的观点,与此惊人相似。但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意义和上位学科教育学的启迪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更广泛地从其他相关学科〔包括从教育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获得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有益启示和借鉴。第三,就思维方法看,源自研究过程的各个环节。我们知道,任何研究过程,起始于某个客观事实、现象或者事件,从中发现问题,经过一手和二手资料的收集与分析,最后得出规律和结论。这样,课程研究的各个环节,即课程本身或者课程现象、课程问题、课程规律等等,就被理解为课程论的研究对象了。这样的思维方法,是否就是唯一的选择呢?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