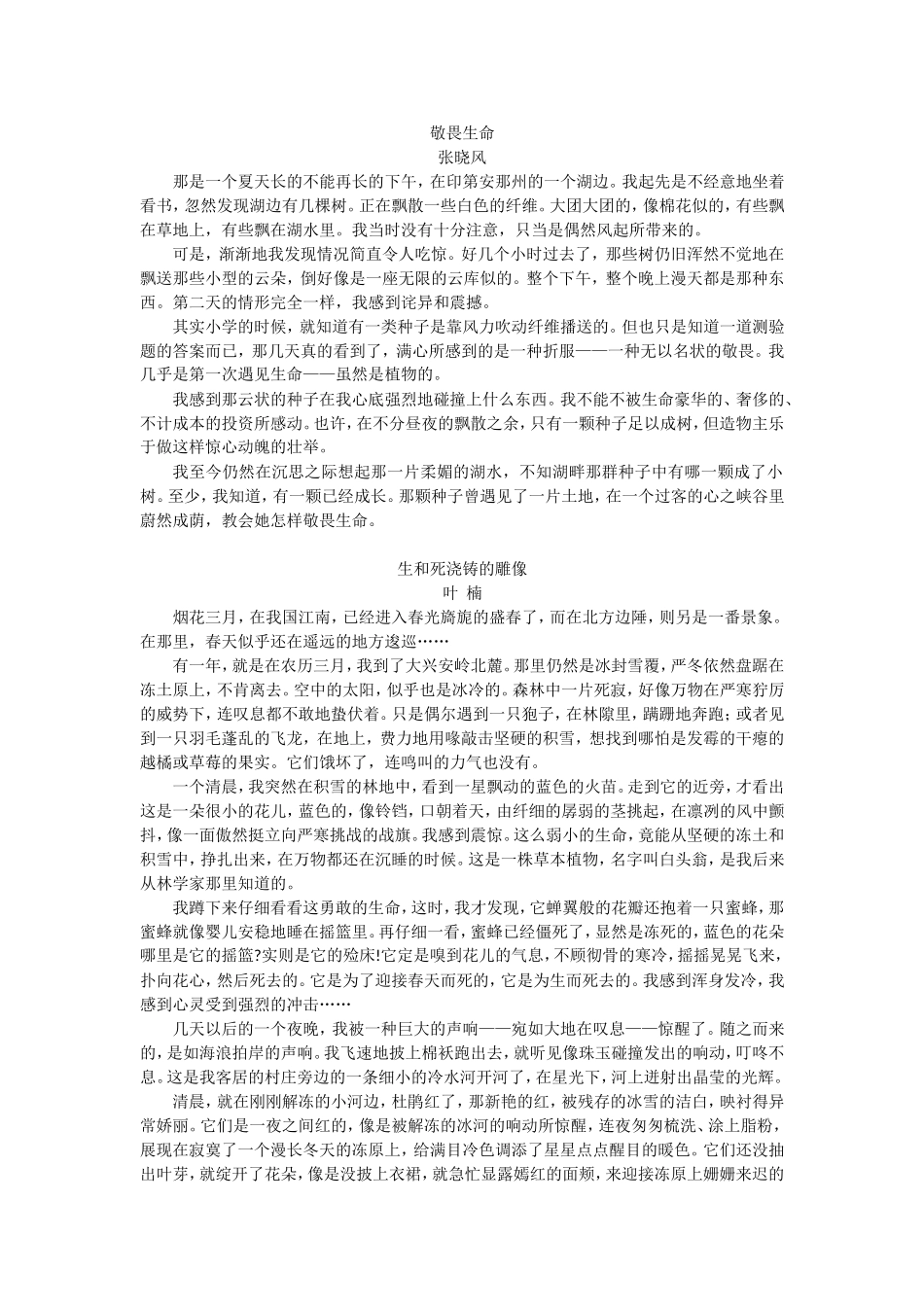敬畏生命张晓风那是一个夏天长的不能再长的下午,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湖边。我起先是不经意地坐着看书,忽然发现湖边有几棵树。正在飘散一些白色的纤维。大团大团的,像棉花似的,有些飘在草地上,有些飘在湖水里。我当时没有十分注意,只当是偶然风起所带来的。可是,渐渐地我发现情况简直令人吃惊。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些树仍旧浑然不觉地在飘送那些小型的云朵,倒好像是一座无限的云库似的。整个下午,整个晚上漫天都是那种东西。第二天的情形完全一样,我感到诧异和震撼。其实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有一类种子是靠风力吹动纤维播送的。但也只是知道一道测验题的答案而已,那几天真的看到了,满心所感到的是一种折服——一种无以名状的敬畏。我几乎是第一次遇见生命——虽然是植物的。我感到那云状的种子在我心底强烈地碰撞上什么东西。我不能不被生命豪华的、奢侈的、不计成本的投资所感动。也许,在不分昼夜的飘散之余,只有一颗种子足以成树,但造物主乐于做这样惊心动魄的壮举。我至今仍然在沉思之际想起那一片柔媚的湖水,不知湖畔那群种子中有哪一颗成了小树。至少,我知道,有一颗已经成长。那颗种子曾遇见了一片土地,在一个过客的心之峡谷里蔚然成荫,教会她怎样敬畏生命。生和死浇铸的雕像叶楠烟花三月,在我国江南,已经进入春光旖旎的盛春了,而在北方边陲,则另是一番景象。在那里,春天似乎还在遥远的地方逡巡……有一年,就是在农历三月,我到了大兴安岭北麓。那里仍然是冰封雪覆,严冬依然盘踞在冻土原上,不肯离去。空中的太阳,似乎也是冰冷的。森林中一片死寂,好像万物在严寒狞厉的威势下,连叹息都不敢地蛰伏着。只是偶尔遇到一只狍子,在林隙里,蹒跚地奔跑;或者见到一只羽毛蓬乱的飞龙,在地上,费力地用喙敲击坚硬的积雪,想找到哪怕是发霉的干瘪的越橘或草莓的果实。它们饿坏了,连鸣叫的力气也没有。一个清晨,我突然在积雪的林地中,看到一星飘动的蓝色的火苗。走到它的近旁,才看出这是一朵很小的花儿,蓝色的,像铃铛,口朝着天,由纤细的孱弱的茎挑起,在凛冽的风中颤抖,像一面傲然挺立向严寒挑战的战旗。我感到震惊。这么弱小的生命,竟能从坚硬的冻土和积雪中,挣扎出来,在万物都还在沉睡的时候。这是一株草本植物,名字叫白头翁,是我后来从林学家那里知道的。我蹲下来仔细看看这勇敢的生命,这时,我才发现,它蝉翼般的花瓣还抱着一只蜜蜂,那蜜蜂就像婴儿安稳地睡在摇篮里。再仔细一看,蜜蜂已经僵死了,显然是冻死的,蓝色的花朵哪里是它的摇篮?实则是它的殓床!它定是嗅到花儿的气息,不顾彻骨的寒冷,摇摇晃晃飞来,扑向花心,然后死去的。它是为了迎接春天而死的,它是为生而死去的。我感到浑身发冷,我感到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几天以后的一个夜晚,我被一种巨大的声响——宛如大地在叹息——惊醒了。随之而来的,是如海浪拍岸的声响。我飞速地披上棉袄跑出去,就听见像珠玉碰撞发出的响动,叮咚不息。这是我客居的村庄旁边的一条细小的冷水河开河了,在星光下,河上迸射出晶莹的光辉。清晨,就在刚刚解冻的小河边,杜鹃红了,那新艳的红,被残存的冰雪的洁白,映衬得异常娇丽。它们是一夜之间红的,像是被解冻的冰河的响动所惊醒,连夜匆匆梳洗、涂上脂粉,展现在寂寞了一个漫长冬天的冻原上,给满目冷色调添了星星点点醒目的暖色。它们还没抽出叶芽,就绽开了花朵,像是没披上衣裙,就急忙显露嫣红的面颊,来迎接冻原上姗姗来迟的春天。在杜鹃后面,是越桔、草莓、稠李子、山汀子……数不清的草木,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像是结队浓妆艳抹的仕女,联袂拥上大兴安岭广阔的舞台。刚刚解冻的水泡子里,首先出现的是黄绒绒的雏野鸭和它们的双亲,它们像编队巡航的舰队,在浮冰中悠悠游弋。你根本不知道老野鸭是什么时候,从温暖的南国飞回来的,也不知道它们在什么地方孵出的雏鸭来。真是“水暖鸭先知”,它们是候鸟的先导,不几日,无数各式各样的候鸟结伴归来了。花儿姹紫嫣红,鸟儿飞舞鸣啭,连衽成纬,繁弦急管,寂寥的千峰万壑,突然变得喧闹了起来。春天来了!以往,我总认为春天是突然来临的,是自自然然来临的。现在,我知道,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