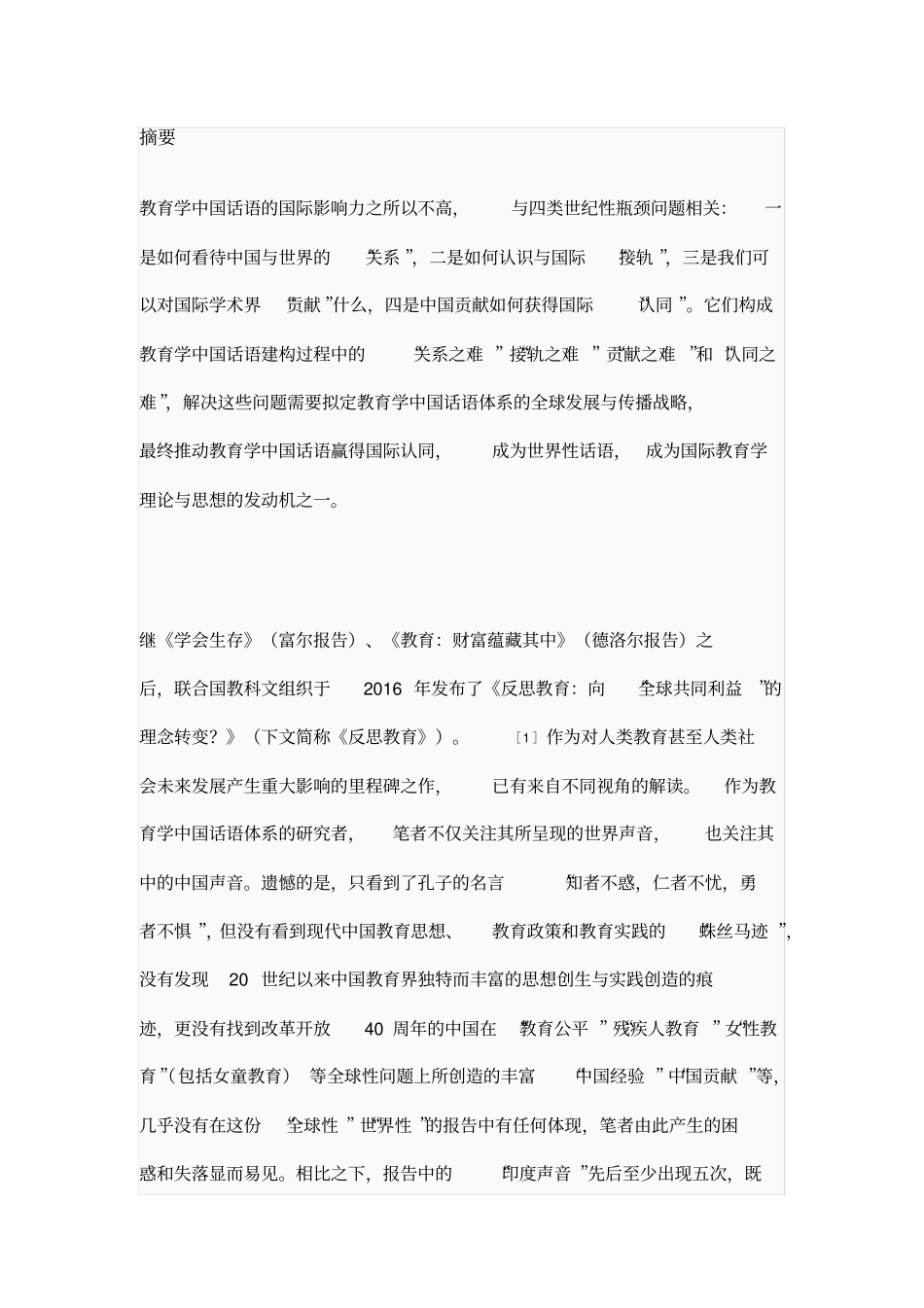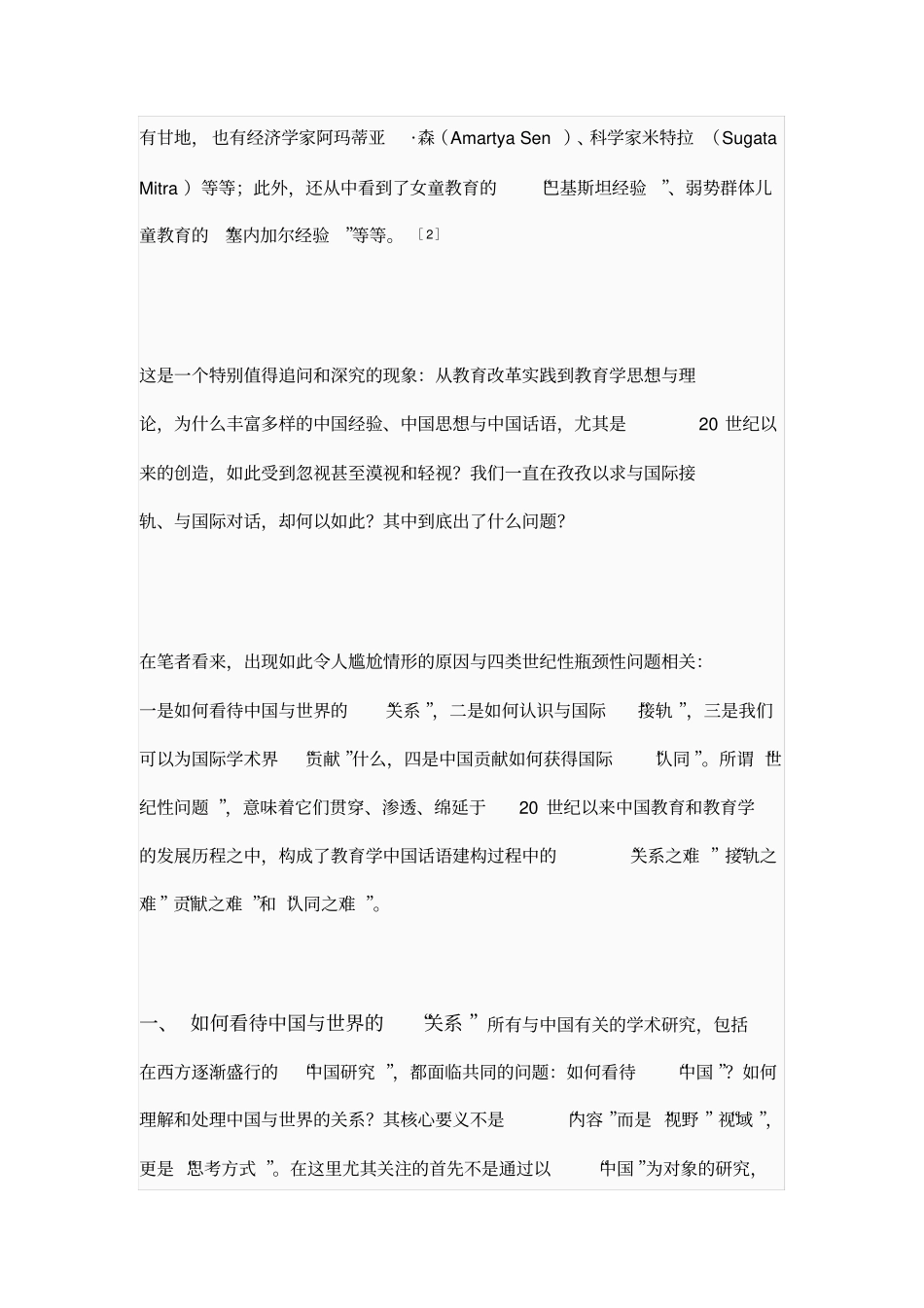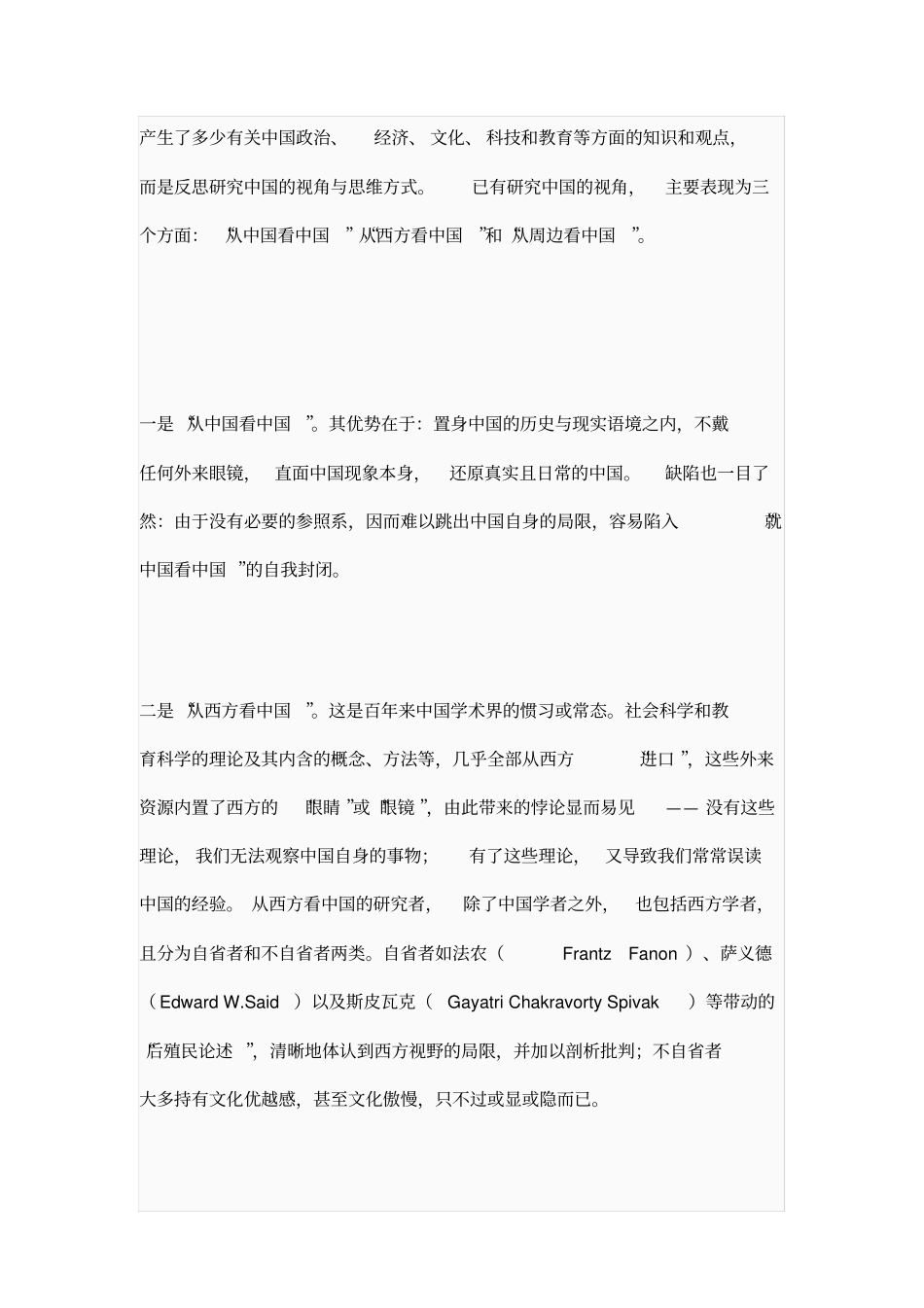摘要教育学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之所以不高,与四类世纪性瓶颈问题相关:一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二是如何认识与国际“接轨 ”,三是我们可以对国际学术界“贡献 ”什么,四是中国贡献如何获得国际“认同 ”。它们构成教育学中国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关系之难 ”“接轨之难 ”“贡献之难 ”和 “认同之难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拟定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全球发展与传播战略,最终推动教育学中国话语赢得国际认同,成为世界性话语,成为国际教育学理论与思想的发动机之一。继《学会生存》(富尔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德洛尔报告)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6 年发布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下文简称《反思教育》)。[ 1 ]作为对人类教育甚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里程碑之作,已有来自不同视角的解读。作为教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研究者,笔者不仅关注其所呈现的世界声音,也关注其中的中国声音。遗憾的是,只看到了孔子的名言“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但没有看到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蛛丝马迹 ”,没有发现20 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界独特而丰富的思想创生与实践创造的痕迹,更没有找到改革开放40 周年的中国在“教育公平 ”“残疾人教育 ”“女性教育 ”(包括女童教育) 等全球性问题上所创造的丰富“中国经验 ”“中国贡献 ”等,几乎没有在这份“全球性 ”“世界性 ”的报告中有任何体现,笔者由此产生的困惑和失落显而易见。相比之下,报告中的“印度声音 ”先后至少出现五次,既有甘地, 也有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科学家米特拉 (Sugata Mitra )等等;此外,还从中看到了女童教育的“巴基斯坦经验”、弱势群体儿童教育的 “塞内加尔经验”等等。 [ 2]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追问和深究的现象:从教育改革实践到教育学思想与理论,为什么丰富多样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与中国话语,尤其是20 世纪以来的创造,如此受到忽视甚至漠视和轻视?我们一直在孜孜以求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对话,却何以如此?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笔者看来,出现如此令人尴尬情形的原因与四类世纪性瓶颈性问题相关:一是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二是如何认识与国际“接轨 ”,三是我们可以为国际学术界“贡献 ”什么,四是中国贡献如何获得国际“认同 ”。所谓 “世纪性问题 ”,意味着它们贯穿、渗透、绵延于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