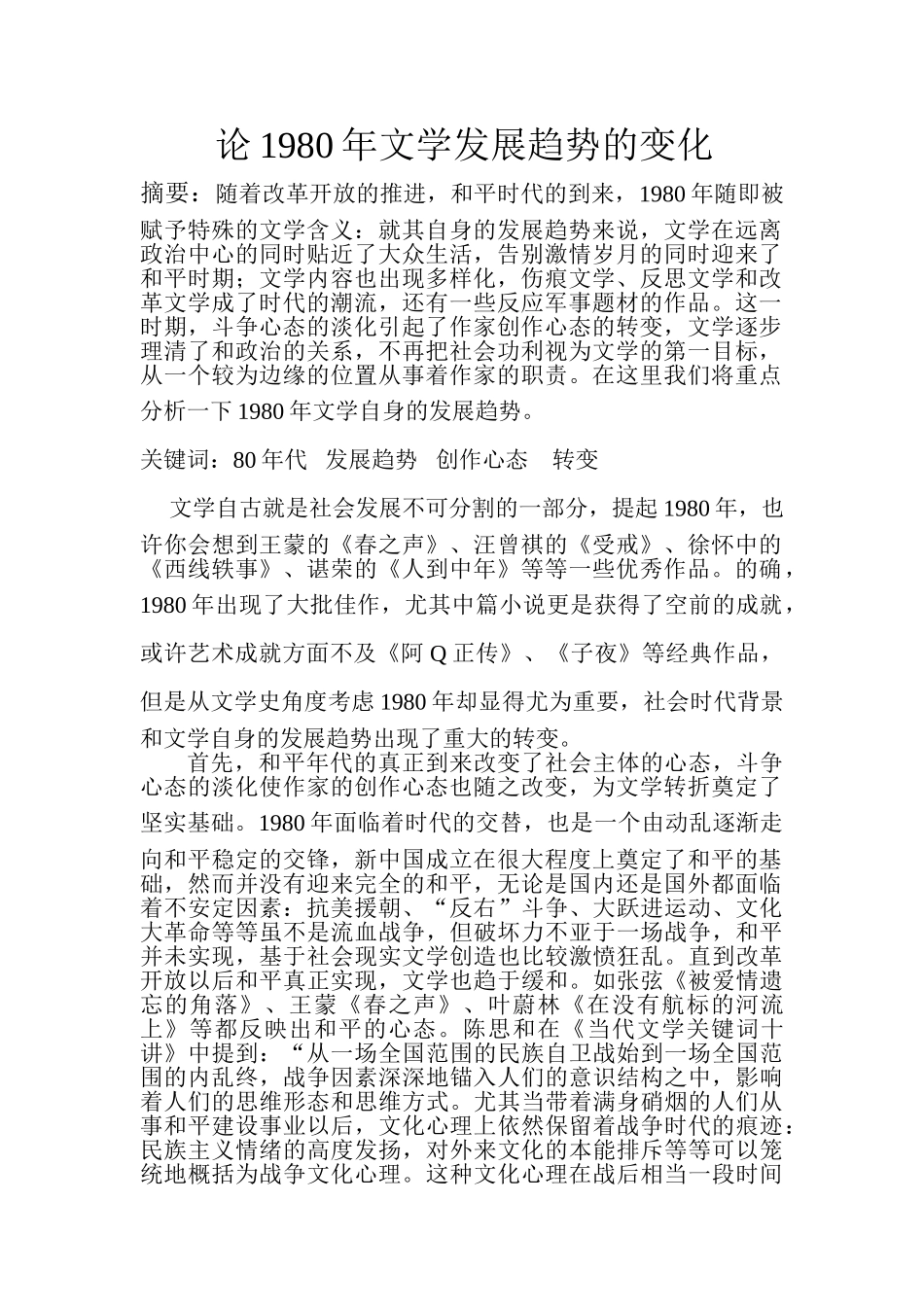论1980年文学发展趋势的变化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平时代的到来,1980年随即被赋予特殊的文学含义:就其自身的发展趋势来说,文学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同时贴近了大众生活,告别激情岁月的同时迎来了和平时期;文学内容也出现多样化,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成了时代的潮流,还有一些反应军事题材的作品。这一时期,斗争心态的淡化引起了作家创作心态的转变,文学逐步理清了和政治的关系,不再把社会功利视为文学的第一目标,从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从事着作家的职责。在这里我们将重点分析一下1980年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关键词:80年代发展趋势创作心态转变文学自古就是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起1980年,也许你会想到王蒙的《春之声》、汪曾祺的《受戒》、徐怀中的《西线轶事》、谌荣的《人到中年》等等一些优秀作品。的确,1980年出现了大批佳作,尤其中篇小说更是获得了空前的成就,或许艺术成就方面不及《阿Q正传》、《子夜》等经典作品,但是从文学史角度考虑1980年却显得尤为重要,社会时代背景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首先,和平年代的真正到来改变了社会主体的心态,斗争心态的淡化使作家的创作心态也随之改变,为文学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1980年面临着时代的交替,也是一个由动乱逐渐走向和平稳定的交锋,新中国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和平的基础,然而并没有迎来完全的和平,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面临着不安定因素:抗美援朝、“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虽不是流血战争,但破坏力不亚于一场战争,和平并未实现,基于社会现实文学创造也比较激愤狂乱。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和平真正实现,文学也趋于缓和。如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王蒙《春之声》、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等都反映出和平的心态。陈思和在《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中提到:“从一场全国范围的民族自卫战始到一场全国范围的内乱终,战争因素深深地锚入人们的意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形态和思维方式。尤其当带着满身硝烟的人们从事和平建设事业以后,文化心理上依然保留着战争时代的痕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度发扬,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排斥等等可以笼统地概括为战争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其实陈思和先生所说的这种战争文化心理最根本的就是一种紧张的斗争心态,如:抗击外族入侵、国内革命战争、各种政治运动、甚至包含与天争胜等,恰恰是这种心态造就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激情文学,可以说这种心态影响了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主流文学。五六十年代整个民族处于极不正常的“红色恐怖”时代,文学也难以幸免,红色的狂热使作家无法安定的写作,只能盲目的图解政治。“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的时代,改革文学成为时代主潮之一,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张锲《改革者》、张一弓《赵镢头的遗嘱》、水运宪《祸起萧墙》等都给人以启蒙思想。对比一下“文革”时期的狂乱,1979年的批判,1980年文学显得风和日丽了许多,和平建设成为时代的主题。其次,文学功能的转折—审美意蕴的重视。十九世纪末,文学被赋予“启蒙”与“救亡”的重任。从梁启超开始就强调小说的社会功能,只言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是以社会功效为标准的,“欲行一国之民,必先行一国之小说”,这本是极夸张的说法,但在那个国势衰败,民族危难的情况下,却赢得广泛认同,文人们纷纷响应且以启蒙者自居。文学渐渐偏离了最本质的轨道,审美意味越来越淡薄,谢冕在《百年中国文学系统:总序一》中指出百年中国文学有三点不足:“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力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其中“重功力而轻审美”可算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恰当论断。20世纪文学在颠覆传统的同时也是自己走上异化,审美意识严重缺失,文学功能单一化,这一时期改革小说隆重出场,1979年7月蒋子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乔厂长上任记》,塑造了乔光朴这一改革英雄形象,但和当时文学相似的是依然是依靠其社会影响轰动的文坛,其美学价值并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秦兆阳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题为《断丝碎缕录》的文章含蓄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小说没能描绘出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