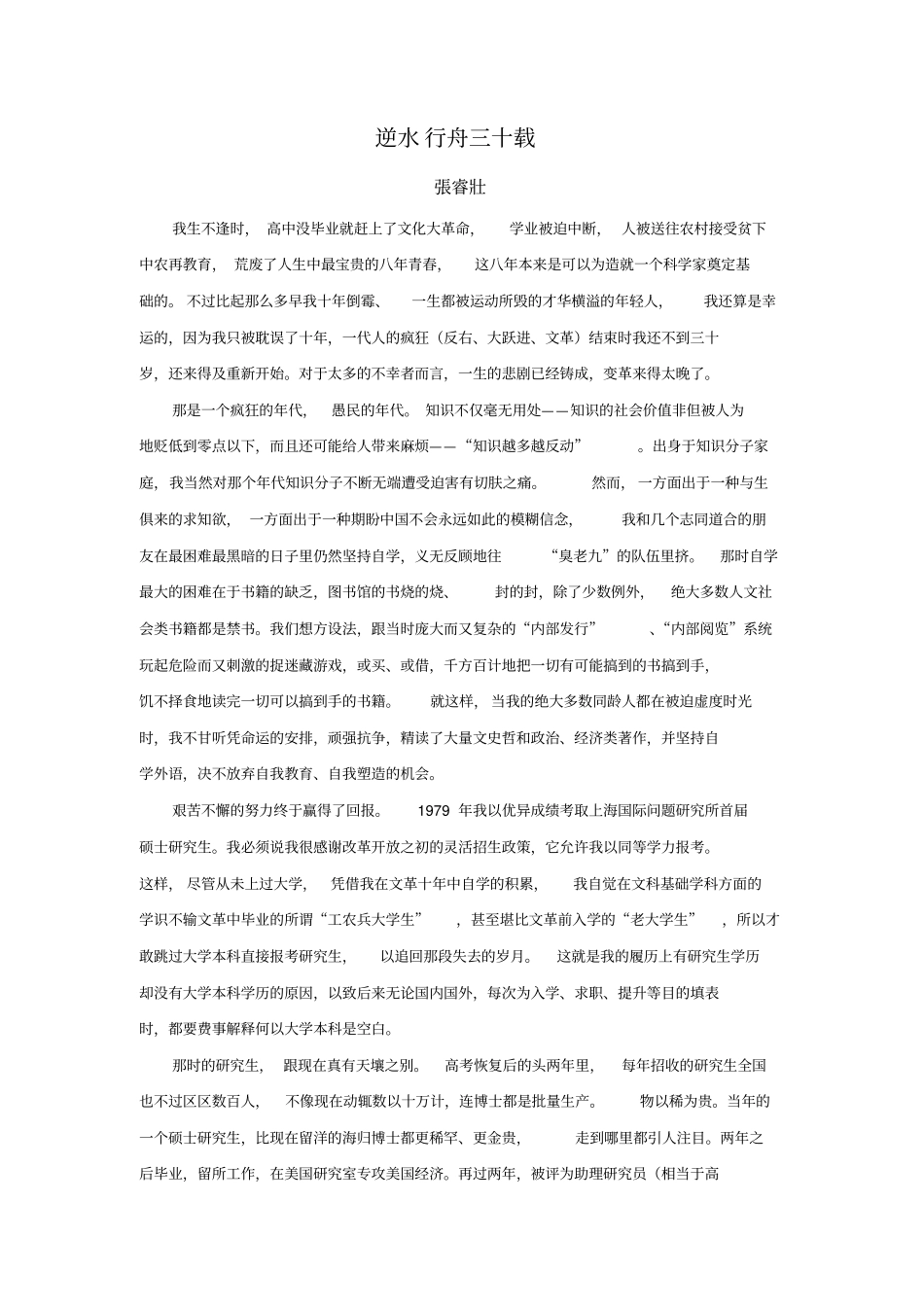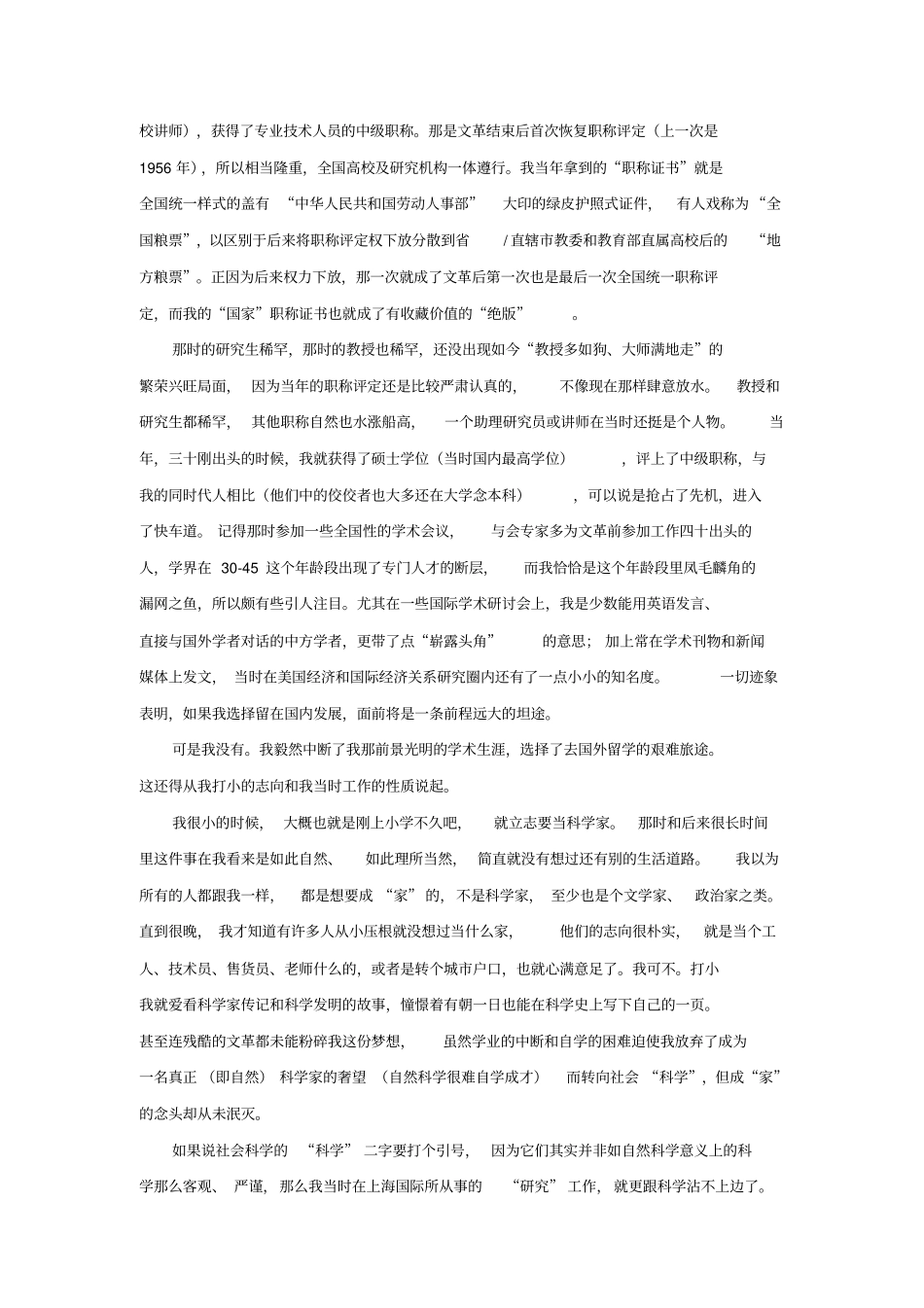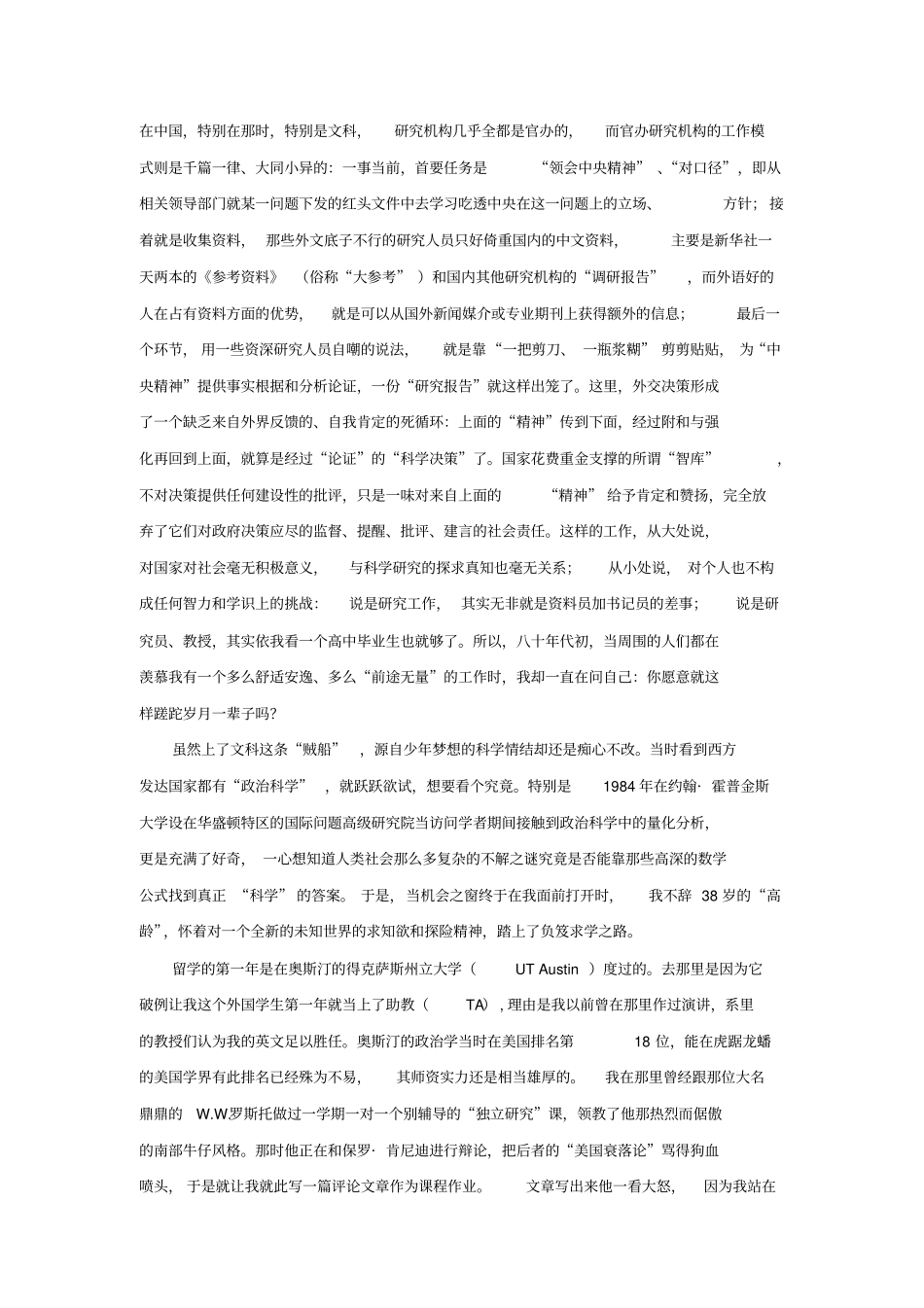逆水 行舟三十载張睿壯我生不逢时, 高中没毕业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业被迫中断, 人被送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荒废了人生中最宝贵的八年青春,这八年本来是可以为造就一个科学家奠定基础的。 不过比起那么多早我十年倒霉、一生都被运动所毁的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我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我只被耽误了十年,一代人的疯狂(反右、大跃进、文革)结束时我还不到三十岁,还来得及重新开始。对于太多的不幸者而言,一生的悲剧已经铸成,变革来得太晚了。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愚民的年代。 知识不仅毫无用处——知识的社会价值非但被人为地贬低到零点以下,而且还可能给人带来麻烦——“知识越多越反动”。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我当然对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不断无端遭受迫害有切肤之痛。然而, 一方面出于一种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一方面出于一种期盼中国不会永远如此的模糊信念,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仍然坚持自学,义无反顾地往“臭老九”的队伍里挤。那时自学最大的困难在于书籍的缺乏,图书馆的书烧的烧、封的封,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人文社会类书籍都是禁书。我们想方设法,跟当时庞大而又复杂的“内部发行”、“内部阅览”系统玩起危险而又刺激的捉迷藏游戏,或买、或借,千方百计地把一切有可能搞到的书搞到手,饥不择食地读完一切可以搞到手的书籍。就这样, 当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在被迫虚度时光时,我不甘听凭命运的安排,顽强抗争,精读了大量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著作,并坚持自学外语,决不放弃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机会。艰苦不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回报。1979 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首届硕士研究生。我必须说我很感谢改革开放之初的灵活招生政策,它允许我以同等学力报考。这样, 尽管从未上过大学,凭借我在文革十年中自学的积累,我自觉在文科基础学科方面的学识不输文革中毕业的所谓“工农兵大学生”,甚至堪比文革前入学的“老大学生”,所以才敢跳过大学本科直接报考研究生,以追回那段失去的岁月。这就是我的履历上有研究生学历却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原因,以致后来无论国内国外,每次为入学、求职、提升等目的填表时,都要费事解释何以大学本科是空白。那时的研究生, 跟现在真有天壤之别。高考恢复后的头两年里,每年招收的研究生全国也不过区区数百人,不像现在动辄数以十万计,连博士都是批量生产。物以稀为贵。当年的一个硕士研究生,比现在留洋的海归博士都更稀罕、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