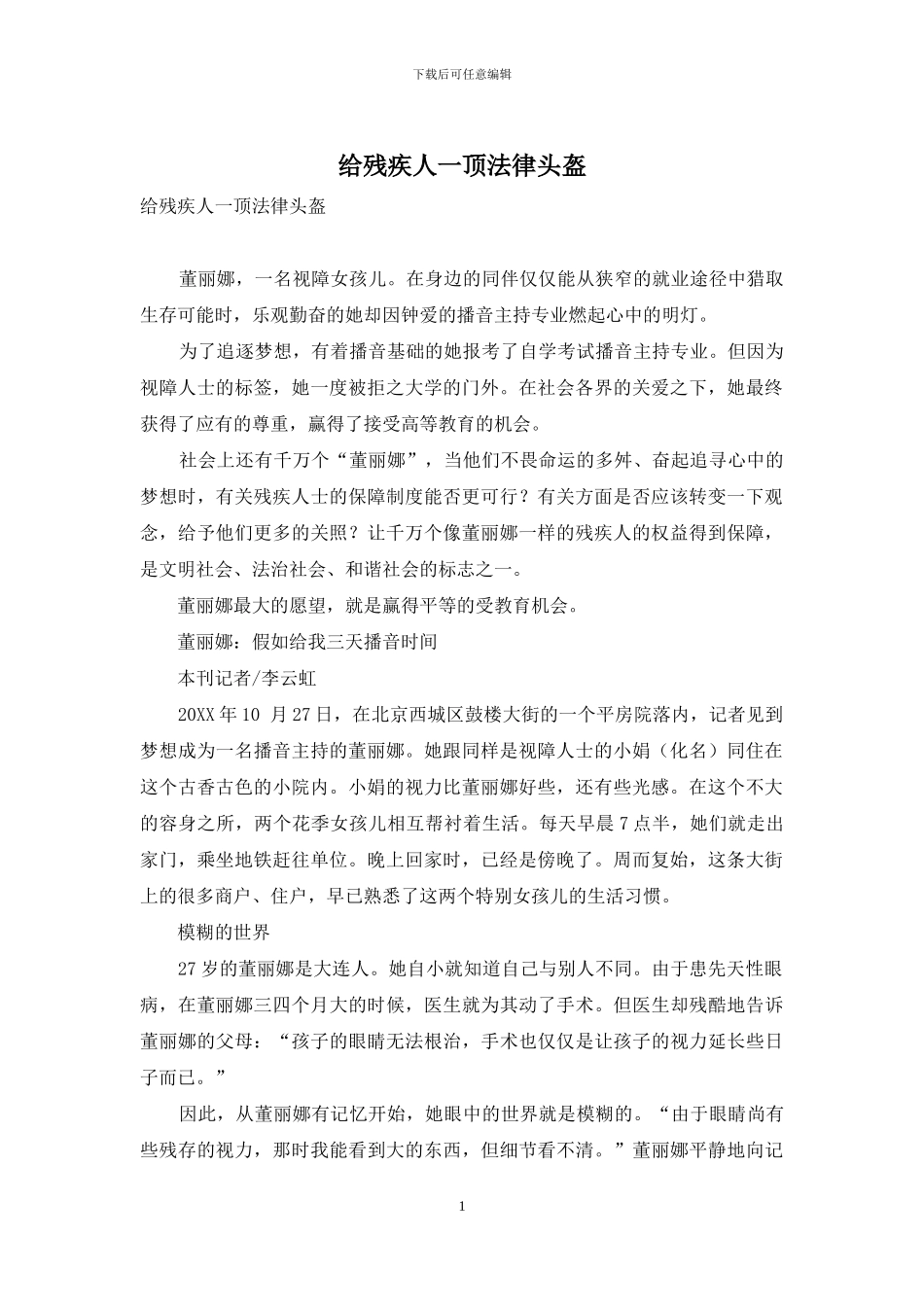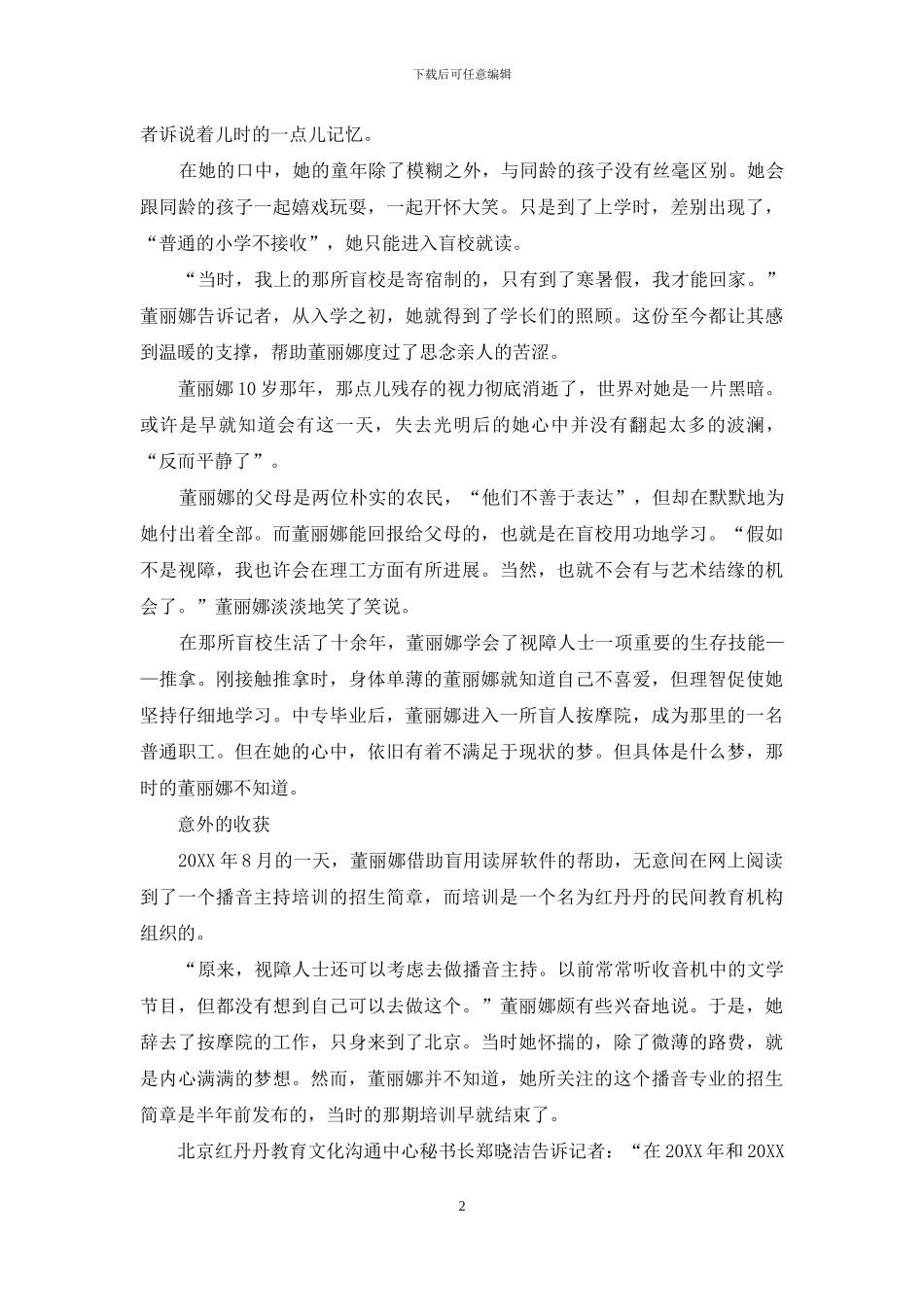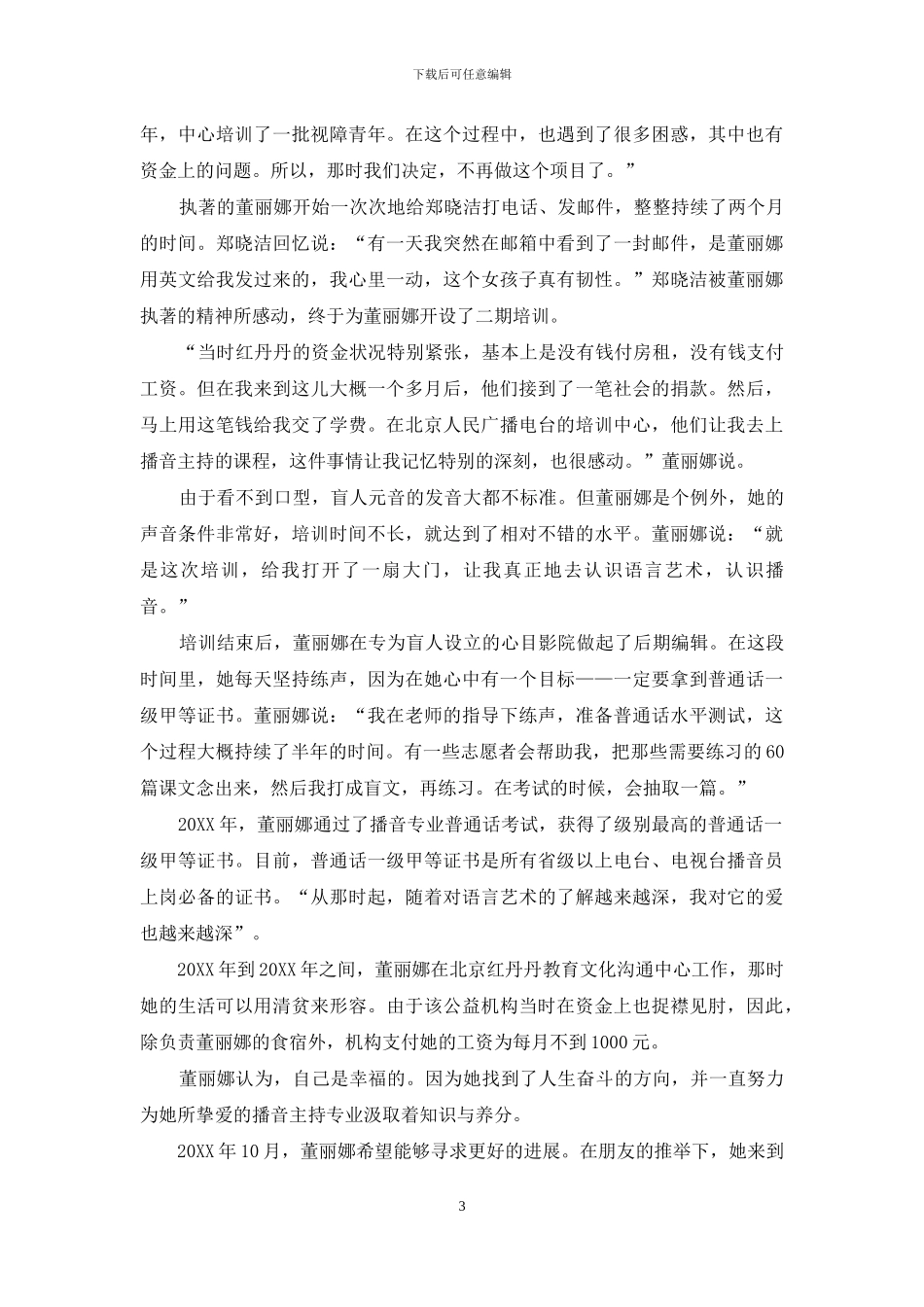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给残疾人一顶法律头盔给残疾人一顶法律头盔 董丽娜,一名视障女孩儿。在身边的同伴仅仅能从狭窄的就业途径中猎取生存可能时,乐观勤奋的她却因钟爱的播音主持专业燃起心中的明灯。 为了追逐梦想,有着播音基础的她报考了自学考试播音主持专业。但因为视障人士的标签,她一度被拒之大学的门外。在社会各界的关爱之下,她最终获得了应有的尊重,赢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社会上还有千万个“董丽娜”,当他们不畏命运的多舛、奋起追寻心中的梦想时,有关残疾人士的保障制度能否更可行?有关方面是否应该转变一下观念,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让千万个像董丽娜一样的残疾人的权益得到保障,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标志之一。 董丽娜最大的愿望,就是赢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董丽娜:假如给我三天播音时间 本刊记者/李云虹 20XX 年 10 月 27 日,在北京西城区鼓楼大街的一个平房院落内,记者见到梦想成为一名播音主持的董丽娜。她跟同样是视障人士的小娟(化名)同住在这个古香古色的小院内。小娟的视力比董丽娜好些,还有些光感。在这个不大的容身之所,两个花季女孩儿相互帮衬着生活。每天早晨 7 点半,她们就走出家门,乘坐地铁赶往单位。晚上回家时,已经是傍晚了。周而复始,这条大街上的很多商户、住户,早已熟悉了这两个特别女孩儿的生活习惯。 模糊的世界 27 岁的董丽娜是大连人。她自小就知道自己与别人不同。由于患先天性眼病,在董丽娜三四个月大的时候,医生就为其动了手术。但医生却残酷地告诉董丽娜的父母:“孩子的眼睛无法根治,手术也仅仅是让孩子的视力延长些日子而已。” 因此,从董丽娜有记忆开始,她眼中的世界就是模糊的。“由于眼睛尚有些残存的视力,那时我能看到大的东西,但细节看不清。”董丽娜平静地向记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者诉说着儿时的一点儿记忆。 在她的口中,她的童年除了模糊之外,与同龄的孩子没有丝毫区别。她会跟同龄的孩子一起嬉戏玩耍,一起开怀大笑。只是到了上学时,差别出现了,“普通的小学不接收”,她只能进入盲校就读。 “当时,我上的那所盲校是寄宿制的,只有到了寒暑假,我才能回家。”董丽娜告诉记者,从入学之初,她就得到了学长们的照顾。这份至今都让其感到温暖的支撑,帮助董丽娜度过了思念亲人的苦涩。 董丽娜 10 岁那年,那点儿残存的视力彻底消逝了,世界对她是一片黑暗。或许是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失去光明后的她心中并没有翻起太多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