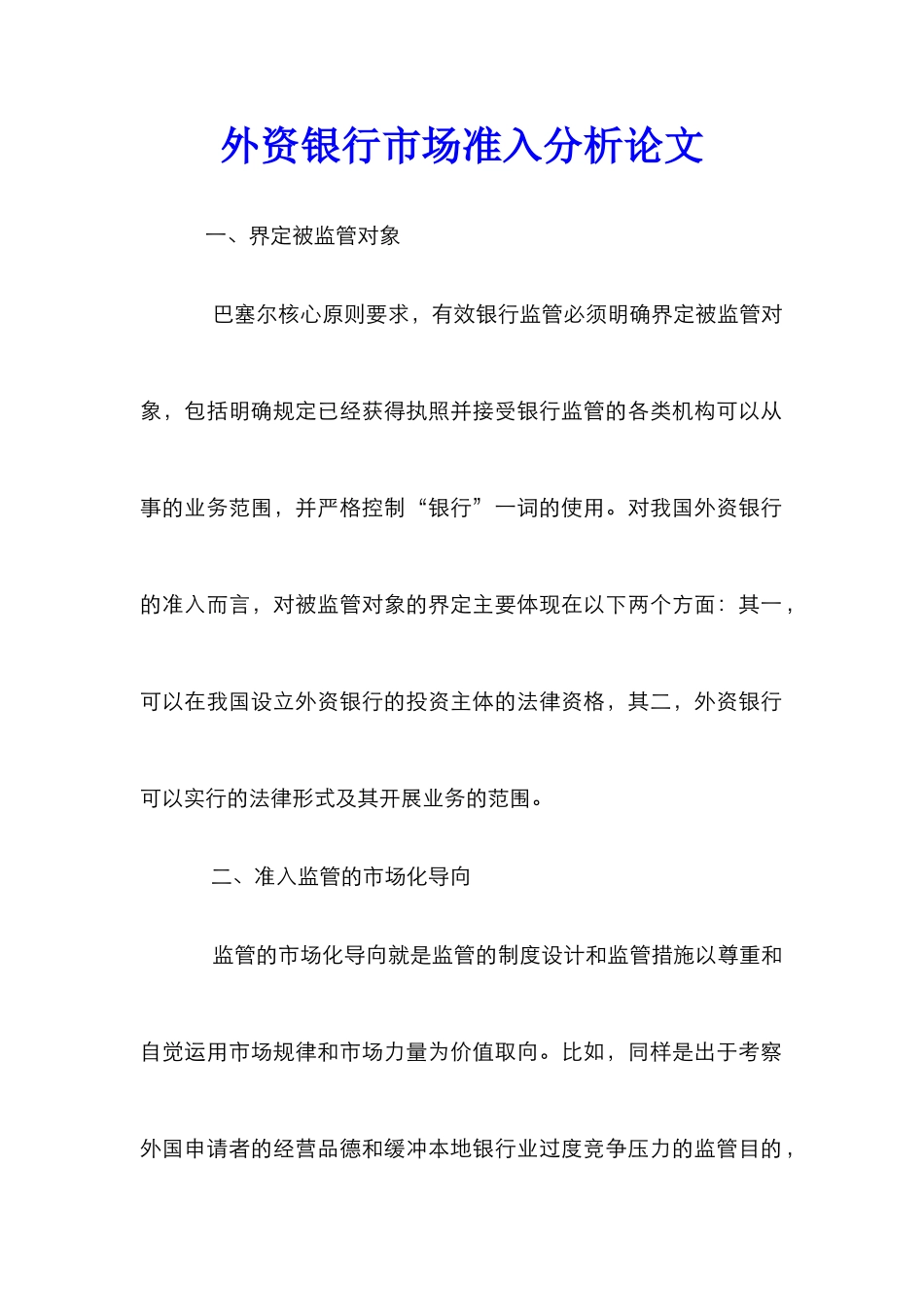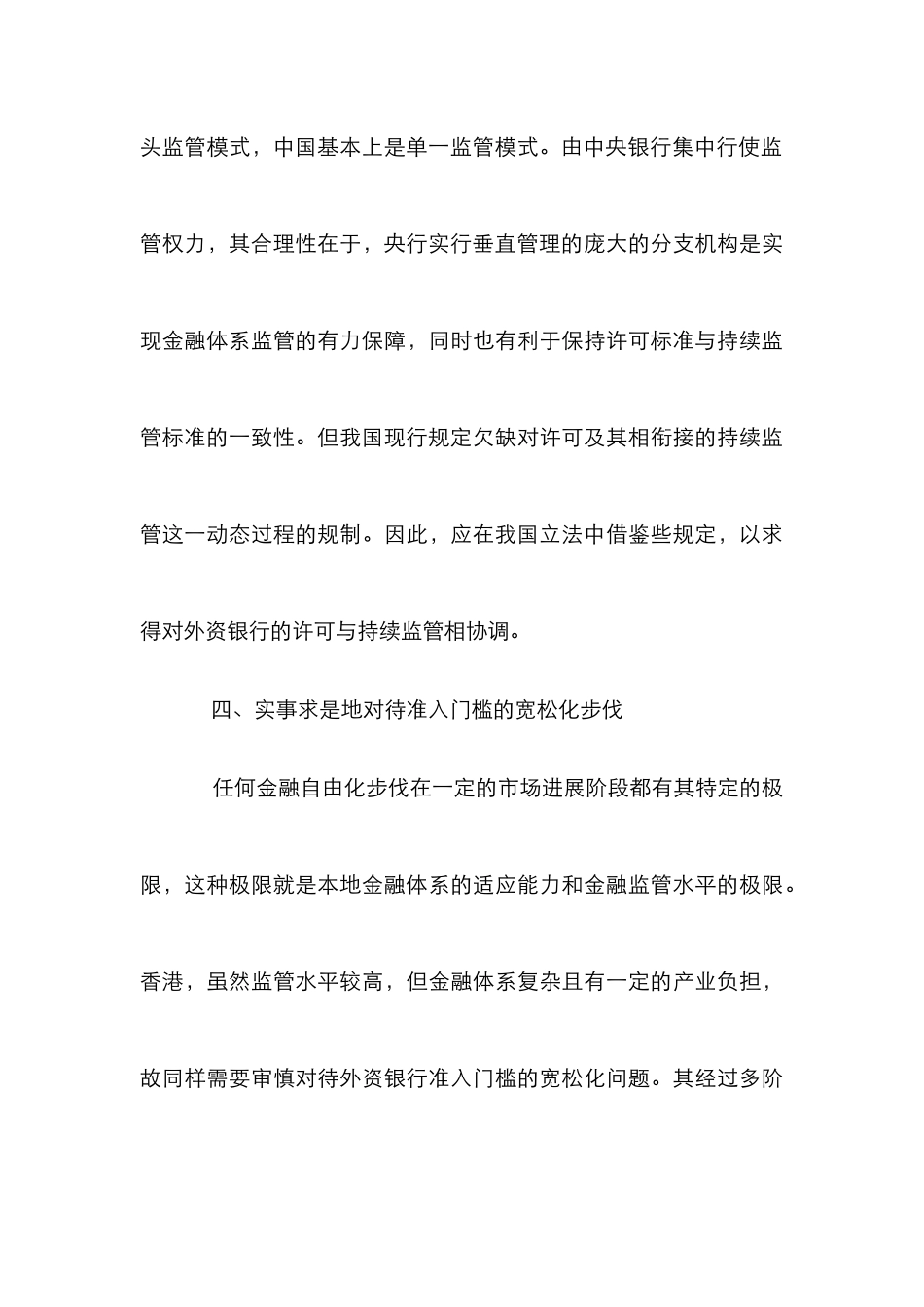外资银行市场准入分析论文 一、界定被监管对象 巴塞尔核心原则要求,有效银行监管必须明确界定被监管对象,包括明确规定已经获得执照并接受银行监管的各类机构可以从事的业务范围,并严格控制“银行”一词的使用。对我国外资银行的准入而言,对被监管对象的界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可以在我国设立外资银行的投资主体的法律资格,其二,外资银行可以实行的法律形式及其开展业务的范围。 二、准入监管的市场化导向 监管的市场化导向就是监管的制度设计和监管措施以尊重和自觉运用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为价值取向。比如,同样是出于考察外国申请者的经营品德和缓冲本地银行业过度竞争压力的监管目的,香港用逐步提升申请者在本地设立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格的办法(由注册存款公司后至限制持牌银行再至持牌银行),内地实行“一刀切”地让申请者设立办事处或者代表处等待一定期限的办法。前者注重从申请者在本地市场竞争中的经营表现来考察其品德,后者消极地关注申请者排队等待的时间。我们虽不能因此就推断哪一种办法更趋国际化,但哪一个更具备市场化导向和更有绩效显而易见。 三、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一致 鉴于在一些国家,对银行的许可发照和持续监督由不同的部门负责,有效银行监管不仅应当建立明确而客观的许可标准,而且还应保证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相一致。这样,当一家既存机构不再符合标准时,就可据此吊销其执照。 一般而言,金融监管大致分两种模式,即单一监管模式和多头监管模式,中国基本上是单一监管模式。由中央银行集中行使监管权力,其合理性在于,央行实行垂直管理的庞大的分支机构是实现金融体系监管的有力保障,同时也有利于保持许可标准与持续监管标准的一致性。但我国现行规定欠缺对许可及其相衔接的持续监管这一动态过程的规制。因此,应在我国立法中借鉴些规定,以求得对外资银行的许可与持续监管相协调。 四、实事求是地对待准入门槛的宽松化步伐 任何金融自由化步伐在一定的市场进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本地金融体系的适应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的极限。香港,虽然监管水平较高,但金融体系复杂且有一定的产业负担,故同样需要审慎对待外资银行准入门槛的宽松化问题。其经过多阶段的分步放开,直至 2024 年才最终取消了海外申请者在资本实力方面的特别要求以及取消“三家分行限制”,就是审慎对待准入门槛宽松化的明证。内地目前对外资银行的准入门槛主要体现在对申请者资本实力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