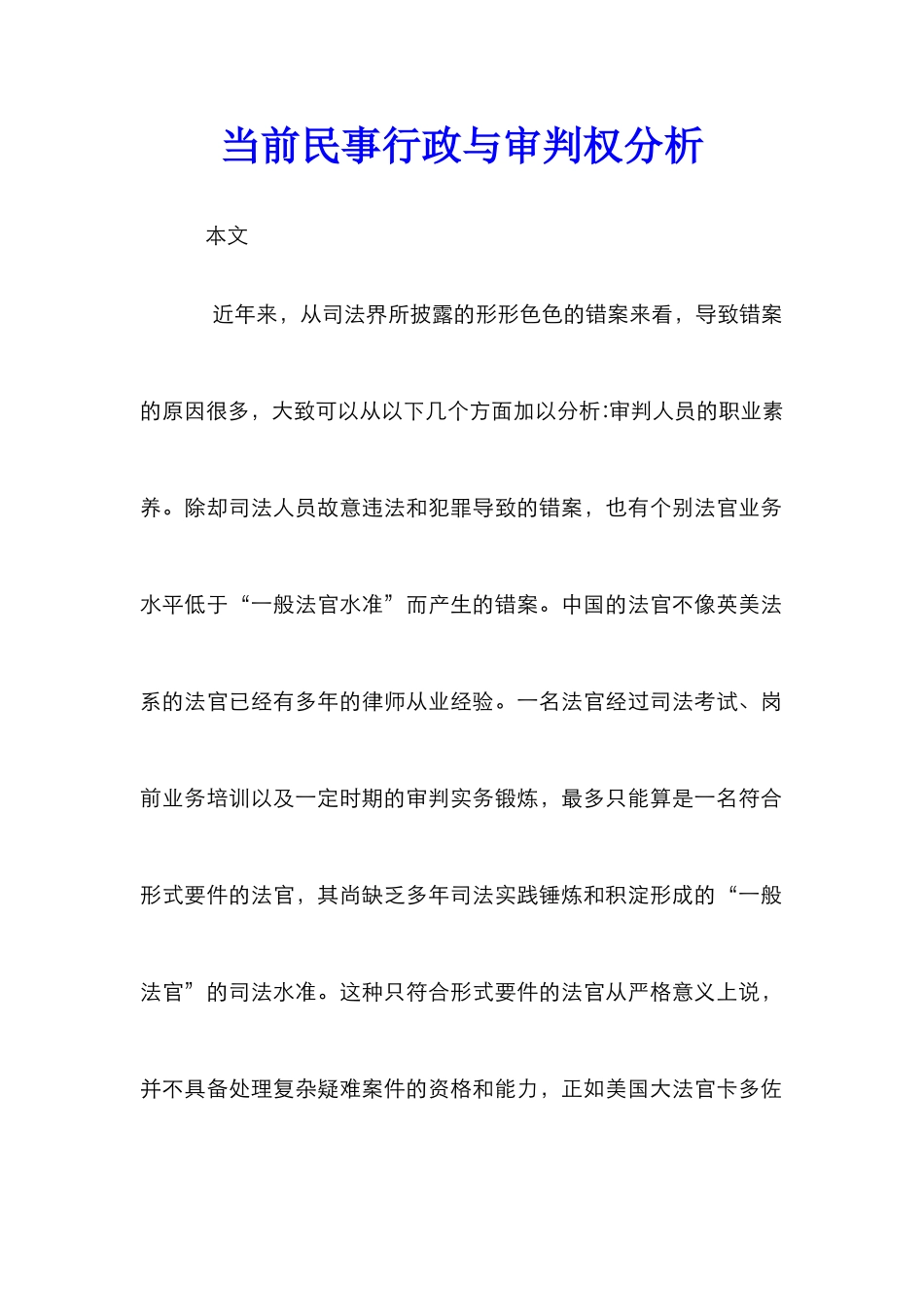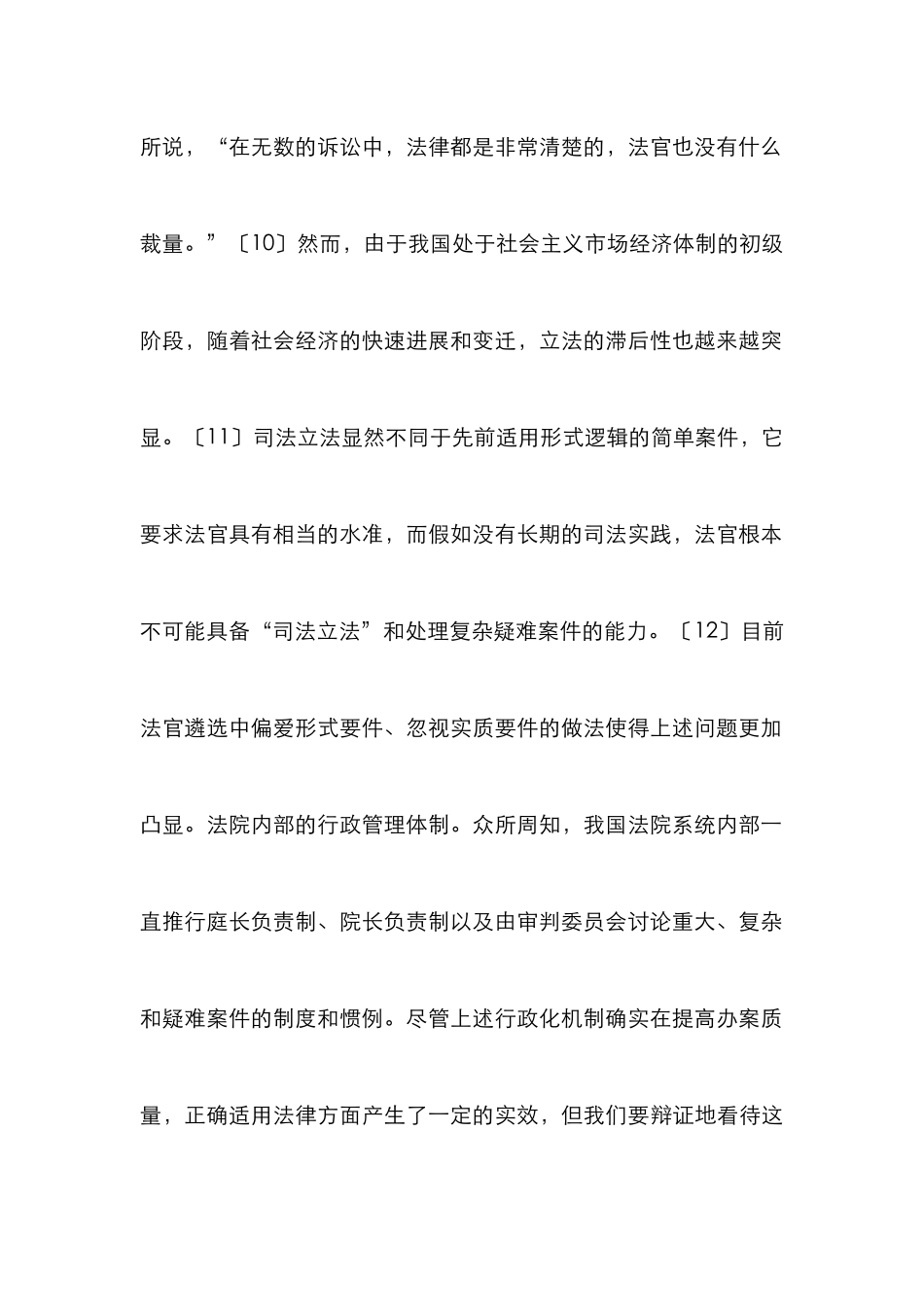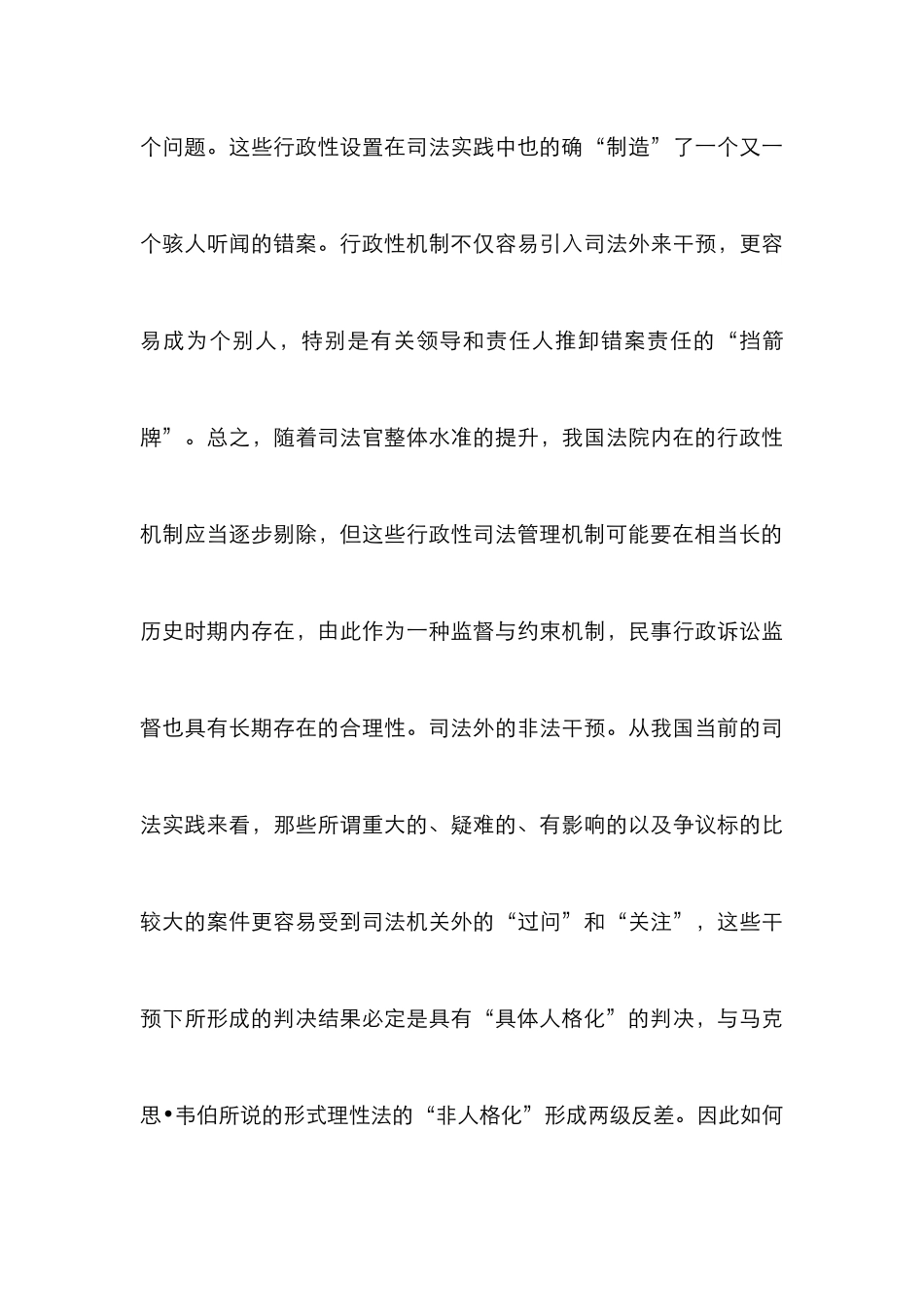当前民事行政与审判权分析 本文 近年来,从司法界所披露的形形色色的错案来看,导致错案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审判人员的职业素养。除却司法人员故意违法和犯罪导致的错案,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一般法官水准”而产生的错案。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10〕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进展和变迁,立法的滞后性也越来越突显。〔11〕司法立法显然不同于先前适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案件,它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水准,而假如没有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官根本不可能具备“司法立法”和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系统内部一直推行庭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以及由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的制度和惯例。尽管上述行政化机制确实在提高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行政性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错案。行政性机制不仅容易引入司法外来干预,更容易成为个别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和责任人推卸错案责任的“挡箭牌”。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外的非法干预。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那些所谓重大的、疑难的、有影响的以及争议标的比较大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司法机关外的“过问”和“关注”,这些干预下所形成的判决结果必定是具有“具体人格化”的判决,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的“非人格化”形成两级反差。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权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退一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