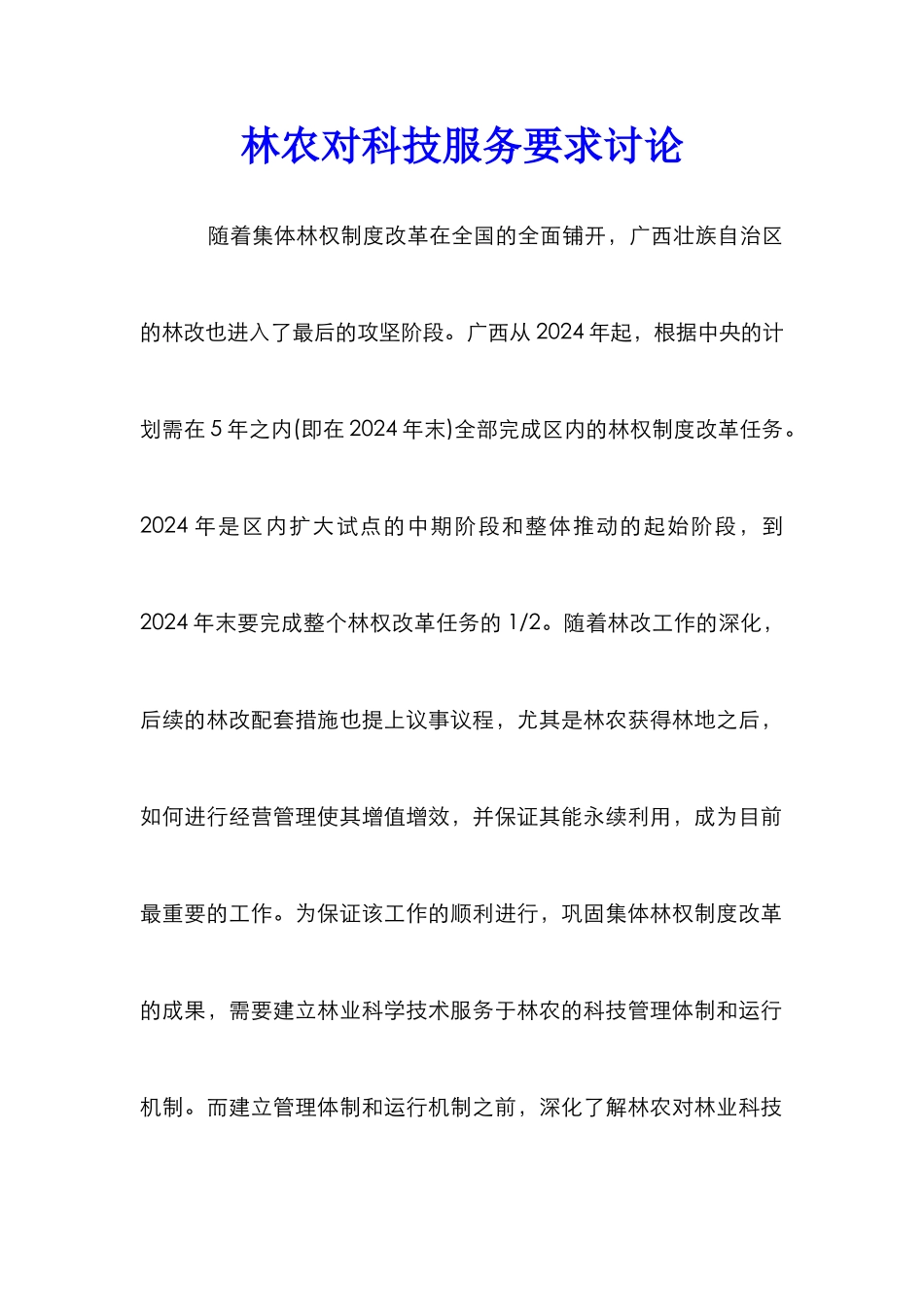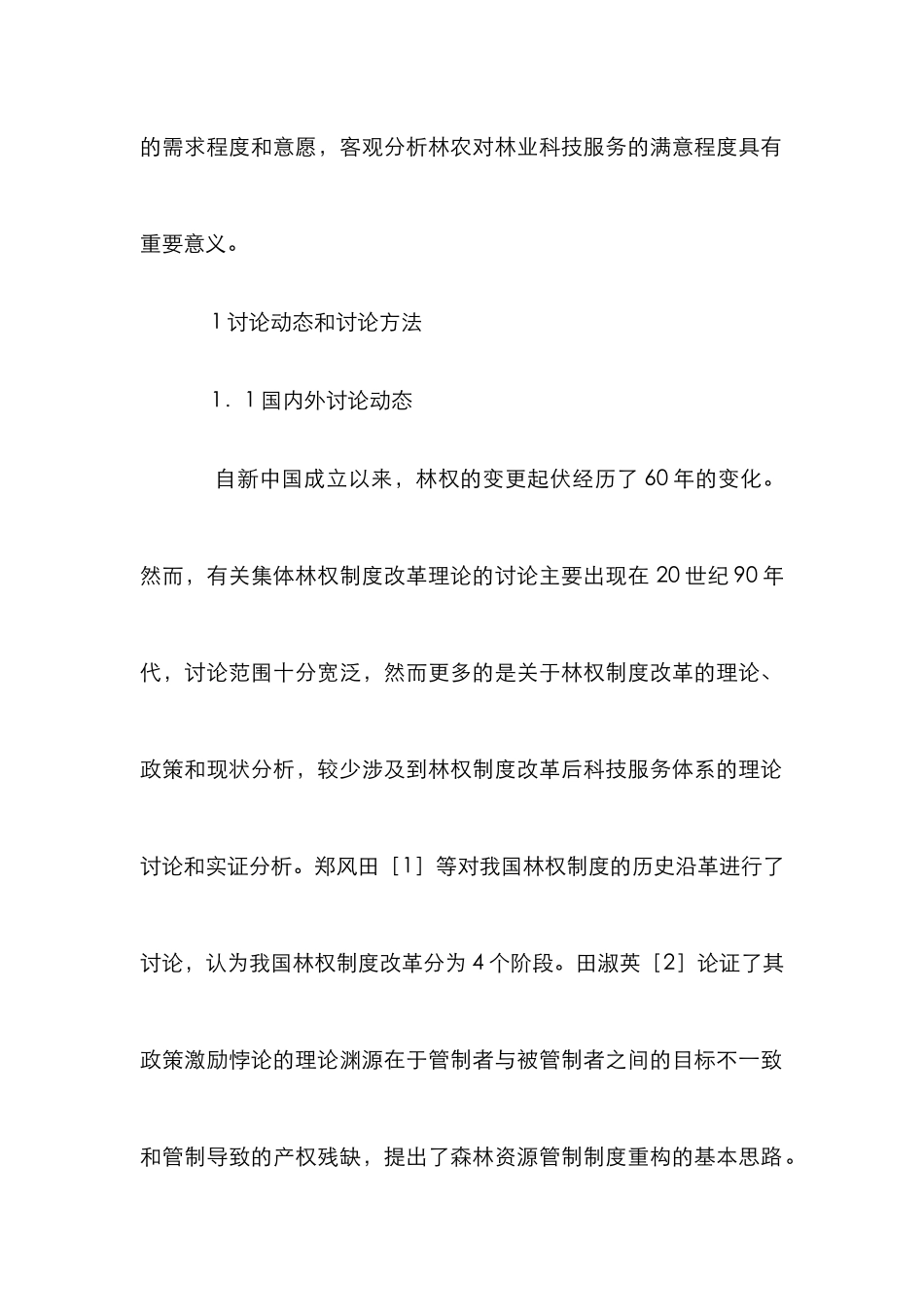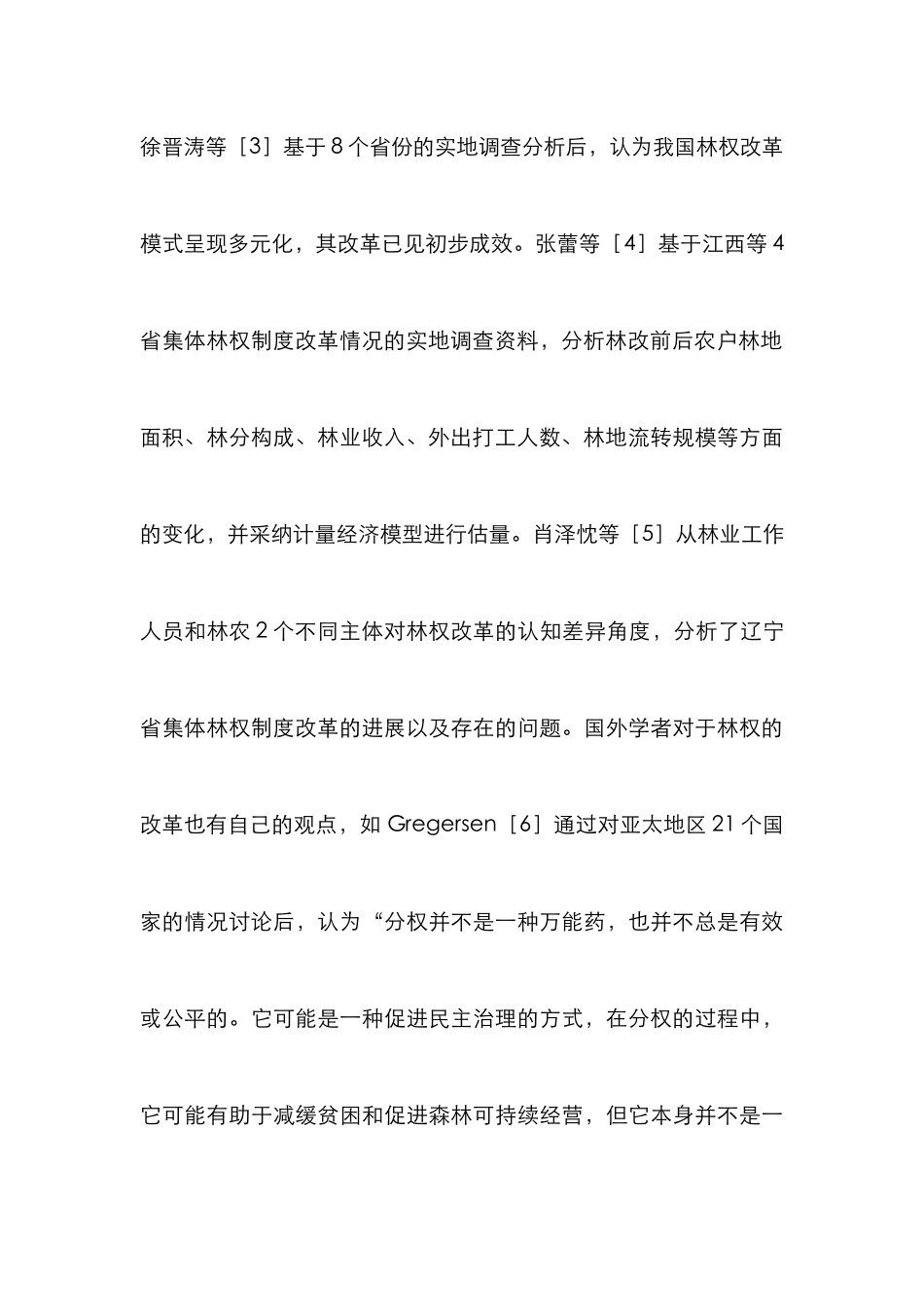林农对科技服务要求讨论 随着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在全国的全面铺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林改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广西从 2024 年起,根据中央的计划需在 5 年之内(即在 2024 年末)全部完成区内的林权制度改革任务。2024 年是区内扩大试点的中期阶段和整体推动的起始阶段,到2024 年末要完成整个林权改革任务的 1/2。随着林改工作的深化,后续的林改配套措施也提上议事议程,尤其是林农获得林地之后,如何进行经营管理使其增值增效,并保证其能永续利用,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为保证该工作的顺利进行,巩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成果,需要建立林业科学技术服务于林农的科技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而建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前,深化了解林农对林业科技的需求程度和意愿,客观分析林农对林业科技服务的满意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1 讨论动态和讨论方法 1.1 国内外讨论动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权的变更起伏经历了 60 年的变化。然而,有关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论的讨论主要出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讨论范围十分宽泛,然而更多的是关于林权制度改革的理论、政策和现状分析,较少涉及到林权制度改革后科技服务体系的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郑风田[1]等对我国林权制度的历史沿革进行了讨论,认为我国林权制度改革分为 4 个阶段。田淑英[2]论证了其政策激励悖论的理论渊源在于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和管制导致的产权残缺,提出了森林资源管制制度重构的基本思路。徐晋涛等[3]基于 8 个省份的实地调查分析后,认为我国林权改革模式呈现多元化,其改革已见初步成效。张蕾等[4]基于江西等 4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情况的实地调查资料,分析林改前后农户林地面积、林分构成、林业收入、外出打工人数、林地流转规模等方面的变化,并采纳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量。肖泽忱等[5]从林业工作人员和林农 2 个不同主体对林权改革的认知差异角度,分析了辽宁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国外学者对于林权的改革也有自己的观点,如 Gregersen[6]通过对亚太地区 21 个国家的情况讨论后,认为“分权并不是一种万能药,也并不总是有效或公平的。它可能是一种促进民主治理的方式,在分权的过程中,它可能有助于减缓贫困和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足够的措施。”目前关于科技服务林改的讨论成果较少,且仅有的讨论内容多为定性分析。如李建民等[7]以福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推行的林业科技推广功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