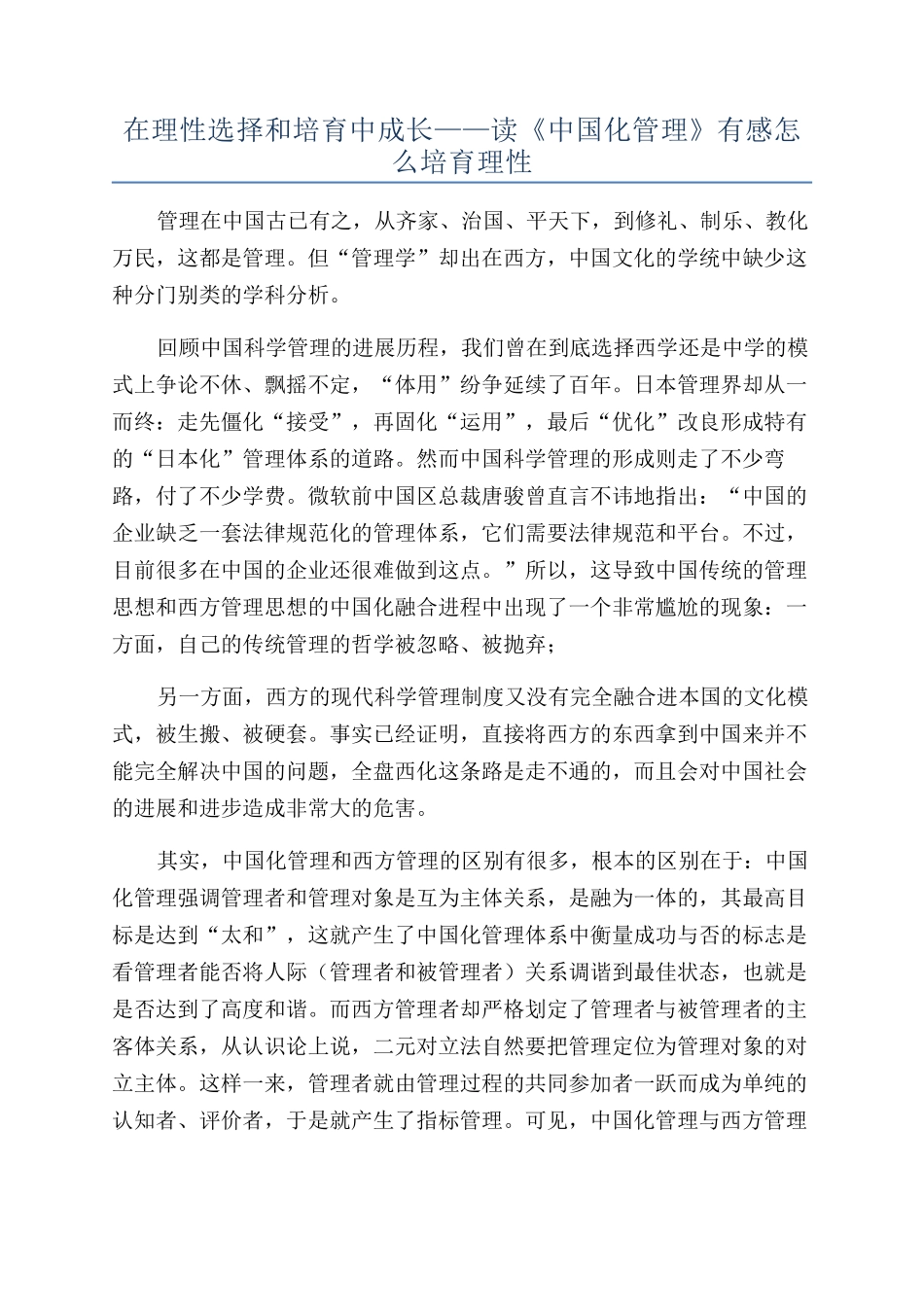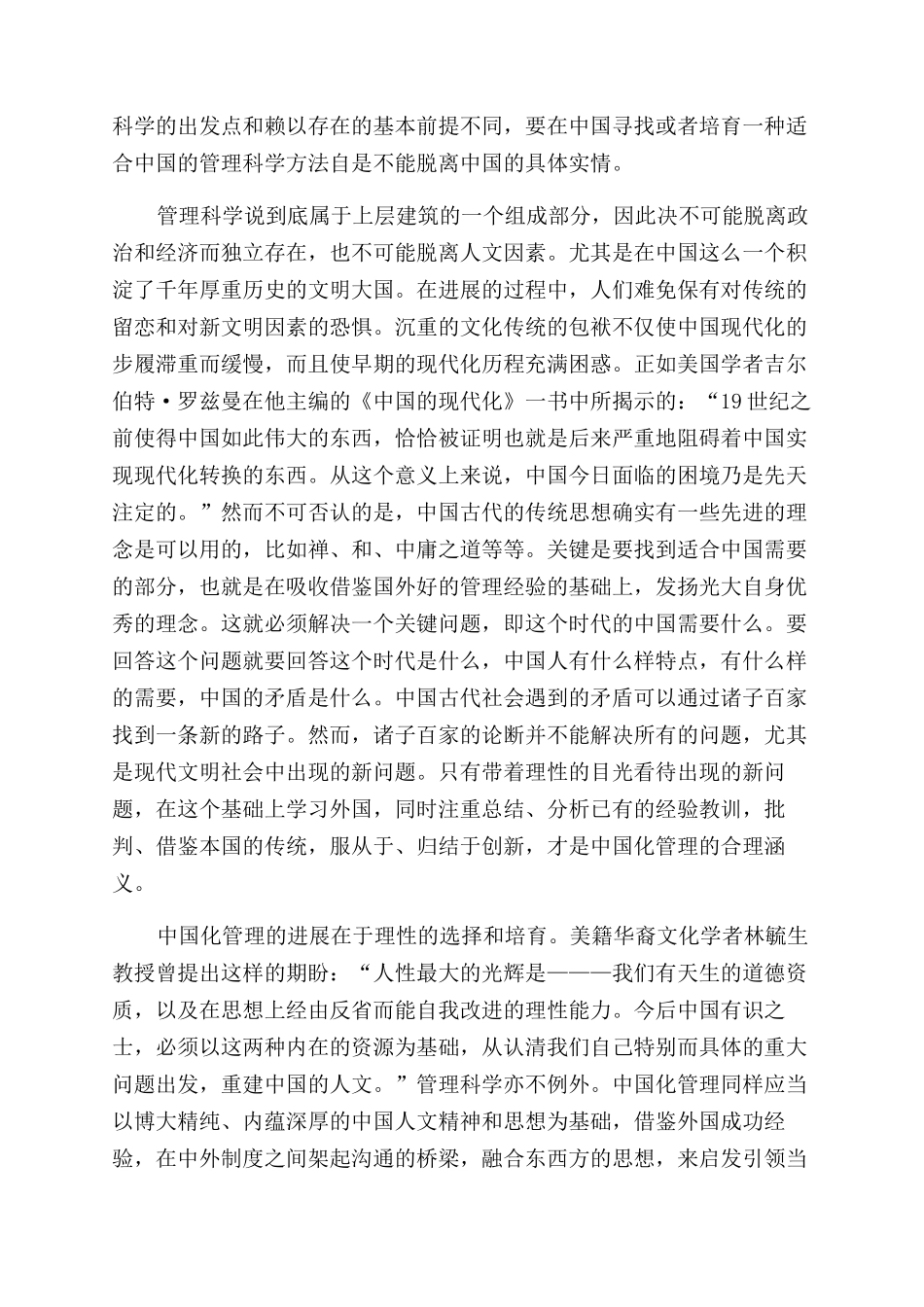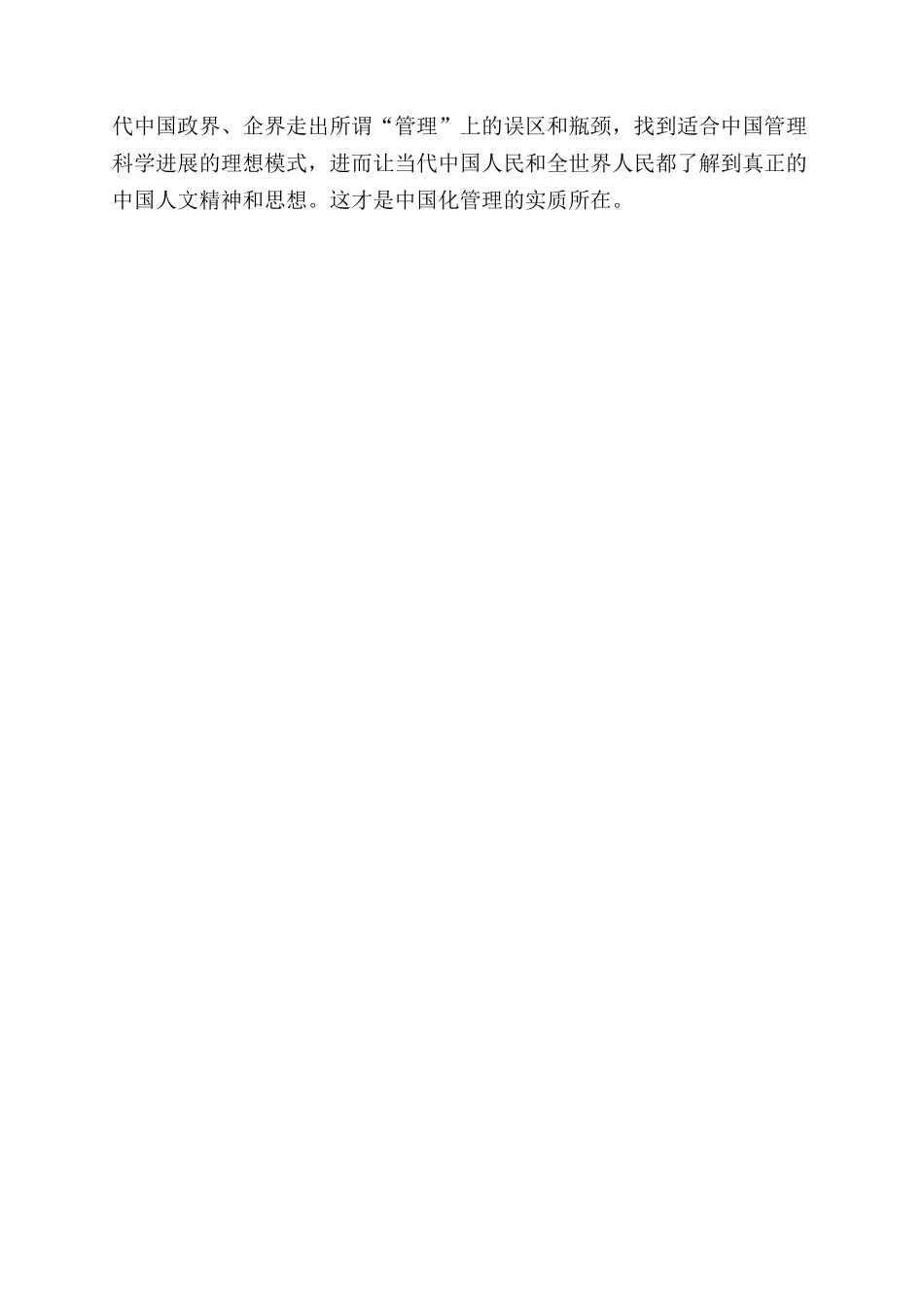在理性选择和培育中成长——读《中国化管理》有感怎么培育理性管理在中国古已有之,从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修礼、制乐、教化万民,这都是管理。但“管理学”却出在西方,中国文化的学统中缺少这种分门别类的学科分析。回顾中国科学管理的进展历程,我们曾在到底选择西学还是中学的模式上争论不休、飘摇不定,“体用”纷争延续了百年。日本管理界却从一而终:走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最后“优化”改良形成特有的“日本化”管理体系的道路。然而中国科学管理的形成则走了不少弯路,付了不少学费。微软前中国区总裁唐骏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的企业缺乏一套法律规范化的管理体系,它们需要法律规范和平台。不过,目前很多在中国的企业还很难做到这点。”所以,这导致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思想的中国化融合进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一方面,自己的传统管理的哲学被忽略、被抛弃;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制度又没有完全融合进本国的文化模式,被生搬、被硬套。事实已经证明,直接将西方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全盘西化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而且会对中国社会的进展和进步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其实,中国化管理和西方管理的区别有很多,根本的区别在于:中国化管理强调管理者和管理对象是互为主体关系,是融为一体的,其最高目标是达到“太和”,这就产生了中国化管理体系中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志是看管理者能否将人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关系调谐到最佳状态,也就是是否达到了高度和谐。而西方管理者却严格划定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主客体关系,从认识论上说,二元对立法自然要把管理定位为管理对象的对立主体。这样一来,管理者就由管理过程的共同参加者一跃而成为单纯的认知者、评价者,于是就产生了指标管理。可见,中国化管理与西方管理科学的出发点和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不同,要在中国寻找或者培育一种适合中国的管理科学方法自是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实情。管理科学说到底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决不可能脱离政治和经济而独立存在,也不可能脱离人文因素。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积淀了千年厚重历史的文明大国。在进展的过程中,人们难免保有对传统的留恋和对新文明因素的恐惧。沉重的文化传统的包袱不仅使中国现代化的步履滞重而缓慢,而且使早期的现代化历程充满困惑。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他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所揭示的:“19 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