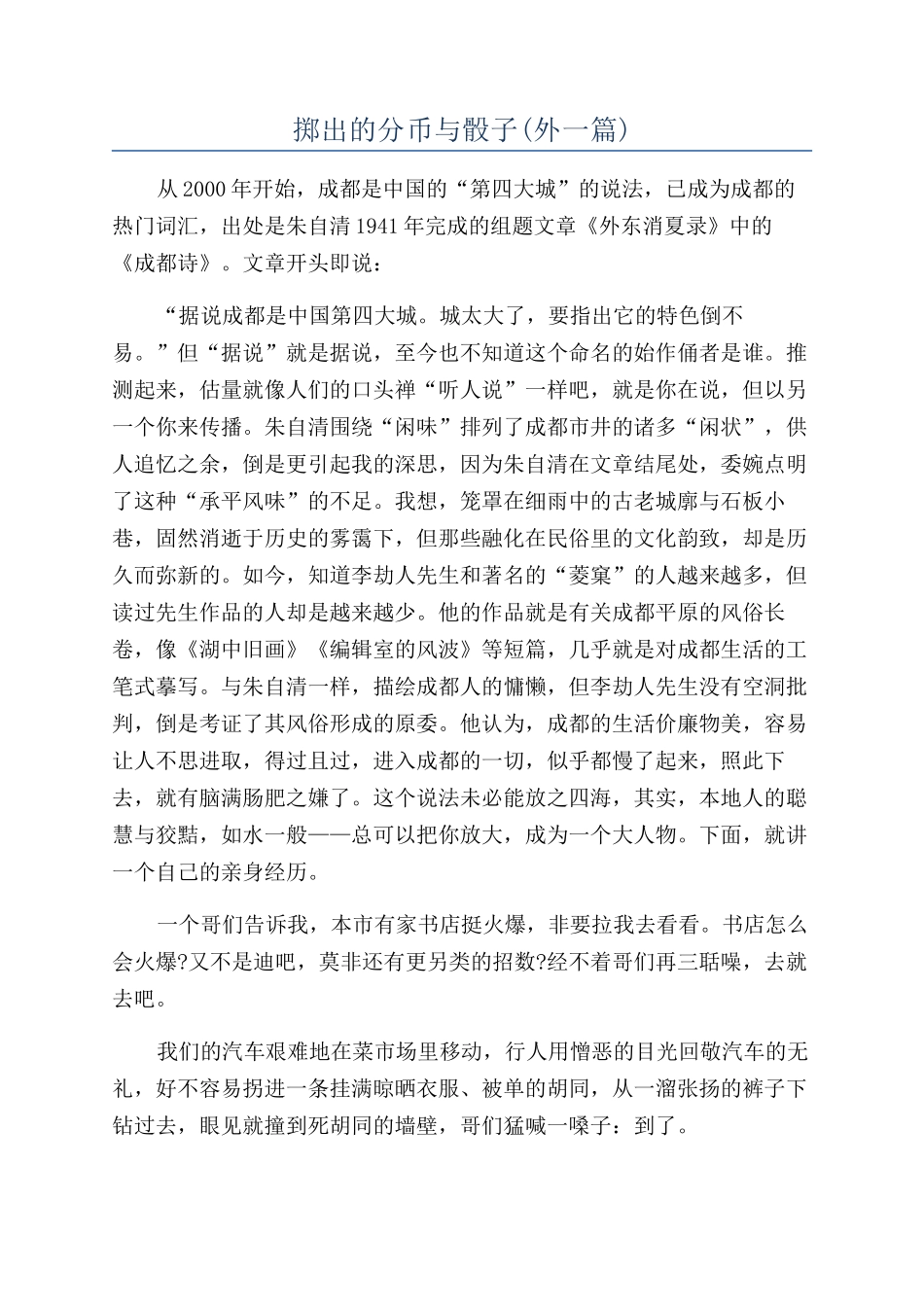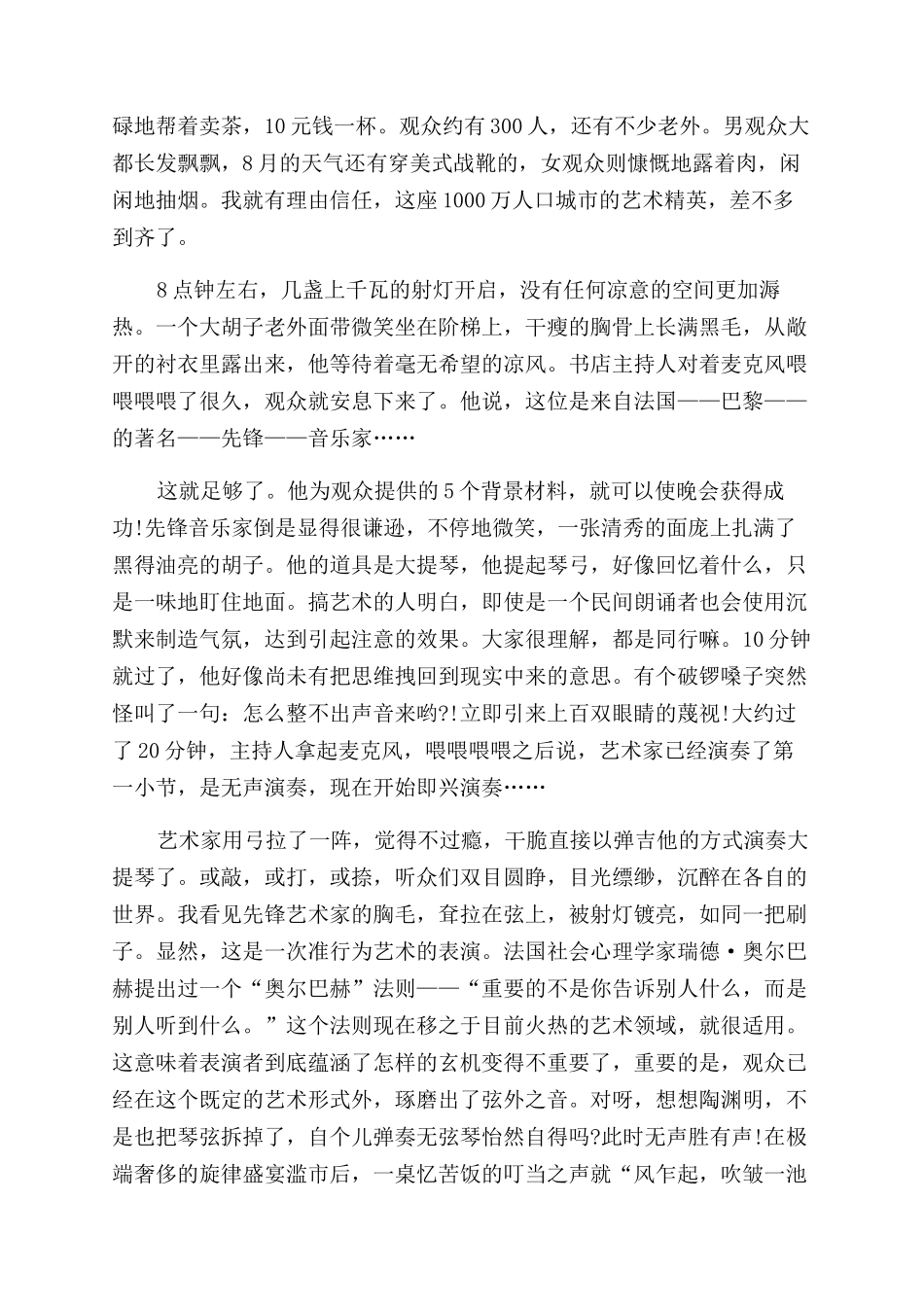掷出的分币与骰子(外一篇)从 2000 年开始,成都是中国的“第四大城”的说法,已成为成都的热门词汇,出处是朱自清 1941 年完成的组题文章《外东消夏录》中的《成都诗》。文章开头即说:“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但“据说”就是据说,至今也不知道这个命名的始作俑者是谁。推测起来,估量就像人们的口头禅“听人说”一样吧,就是你在说,但以另一个你来传播。朱自清围绕“闲味”排列了成都市井的诸多“闲状”,供人追忆之余,倒是更引起我的深思,因为朱自清在文章结尾处,委婉点明了这种“承平风味”的不足。我想,笼罩在细雨中的古老城廓与石板小巷,固然消逝于历史的雾霭下,但那些融化在民俗里的文化韵致,却是历久而弥新的。如今,知道李劫人先生和著名的“菱窠”的人越来越多,但读过先生作品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他的作品就是有关成都平原的风俗长卷,像《湖中旧画》《编辑室的风波》等短篇,几乎就是对成都生活的工笔式摹写。与朱自清一样,描绘成都人的慵懒,但李劫人先生没有空洞批判,倒是考证了其风俗形成的原委。他认为,成都的生活价廉物美,容易让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进入成都的一切,似乎都慢了起来,照此下去,就有脑满肠肥之嫌了。这个说法未必能放之四海,其实,本地人的聪慧与狡黠,如水一般——总可以把你放大,成为一个大人物。下面,就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一个哥们告诉我,本市有家书店挺火爆,非要拉我去看看。书店怎么会火爆?又不是迪吧,莫非还有更另类的招数?经不着哥们再三聒噪,去就去吧。我们的汽车艰难地在菜市场里移动,行人用憎恶的目光回敬汽车的无礼,好不容易拐进一条挂满晾晒衣服、被单的胡同,从一溜张扬的裤子下钻过去,眼见就撞到死胡同的墙壁,哥们猛喊一嗓子:到了。一套底楼的住宅,将墙打掉开成门面,一排排书架在拥塞的空间里,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安置。几幅油画待在楠木画框里,因沉重而气概不凡。空气芳香剂飘浮着玫瑰花香型的化学改良味道,让热汗缠身的我也突然想起了风情万种的女人!在这个时候,男人都是大方的。CD 版的萨克斯因播放太狠,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出尘了,但恰到好处地在提醒你,思维不能飘逸得太远,还是选书要紧!这时,我听见深切的歌声,从书架深处弥散出来。在我走向声音的发源地时,才反应过来,这是唱诗班的功课,是布道时刻对天父的赞美。莫非书店还兼有教堂的?走到一扇小门边,发现别有洞天,里面还有一间茶室。看见有好几十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