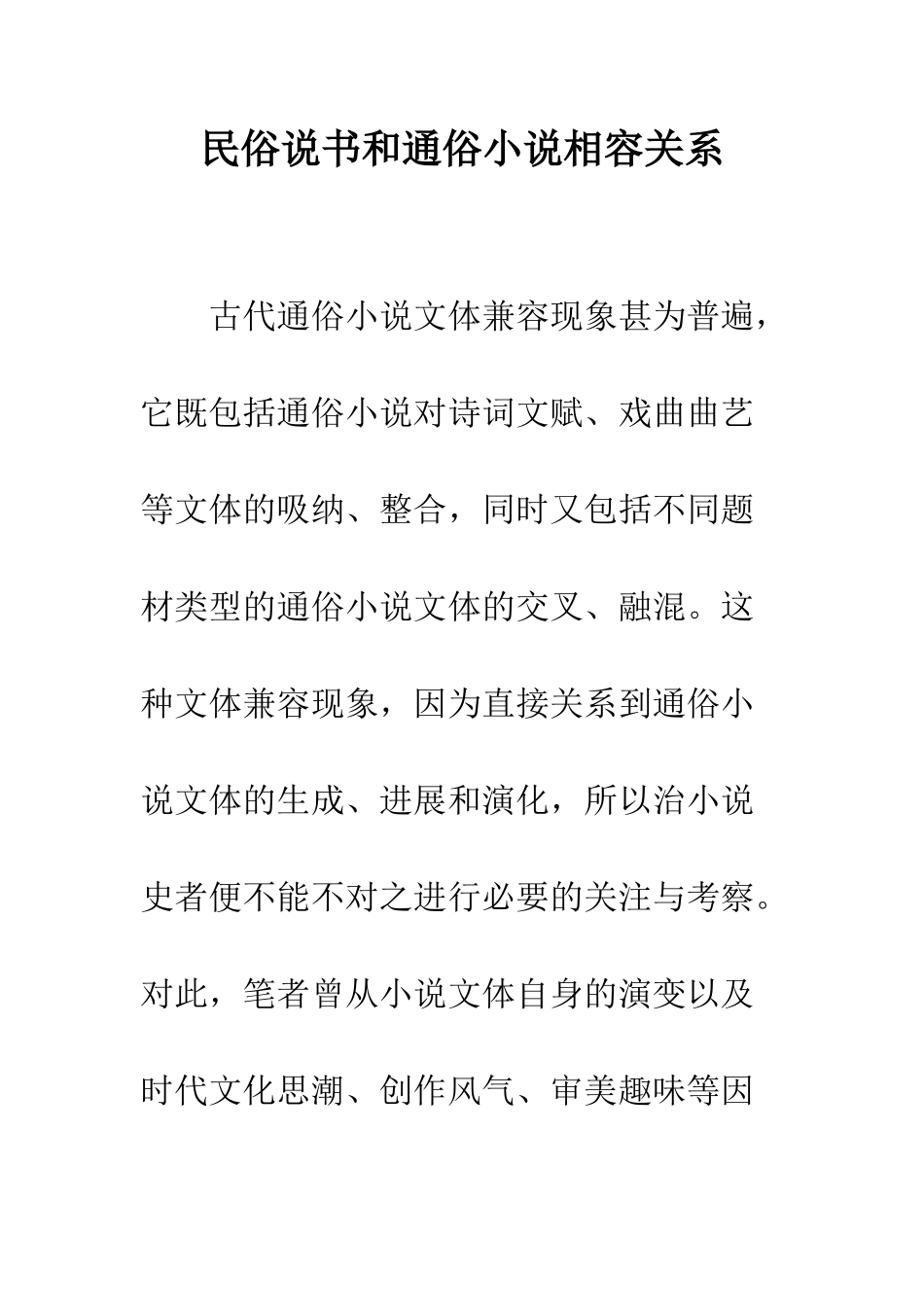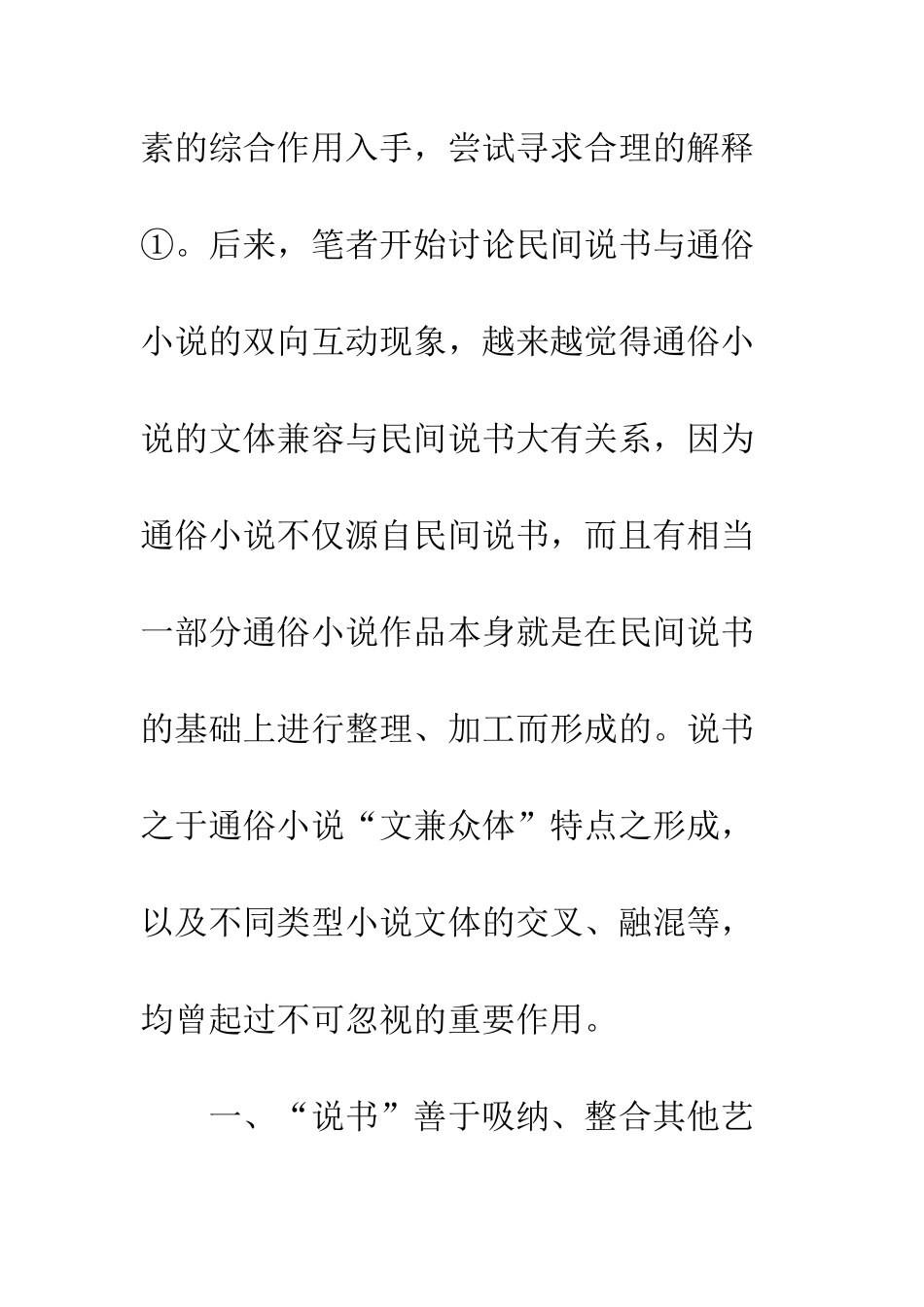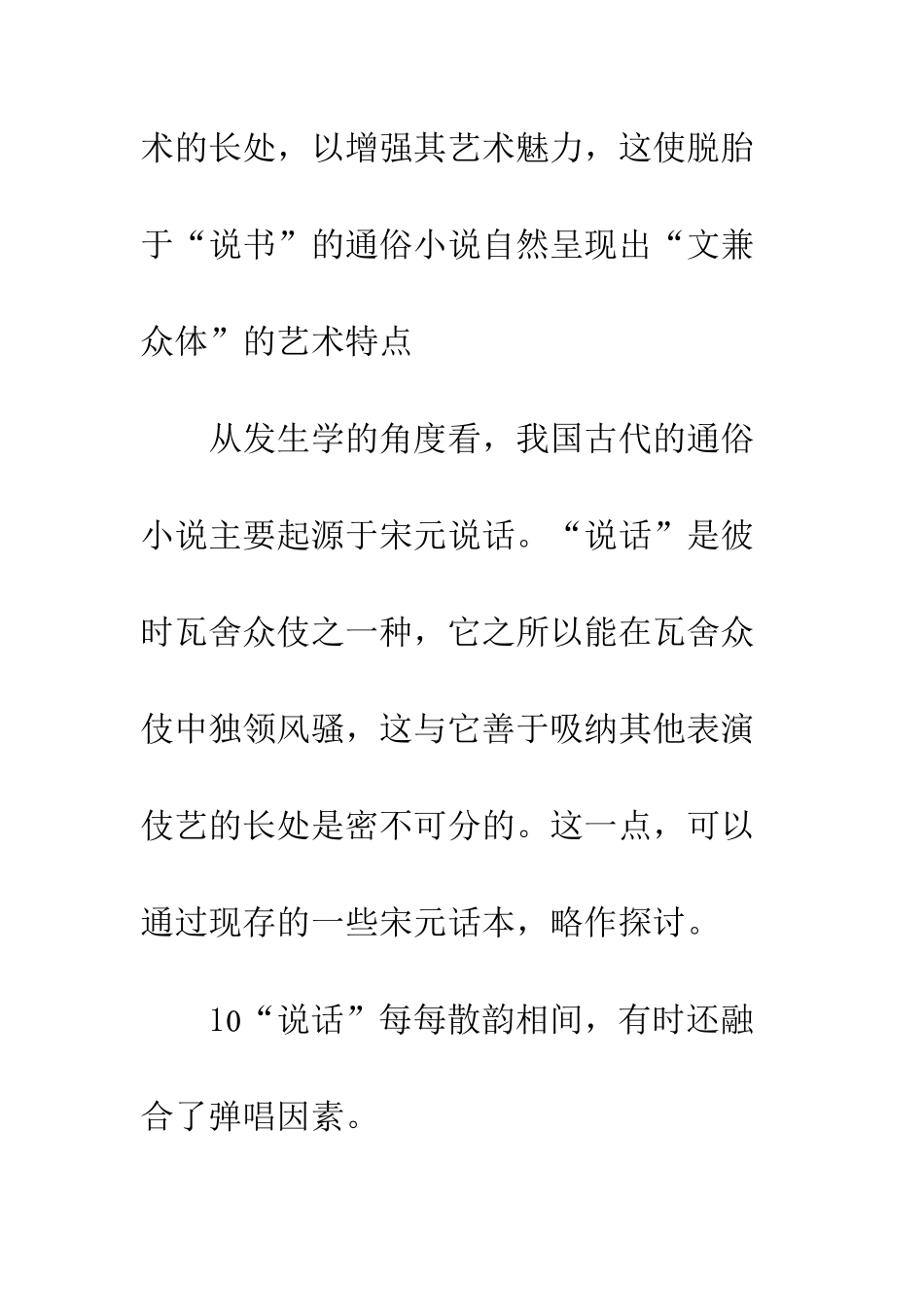民俗说书和通俗小说相容关系 古代通俗小说文体兼容现象甚为普遍,它既包括通俗小说对诗词文赋、戏曲曲艺等文体的吸纳、整合,同时又包括不同题材类型的通俗小说文体的交叉、融混。这种文体兼容现象,因为直接关系到通俗小说文体的生成、进展和演化,所以治小说史者便不能不对之进行必要的关注与考察。对此,笔者曾从小说文体自身的演变以及时代文化思潮、创作风气、审美趣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入手,尝试寻求合理的解释①。后来,笔者开始讨论民间说书与通俗小说的双向互动现象,越来越觉得通俗小说的文体兼容与民间说书大有关系,因为通俗小说不仅源自民间说书,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通俗小说作品本身就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加工而形成的。说书之于通俗小说“文兼众体”特点之形成,以及不同类型小说文体的交叉、融混等,均曾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一、“说书”善于吸纳、整合其他艺术的长处,以增强其艺术魅力,这使脱胎于“说书”的通俗小说自然呈现出“文兼众体”的艺术特点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我国古代的通俗小说主要起源于宋元说话。“说话”是彼时瓦舍众伎之一种,它之所以能在瓦舍众伎中独领风骚,这与它善于吸纳其他表演伎艺的长处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现存的一些宋元话本,略作探讨。 1 “说话”每每散韵相间,有时还融合了弹唱因素。 “说话”当然需要口才,但是艺人为了使所说之“话”引人入胜,并能产生声调铿锵,节奏多变的艺术效果,还常常穿插、念诵大量的诗词歌赋或骈词骊语,所谓“曰得词,念得诗”,“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②。这样,就使那些根据“说话”成果整理而成的话本小说,兼具了诗词文体的长处,既可以提升“说话”的文化品位,同时又具有多方面的艺术功能:或概括正话的主要旨意,评论人物、事件;或描摹环境、景物,渲染场景氛围;或调节叙述速度,使情节张弛有致,等等。 有时,说话人为了更为有效地增强听众的兴趣,还在叙事时伴以弹唱。“小说”在初期就是有说有唱的。耐得翁《都城纪胜》即说“小说谓之银字儿”③。银字在唐代是一种乐器,这种乐器以“银字制笙,以银作字,饰其音节”。徐养原《管色考》说:“一云镂字于管,钿之以银,谓之银字管。”宋代则有银字笙和银字醏篥。小说之所以叫“银字儿”,这是因为艺人一面讲说,一面还以银字笙和银字醏篥伴奏、演唱话本中的歌词。象《刎颈鸳鸯会》这样的话本就是说中带唱的;该话本中“奉劳歌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