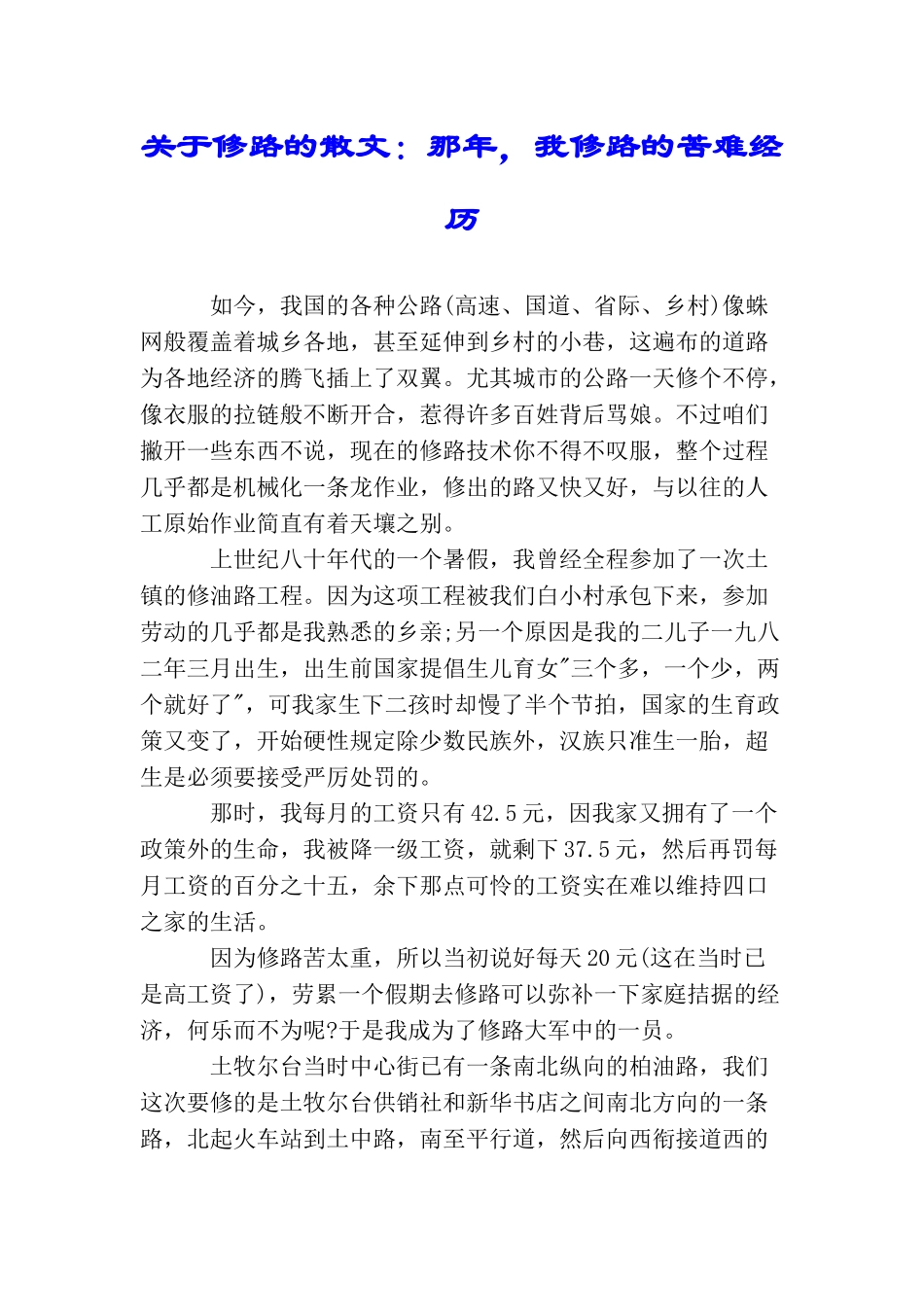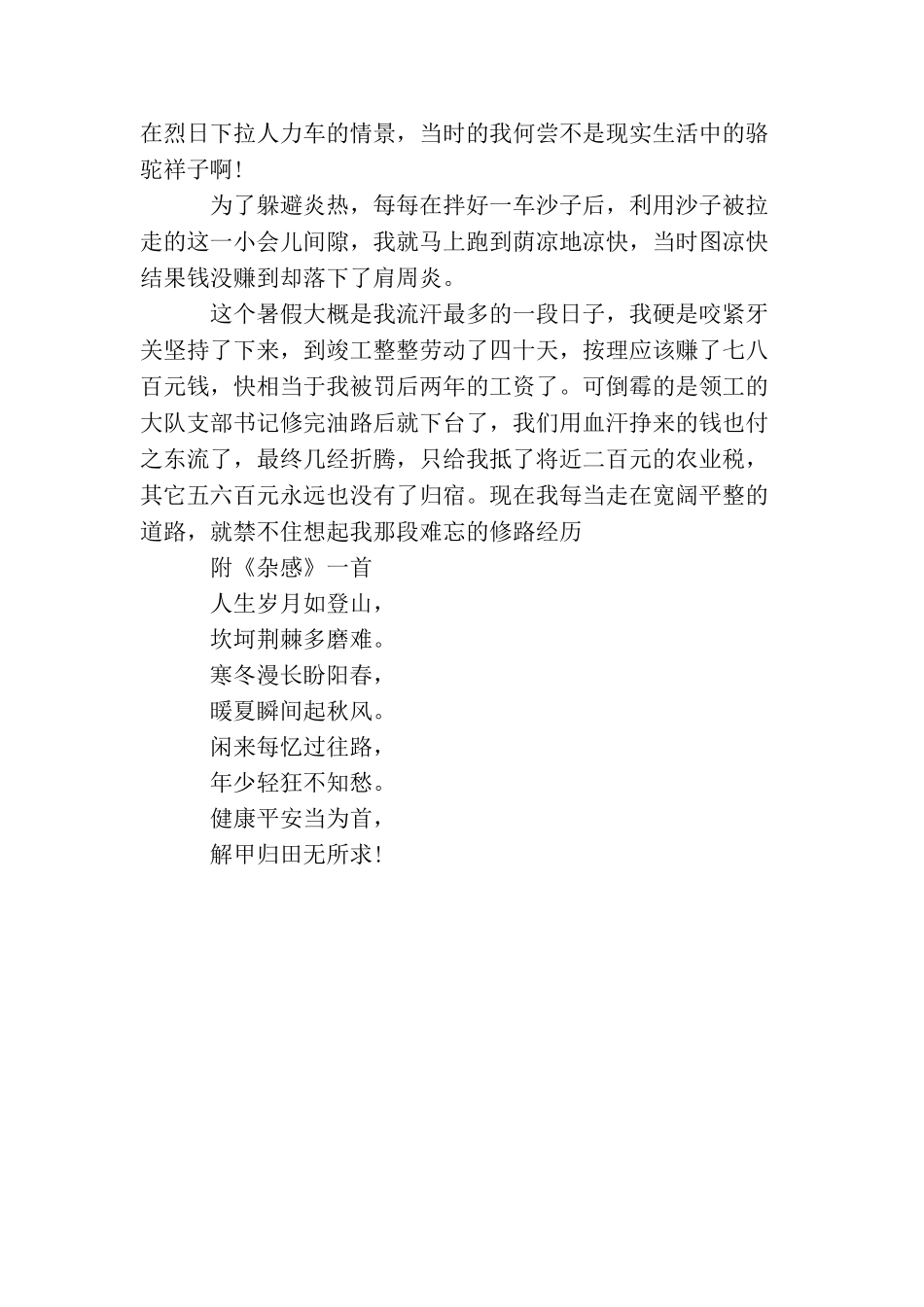关于修路的散文:那年,我修路的苦难经历 如今,我国的各种公路(高速、国道、省际、乡村)像蛛网般覆盖着城乡各地,甚至延伸到乡村的小巷,这遍布的道路为各地经济的腾飞插上了双翼。尤其城市的公路一天修个不停,像衣服的拉链般不断开合,惹得许多百姓背后骂娘。不过咱们撇开一些东西不说,现在的修路技术你不得不叹服,整个过程几乎都是机械化一条龙作业,修出的路又快又好,与以往的人工原始作业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暑假,我曾经全程参加了一次土镇的修油路工程。因为这项工程被我们白小村承包下来,参加劳动的几乎都是我熟悉的乡亲;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二儿子一九八二年三月出生,出生前国家提倡生儿育女"三个多,一个少,两个就好了",可我家生下二孩时却慢了半个节拍,国家的生育政策又变了,开始硬性规定除少数民族外,汉族只准生一胎,超生是必须要接受严厉处罚的。 那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 42.5 元,因我家又拥有了一个政策外的生命,我被降一级工资,就剩下 37.5 元,然后再罚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十五,余下那点可怜的工资实在难以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 因为修路苦太重,所以当初说好每天 20 元(这在当时已是高工资了),劳累一个假期去修路可以弥补一下家庭拮据的经济,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成为了修路大军中的一员。 土牧尔台当时中心街已有一条南北纵向的柏油路,我们这次要修的是土牧尔台供销社和新华书店之间南北方向的一条路,北起火车站到土中路,南至平行道,然后向西衔接道西的208 国道。那时没有挖掘机,路基取土都是靠人工用铁锹和镐头,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点蚕食。第一步是挖路基,需要至少挖 30 多公分深,两车道宽,这道工序验收合格后接下来就是铺石子,之后再在石子上铺一层火山灰、白灰和红粘土,为了使三者混和均匀,没有搅拌机只能用两匹马拉着耕地用的犁来回耕三、四次,待这些东西混和均匀后再在上面浇水,为了使路的基础扎实少空隙,弄好这道工序得反复两三次,我们连夜加班加点地干,陆续接通路旁居民家的水,浇好后再用马拉着碌碡碾压结实,这些都做好后,就只等最后一道工序上油了,整个过程不亚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筑路的艰难。 最后一道工序上油更是在烈日下的煎熬。炼油场地设在新华书店南戏台院内,这里是每年沟通会唱晋剧的喧闹地方。北墙下备有小山丘般的细沙,西边戏台下是用沙子围着的沥青,这样做是怕胶状的沥青被太阳晒化了外流;中间架起两块厚厚的大铁板,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