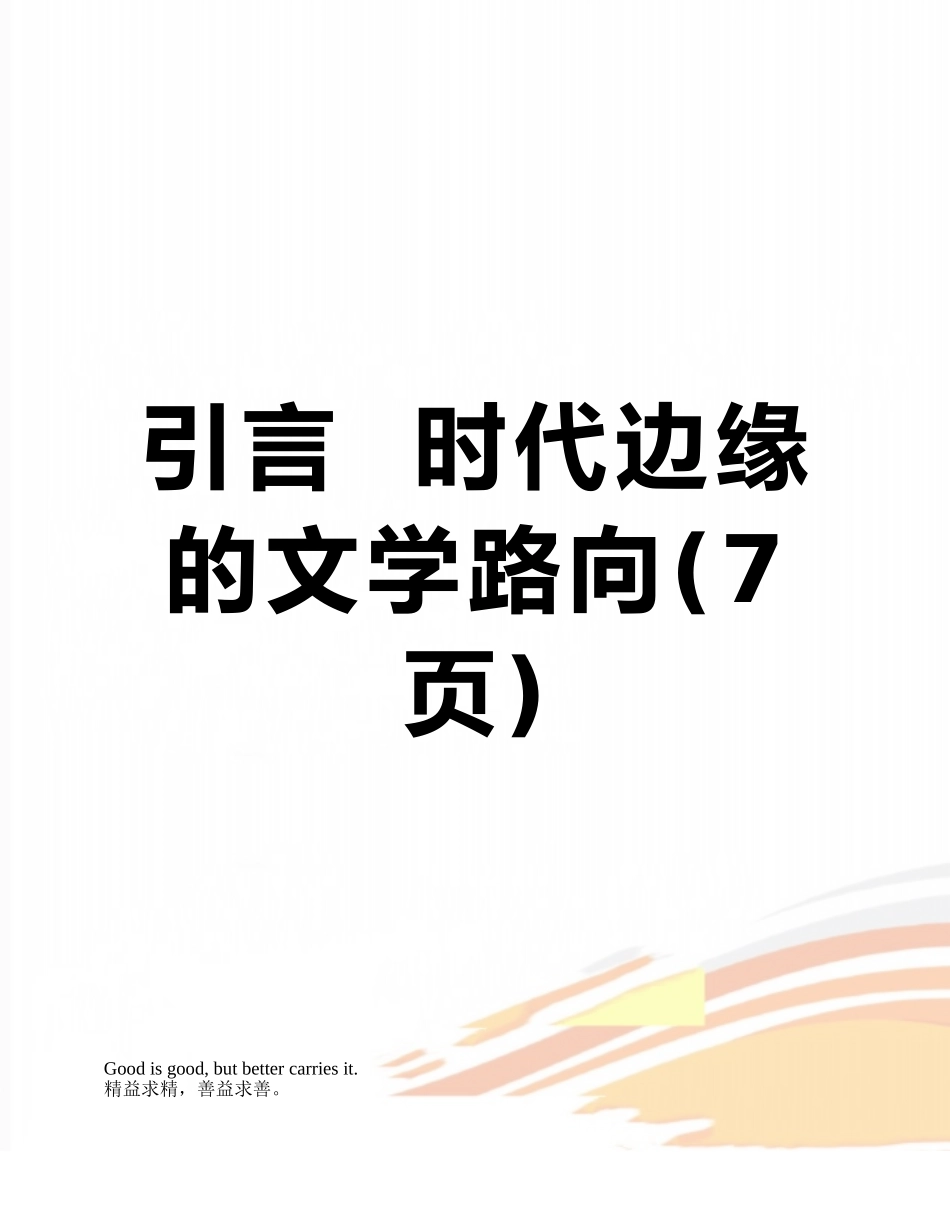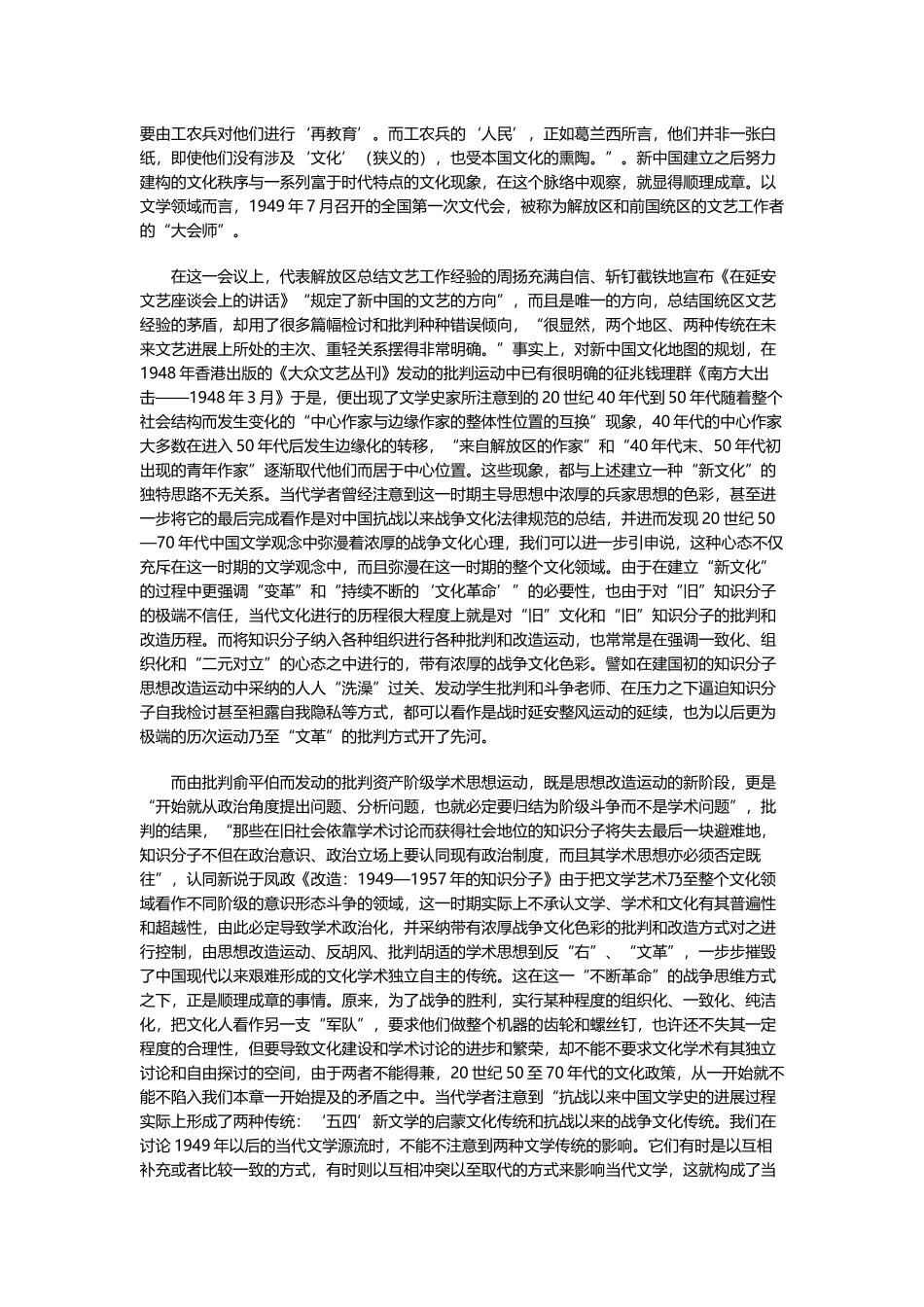引言 时代边缘的文学路向(7页)Good is good, but better carries it.精益求精,善益求善。引言时代边缘的文学路向 域外学者曾经注意到 20 世纪 50—70 年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政策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在向知识分子灌输新的意识形态时,它“比以往儒家思想对传统文人施加的影响更全面,更深化细致”;另一方面,“它又想激励知识分子在专业上多生产一些东西”。在比较严厉的时期它“要知识分子服从思想改造运动;在比较松弛的时期又给他们以某些责任和优遇,希望在实现现代化中赢得他们的合作。”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评述参看默尔-戈德曼撰写的该书第五章《党与知识分子》和第十章《党与知识分子:第二阶段》。至少对于 1949—1965 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政策来说,这个观察是相当客观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摇摆始终没有达到比较平衡的状态,改造和组织始终是占优势的因素。组织的方式,譬如各种专业协会的建立与各种刊物的编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对于这种模式,当时不是没有置疑和批判的意见,但这些意见在当时并无成效例如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就对文学刊物的组织和出版方式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又如根据前苏联模式进行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在一开始受到不少专家学者的批判和抵制这一模式的优缺点,后来的学者有更清楚的认识。从文学领域来说,洪子诚先生就曾指出,作家领取固定的薪金,固然可以缓解经济上的重大压力,“不过,作家不受写作实际情况影响的固定薪金收入,有时也会演变为失去写作紧迫感,而放松了作家原来应承担的责任。这种状况,使他们中有的人多年不写作,而仅靠既往的‘名声’生活。”另一方面,知名作家担任各种组织的官职,“这自然是对他们所取得的成绩的一种‘报答’,不过,政治力量把他们推上原来与他们不相干的位置,如何不辜负这一‘名声’与‘位置’,自然要为他们所考虑。这种褒奖,对一些人来说。最终可能使他们牺牲了思想艺术上的制造力和精神上的独立性,以换得对这种社会地位的保持。”而对于敢于向当时的法律规范挑战的作家来说,彻底纳入组织化又会导致他们命运的极端不幸,“他们遇到的打击,生活道路的坎坷,也是其他时期的作家所难以比拟的。当他们对确立的文学法律规范、路线表示出离异、悖逆或进行挑战时,其物质、社会政治地位便会一落千丈。 通常的惩治措施是开除作协会员资格(这意味着失去写作权利)、降职降薪,‘下放’至工厂、农村或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