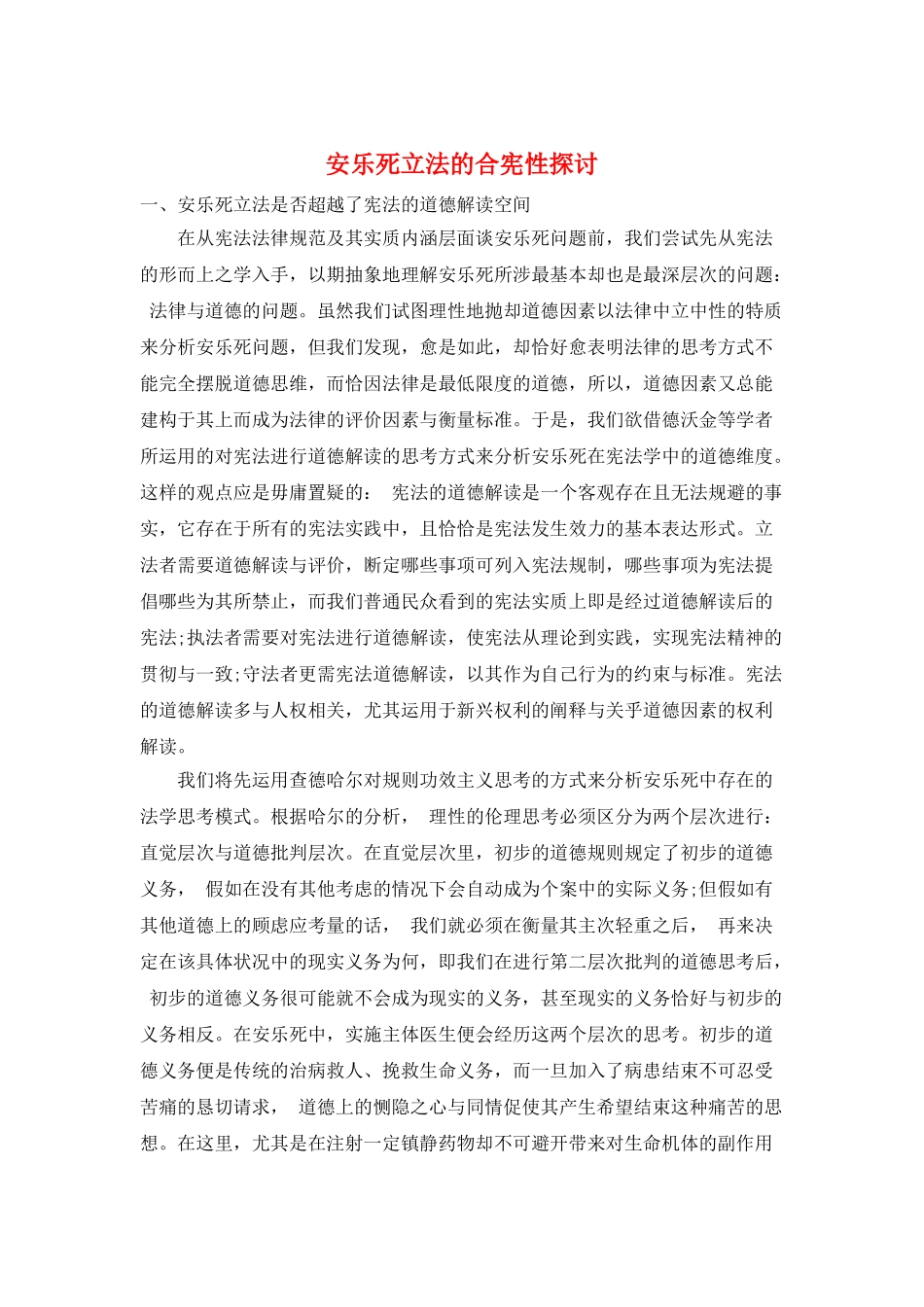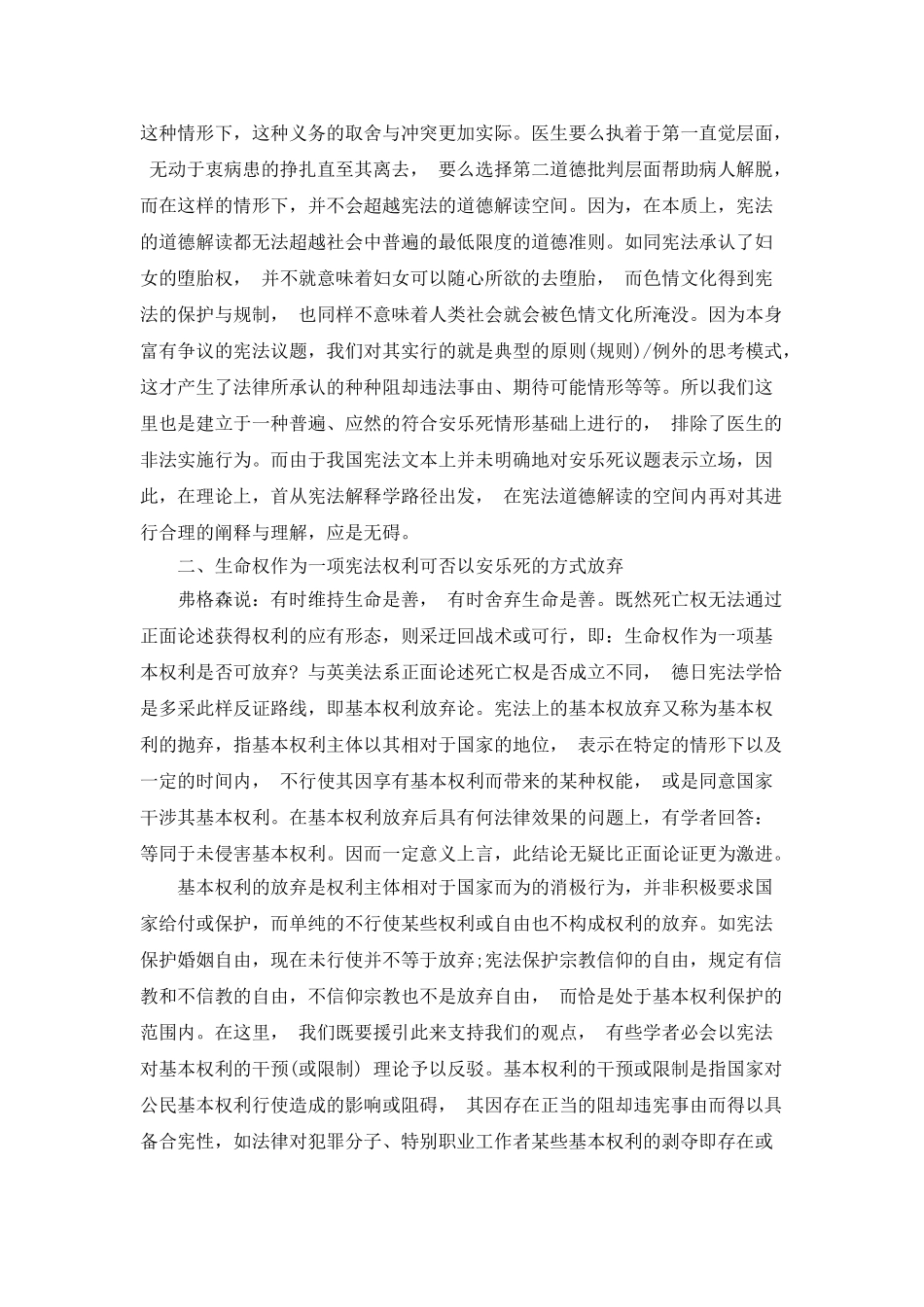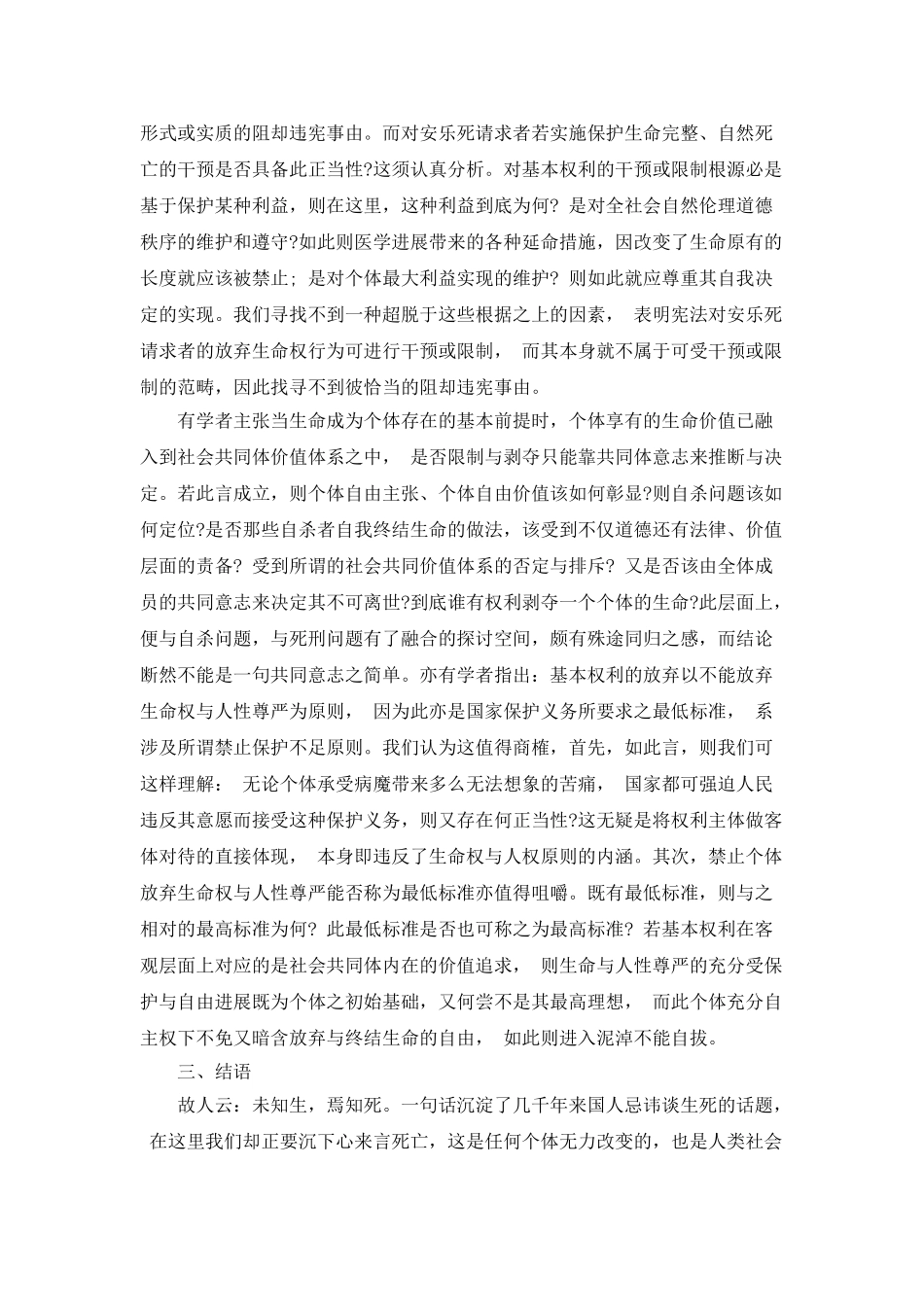安乐死立法的合宪性探讨一、安乐死立法是否超越了宪法的道德解读空间 在从宪法法律规范及其实质内涵层面谈安乐死问题前,我们尝试先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入手,以期抽象地理解安乐死所涉最基本却也是最深层次的问题: 法律与道德的问题。虽然我们试图理性地抛却道德因素以法律中立中性的特质来分析安乐死问题,但我们发现,愈是如此,却恰好愈表明法律的思考方式不能完全摆脱道德思维,而恰因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所以,道德因素又总能建构于其上而成为法律的评价因素与衡量标准。于是,我们欲借德沃金等学者所运用的对宪法进行道德解读的思考方式来分析安乐死在宪法学中的道德维度。这样的观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宪法的道德解读是一个客观存在且无法规避的事实,它存在于所有的宪法实践中,且恰恰是宪法发生效力的基本表达形式。立法者需要道德解读与评价,断定哪些事项可列入宪法规制,哪些事项为宪法提倡哪些为其所禁止,而我们普通民众看到的宪法实质上即是经过道德解读后的宪法;执法者需要对宪法进行道德解读,使宪法从理论到实践,实现宪法精神的贯彻与一致;守法者更需宪法道德解读,以其作为自己行为的约束与标准。宪法的道德解读多与人权相关,尤其运用于新兴权利的阐释与关乎道德因素的权利解读。 我们将先运用查德哈尔对规则功效主义思考的方式来分析安乐死中存在的法学思考模式。根据哈尔的分析, 理性的伦理思考必须区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直觉层次与道德批判层次。在直觉层次里,初步的道德规则规定了初步的道德义务, 假如在没有其他考虑的情况下会自动成为个案中的实际义务;但假如有其他道德上的顾虑应考量的话, 我们就必须在衡量其主次轻重之后, 再来决定在该具体状况中的现实义务为何,即我们在进行第二层次批判的道德思考后, 初步的道德义务很可能就不会成为现实的义务,甚至现实的义务恰好与初步的义务相反。在安乐死中,实施主体医生便会经历这两个层次的思考。初步的道德义务便是传统的治病救人、挽救生命义务,而一旦加入了病患结束不可忍受苦痛的恳切请求, 道德上的恻隐之心与同情促使其产生希望结束这种痛苦的思想。在这里,尤其是在注射一定镇静药物却不可避开带来对生命机体的副作用这种情形下,这种义务的取舍与冲突更加实际。医生要么执着于第一直觉层面, 无动于衷病患的挣扎直至其离去, 要么选择第二道德批判层面帮助病人解脱,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并不会超越宪法的道德解读空间。因为,在本质上,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