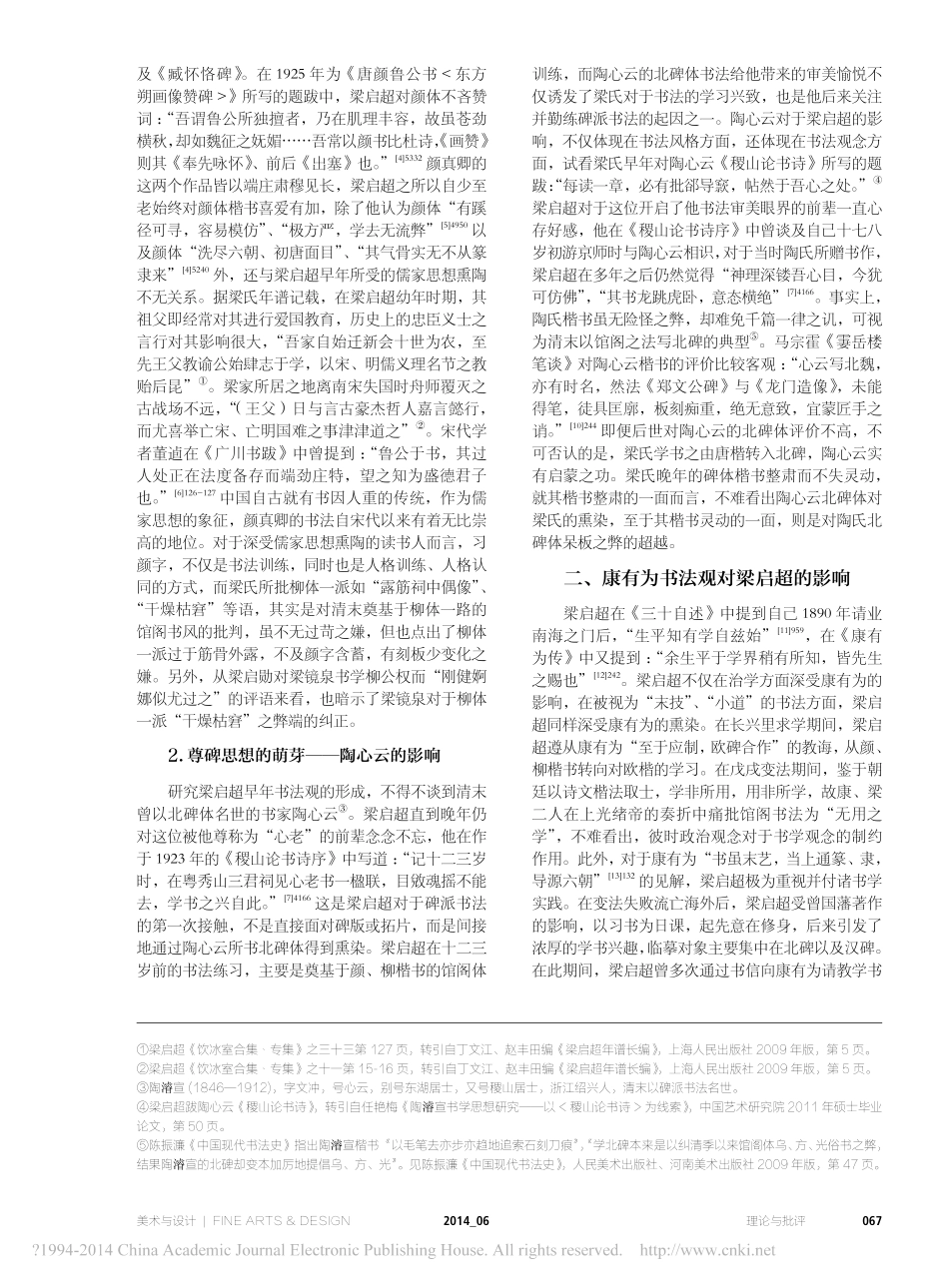066理论与批评067美术与设计|FINEARTS&DESIGN2014_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张铁华(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049)[摘要]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在师从康有为之后,梁启超的书法观念深受其师的影响,尤其体现在对干禄书体的态度、学书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以及“体兼碑帖”等方面。梁氏于书法一途既汲取康氏书论中的合理因素,又不为康氏的观点遮蔽望眼。从对梁启超书法观念之转变的剖析中,亦可折射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对于书法的不同体认。[关键词]康有为;梁启超;书法观念[中图分类号]J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6-06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之影响考辨收稿日期:2014-08-11作者简介:张铁华(1974-),男,安徽无为人,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书法史论、书法美学。①梁启勋《高祖以下之家谱》,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②叶大焯《镜泉梁老先生庆寿序》,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二人不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清末民初书坛,二人也颇有建树。康、梁书法风格差异很大,季惟斋《书史》提到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而取法北朝隋唐,浑穆自高,气体亦能清肃,高过其师矣”[1]271。季氏所论梁启超“作书全不以为然”,如仅指康、梁书法风格而言,尚可成立,如兼指书法观念而言,则有失公允。丁文隽《书法精论》称赞梁启超书法“结字之谨严,笔力之险劲,风格之高古,远出邓石如、赵之谦、李瑞清诸家之上,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2]106-107。丁氏对梁启超书法的评价不无溢美之嫌,至于“康氏盛倡尊碑之说,得此高足,堪以自慰矣”则暗示了康、梁书法观念的传承关系。从梁启超书法观念的转变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意在功名而练习馆阁体,对于科考之以楷法取士深感痛恶;中年时期受曾国藩著作的影响,效仿曾氏以习字作为修身的方便法门;晚年以学书为乐,注重习书过程之趣味的体验,并对现代书法美学有开创之功。检诸梁启超年谱以及康、梁往来书信等资料,可以发现在不同时期,梁启超曾多次向康有为请益书法。因此,研究梁启超的书法观念,不应忽视康有为对梁氏的影响。一、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在考察康有为书法观念对梁启超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先对梁氏早年的书法观念作一梳理,以便通过对比,揭示梁启超在师从康有为之后,其书法观念所发生的转变。梁启超早年的书法观念主要体现在对颜、柳楷书的取舍以及对陶心云碑体楷书的认同等方面。1.喜颜恶柳梁启超早年的书法学习主要得益于家庭的影响,尤其是其祖父梁镜泉的指授。据梁启勋《高祖以下家谱》记载,梁启超的祖父梁镜泉“好学问,书法学柳公权,刚健婀娜似尤过之”①。梁镜泉“课诸孙也详而明”②,在诸孙之中,梁镜泉最喜梁启超。由此不难推测,梁启超早年习字必定得到过祖父梁镜泉的指授。从存世的梁启超在1894年为家乡茶坑村文昌阁所书七言对联来看,书风端正、拘谨,柳体特征明显,可以印证梁启超早年确实对柳体楷书下过工夫,而联系梁氏后来的有关论述来看,他其实对于书学柳体颇为反感。在1925年为《唐颜鲁公书<东方朔画像赞碑>》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曾把颜、柳楷书的特点加以对比,对柳体不乏抨击之词:“若柳诚悬则露筋祠中偶像,无取焉耳。”[4]5323在一年后的1926年,梁启超在为清华学校教职员工书法研究会所做的演讲中,又把柳体列入初学书法最不宜模仿的四派之一:“(柳公权)这一派,干燥枯窘。本身虽好,学之不宜,我常说柳字好像四月的腊肠,好是好吃,只是咬不动。学他的人,一点不感乐趣。”[5]4949与对“干燥枯窘”的柳体印象不同的是,少年时期的梁启超对颜体楷书情有独钟,喜临《颜家庙碑》及《臧怀恪碑》。在1925年为《唐颜鲁公书<东方朔画像赞碑>》所写的题跋中,梁启超对颜体不吝赞词:“吾谓鲁公所独擅者,乃在肌理丰容,故虽苍劲横秋,却如魏征之妩媚……吾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