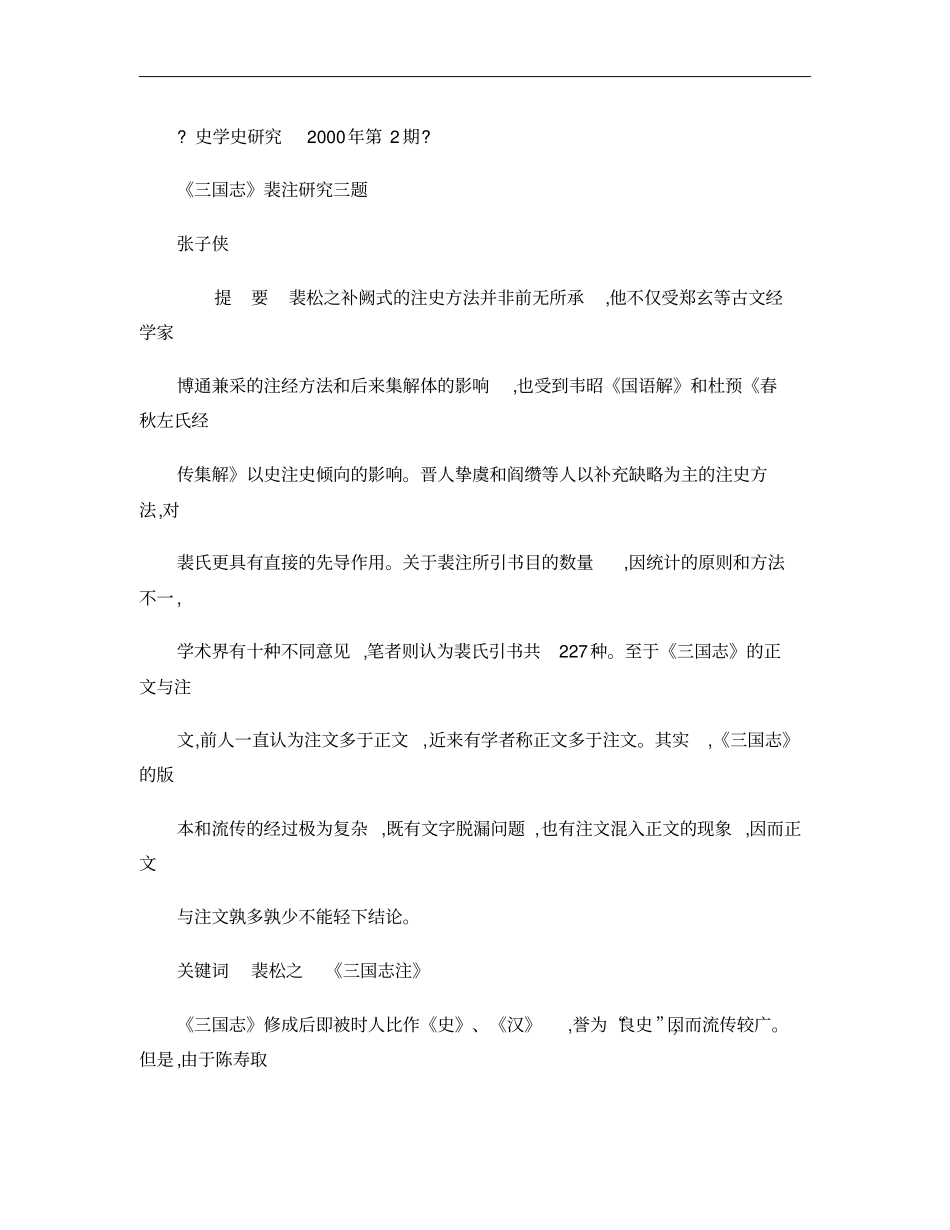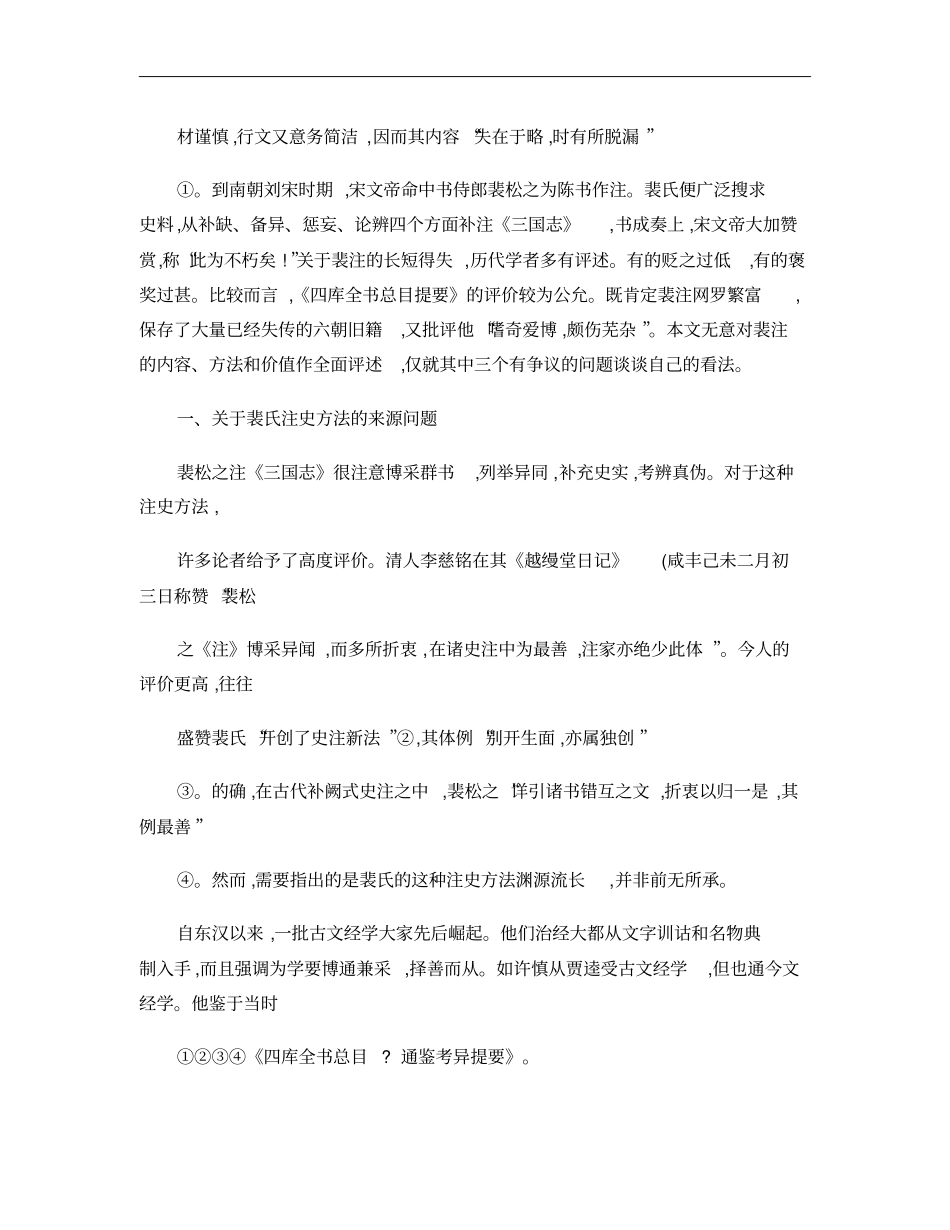?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张子侠提要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因统计的原则和方法不一,学术界有十种不同意见,笔者则认为裴氏引书共227种。至于《三国志》的正文与注文,前人一直认为注文多于正文,近来有学者称正文多于注文。其实,《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关键词裴松之《三国志注》《三国志》修成后即被时人比作《史》、《汉》,誉为“良史”,因而流传较广。但是,由于陈寿取材谨慎,行文又意务简洁,因而其内容“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①。到南朝刘宋时期,宋文帝命中书侍郎裴松之为陈书作注。裴氏便广泛搜求史料,从补缺、备异、惩妄、论辨四个方面补注《三国志》,书成奏上,宋文帝大加赞赏,称“此为不朽矣!”关于裴注的长短得失,历代学者多有评述。有的贬之过低,有的褒奖过甚。比较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价较为公允。既肯定裴注网罗繁富,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六朝旧籍,又批评他“嗜奇爱博,颇伤芜杂”。本文无意对裴注的内容、方法和价值作全面评述,仅就其中三个有争议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关于裴氏注史方法的来源问题裴松之注《三国志》很注意博采群书,列举异同,补充史实,考辨真伪。对于这种注史方法,许多论者给予了高度评价。清人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称赞“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今人的评价更高,往往盛赞裴氏“开创了史注新法”②,其体例“别开生面,亦属独创”③。的确,在古代补阙式史注之中,裴松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④。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裴氏的这种注史方法渊源流长,并非前无所承。自东汉以来,一批古文经学大家先后崛起。他们治经大都从文字训诂和名物典制入手,而且强调为学要博通兼采,择善而从。如许慎从贾逵受古文经学,但也通今文经学。他鉴于当时①②③④《四库全书总目?通鉴考异提要》。缪钺:《三国志导读》第31页,巴蜀书社1988年版。杨翼骧:《裴松之与〈三国志〉注》,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诸经解说纷纭,尤其是今文经说与古文经说差异很大,需要辨别是非,决定取舍,于是撰写了《五经异义》。其体例是先以专题类目为纲,罗列今古文各家之说,然后加以案断,定于一尊。书中涉及许多名物典制,保存了丰富的经今古文异说的材料。在博通兼采方面,郑玄更为突出。他博学多师,于经传百家之学无所不通。他在遍注群经的过程中,虽立足于古文,但兼综博采,参互各说,以立己见。既有对经文文字的注释、校勘,又有对异文的罗列、综论和考辨,其学术表现出博通兼采和独创的特点。郑注出现之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苦于今古文家法烦琐,又震于郑氏经术的博洽,于是翕然宗从,郑学遂独盛一时。到魏晋时期,许多今文经传或已亡佚,或无传人,而古文经学则重新兴起,东晋元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弼,《尚书》郑氏(玄,《古文尚书》孔氏(伪孔安国,《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预、服氏(虔,《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至此,西汉今文十四博士已无一存。裴松之在东晋生活了近五十年,这种今文经学灭绝而古文经学复兴的学术背景对其治学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据《宋书》本传记载,“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从他研读的经典和治学的风格来看,显然是走的古文经学家的路子。裴注中有时也征引经文或经注上的材料,其中采用最多的是郑玄注。这说明他受古文经学家的影响很大,郑玄等人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与其蜜蜂兼采务在周悉的注史方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就注释的体例而言,裴注受集解体的影响也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注、史注和子注都很兴盛,注释的体例也有较大发展,表现之一就是集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