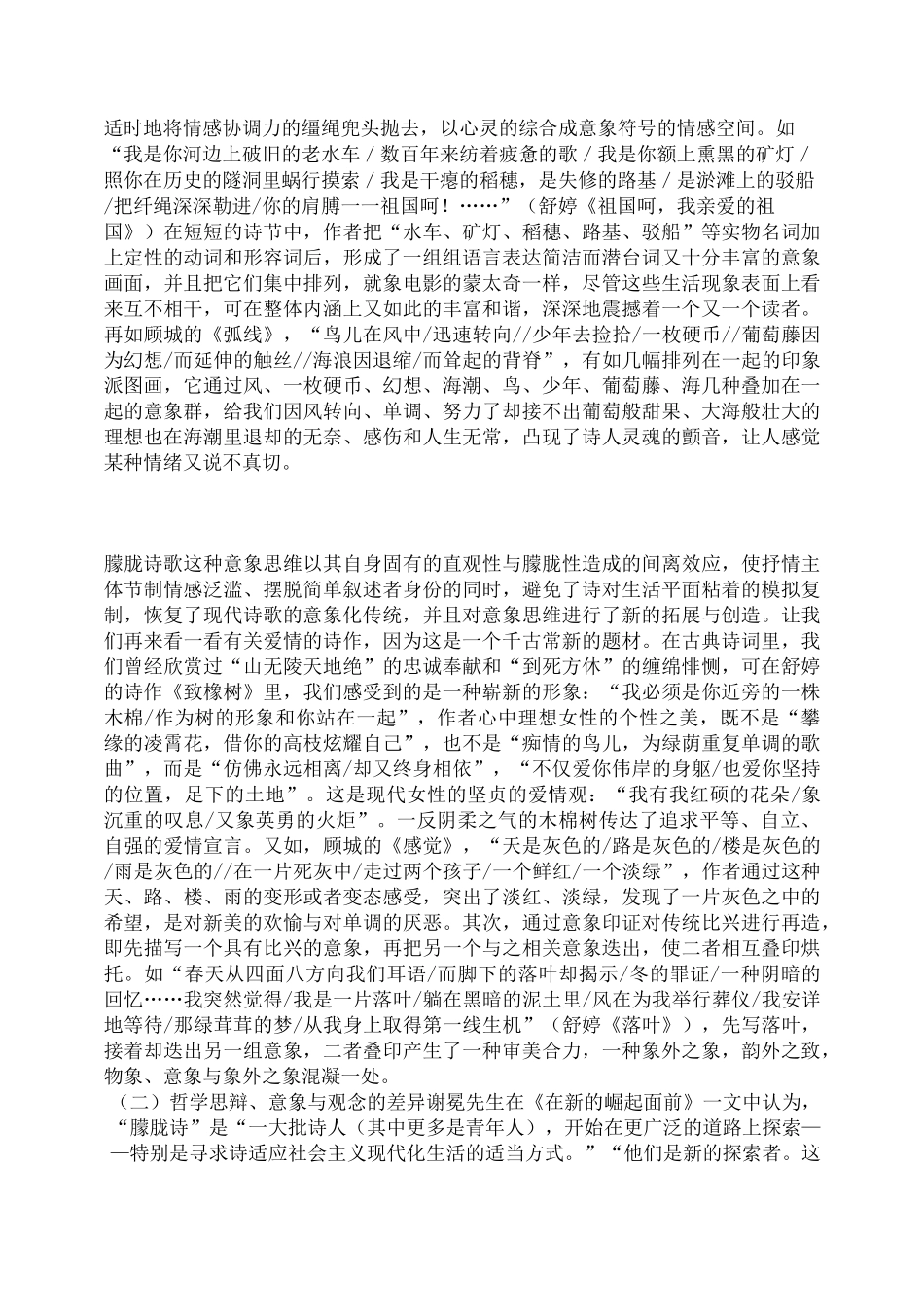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唐文英“朦胧”(ambiguity,又译“模糊”、“晦涩”和“含混”等)是一个本体论范畴。燕卜荪指出,“伟大的诗歌在描写具体的事物时,总是表达出一种普通的情感,总是吸引人们探索人类经验深入的奥妙,这种奥妙越是不可名状,其存在便越不可否认。”[1]也就是说,优秀的诗作所表达的东西都是不可名状的,因此,用清晰明确的语言根本无法将其表达出来,只有用朦胧的语言,才能引导人们去感受和思考语言之外的东西。朦胧诗作为一种新诗潮,一开始便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审美特征。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构成朦胧诗的思想核心,而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和隐喻性,则是朦胧诗艺术表现上的重要特征。朦胧诗是新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流派,是“文革”后期一群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青年(舒婷、北岛、顾城、江河、杨炼等)利用诗歌的形式,对现实进行反思和追求诗歌独立的审美价值的产物。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是的,回顾朦胧诗远去的一路风尘,我们深深意识到,雷同平庸的标准件艺术终于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下面,本文将从朦胧诗的思维方式、文本结构、语言艺术三个方面予以论述之。一、思维方式:诗歌精神的嬗变文革十年断裂的艺术空白为朦胧诗提供了恣意纵横的广阔诗意空间,听命于直觉的驱动,朦胧诗人们顿悟到诗歌它不能镜子般被动地再现外在生活,而应曲笔涉入折射外在生活的心理空间,从而抵达诗歌质的本性,进而对人生、社会、自我进行思考和感悟,从他们灵感迸放出来漫天的绚丽烟花里,此时的诗歌是个“在这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和法制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的界限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仿佛回到宇宙的初创期,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一一于是发生变形。”[2]以此寄托急剧变幻的现实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风暴。(一)灵感迸放出了意象的火花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经过长时间的“冰川”冻结后,灵感像决口的河堤,从冰缝里迸发出来,晶莹、高洁、绚丽……它使朦胧诗人们将意象作为思维活动的主要凭借,进行艺术的感觉、思考和创造。变化莫测的婀娜灵感窜出来时,朦胧诗人们适时地将情感协调力的缰绳兜头抛去,以心灵的综合成意象符号的情感空间。如“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一一祖国呵!……”(舒婷《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在短短的诗节中,作者把“水车、矿灯、稻穗、路基、驳船”等实物名词加上定性的动词和形容词后,形成了一组组语言表达简洁而潜台词又十分丰富的意象画面,并且把它们集中排列,就象电影的蒙太奇一样,尽管这些生活现象表面上看来互不相干,可在整体内涵上又如此的丰富和谐,深深地震撼着一个又一个读者。再如顾城的《弧线》,“鸟儿在风中/迅速转向//少年去捡拾/一枚硬币//葡萄藤因为幻想/而延伸的触丝//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有如几幅排列在一起的印象派图画,它通过风、一枚硬币、幻想、海潮、鸟、少年、葡萄藤、海几种叠加在一起的意象群,给我们因风转向、单调、努力了却接不出葡萄般甜果、大海般壮大的理想也在海潮里退却的无奈、感伤和人生无常,凸现了诗人灵魂的颤音,让人感觉某种情绪又说不真切。朦胧诗歌这种意象思维以其自身固有的直观性与朦胧性造成的间离效应,使抒情主体节制情感泛滥、摆脱简单叙述者身份的同时,避免了诗对生活平面粘着的模拟复制,恢复了现代诗歌的意象化传统,并且对意象思维进行了新的拓展与创造。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有关爱情的诗作,因为这是一个千古常新的题材。在古典诗词里,我们曾经欣赏过“山无陵天地绝”的忠诚奉献和“到死方休”的缠绵悱恻,可在舒婷的诗作《致橡树》里,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崭新的形象:“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作者心中理想女性的个性之美,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