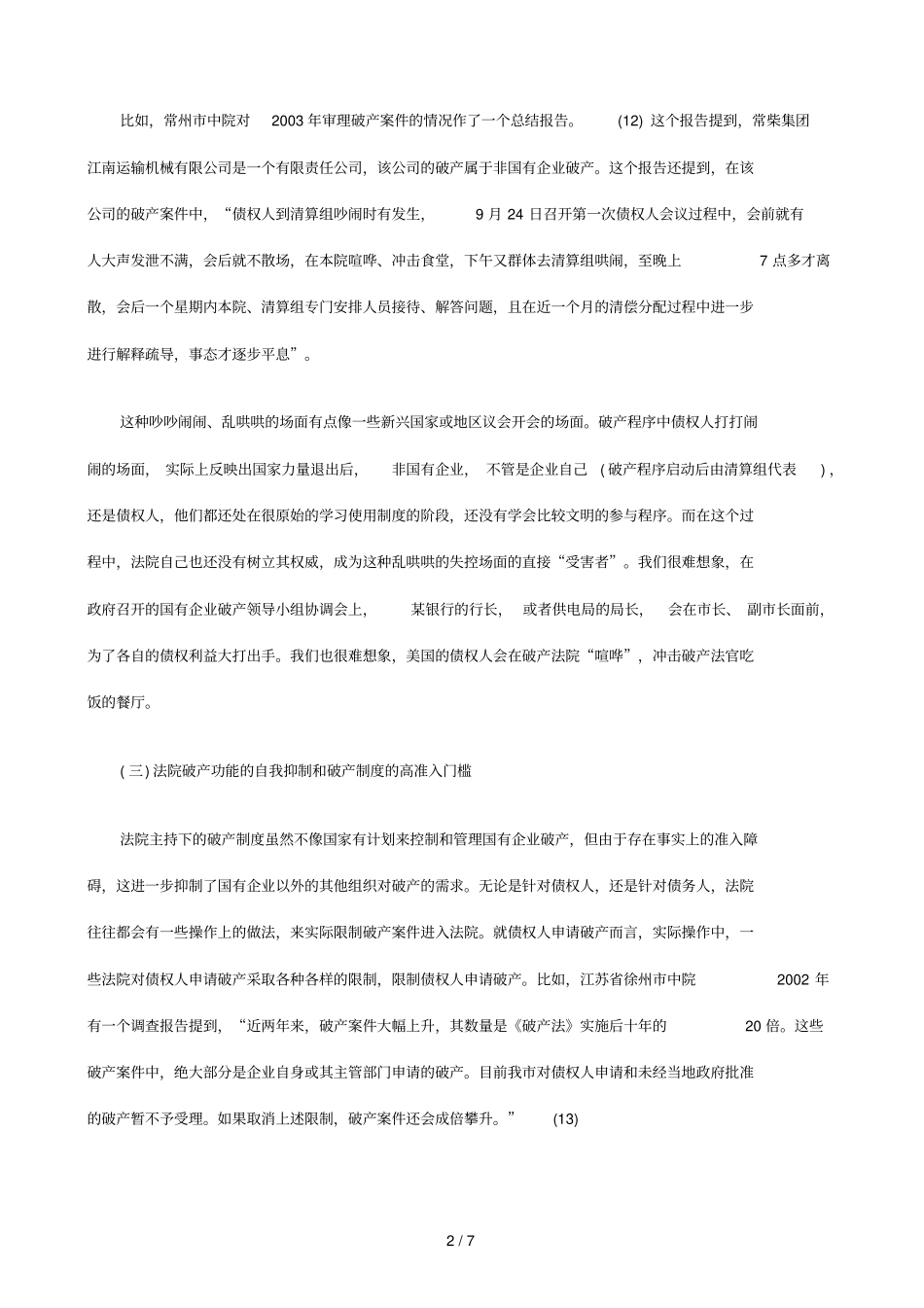1/7为什么执行程序处理破产问题下(二)非国有企业享受不到国家的“制度性补贴”国家对国有企业破产进行管理和控制,直接影响了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银行,对破产制度的需求。那么,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呢?理论上,他们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需求,不受国家对国有企业破产控制的影响。但实际上,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对破产的需求也不高。最近几年,法院每年受理几千件破产案件,大约国有企业破产占一半,另外一半为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的破产案件。之所以其他组织,尤其是私营企业,对破产制度的需求也不是很高,一方面在于这些企业还不够大,整个90年代乃至现在,它们还处在发展时期,对于昂贵的破产制度,这些组织还没有很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计划控制和管理的同时,也在对国有企业的破产进行隐性的“补贴”,而非国有企业却没有这种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对破产制度的需求。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国有企业的破产来看,破产属于整个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环节,破产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工作中的一个部分,破产制度的很多程序不是由法院主导,也不需要破产企业或者其债权人来张罗,而是由政府来组织实施。比如,就组织形态而言,如前所述,从地方到中央,上上下下都有政府负责人牵头成立的破产工作领导小组,其小组成员来自政府各个部门、银行以及法院等司法部门。这类领导小组权限很大,职能很多,大到负责决定哪个企业可以破产,小到负责制定破产预案,职工安置方案等等具体文件。他们实际上起着债权人会议功能、清算组功能,甚至行使破产财产如何分配、债权之间的分配顺序等等类似裁判的职能。因此,绝大部分破产意义上的工作,都是由这个程序承担和完成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破产提供了制度性的补贴。相反,同国有企业相比,其他企业,不管是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或者是其他形式的企业组织,都没有这个便利。召集债权人开个会,组成清算组,这些看似程序性和简单的工作,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报道,介绍在没有政府主导的情况下,破产程序中看似简单的工作如何在实践中变得复杂,乃至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2/7比如,常州市中院对2003年审理破产案件的情况作了一个总结报告。(12)这个报告提到,常柴集团江南运输机械有限公司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破产属于非国有企业破产。这个报告还提到,在该公司的破产案件中,“债权人到清算组吵闹时有发生,9月24日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过程中,会前就有人大声发泄不满,会后就不散场,在本院喧哗、冲击食堂,下午又群体去清算组哄闹,至晚上7点多才离散,会后一个星期内本院、清算组专门安排人员接待、解答问题,且在近一个月的清偿分配过程中进一步进行解释疏导,事态才逐步平息”。这种吵吵闹闹、乱哄哄的场面有点像一些新兴国家或地区议会开会的场面。破产程序中债权人打打闹闹的场面,实际上反映出国家力量退出后,非国有企业,不管是企业自己(破产程序启动后由清算组代表),还是债权人,他们都还处在很原始的学习使用制度的阶段,还没有学会比较文明的参与程序。而在这个过程中,法院自己也还没有树立其权威,成为这种乱哄哄的失控场面的直接“受害者”。我们很难想象,在政府召开的国有企业破产领导小组协调会上,某银行的行长,或者供电局的局长,会在市长、副市长面前,为了各自的债权利益大打出手。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的债权人会在破产法院“喧哗”,冲击破产法官吃饭的餐厅。(三)法院破产功能的自我抑制和破产制度的高准入门槛法院主持下的破产制度虽然不像国家有计划来控制和管理国有企业破产,但由于存在事实上的准入障碍,这进一步抑制了国有企业以外的其他组织对破产的需求。无论是针对债权人,还是针对债务人,法院往往都会有一些操作上的做法,来实际限制破产案件进入法院。就债权人申请破产而言,实际操作中,一些法院对债权人申请破产采取各种各样的限制,限制债权人申请破产。比如,江苏省徐州市中院2002年有一个调查报告提到,“近两年来,破产案件大幅上升,其数量是《破产法》实施后十年的20倍。这些破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