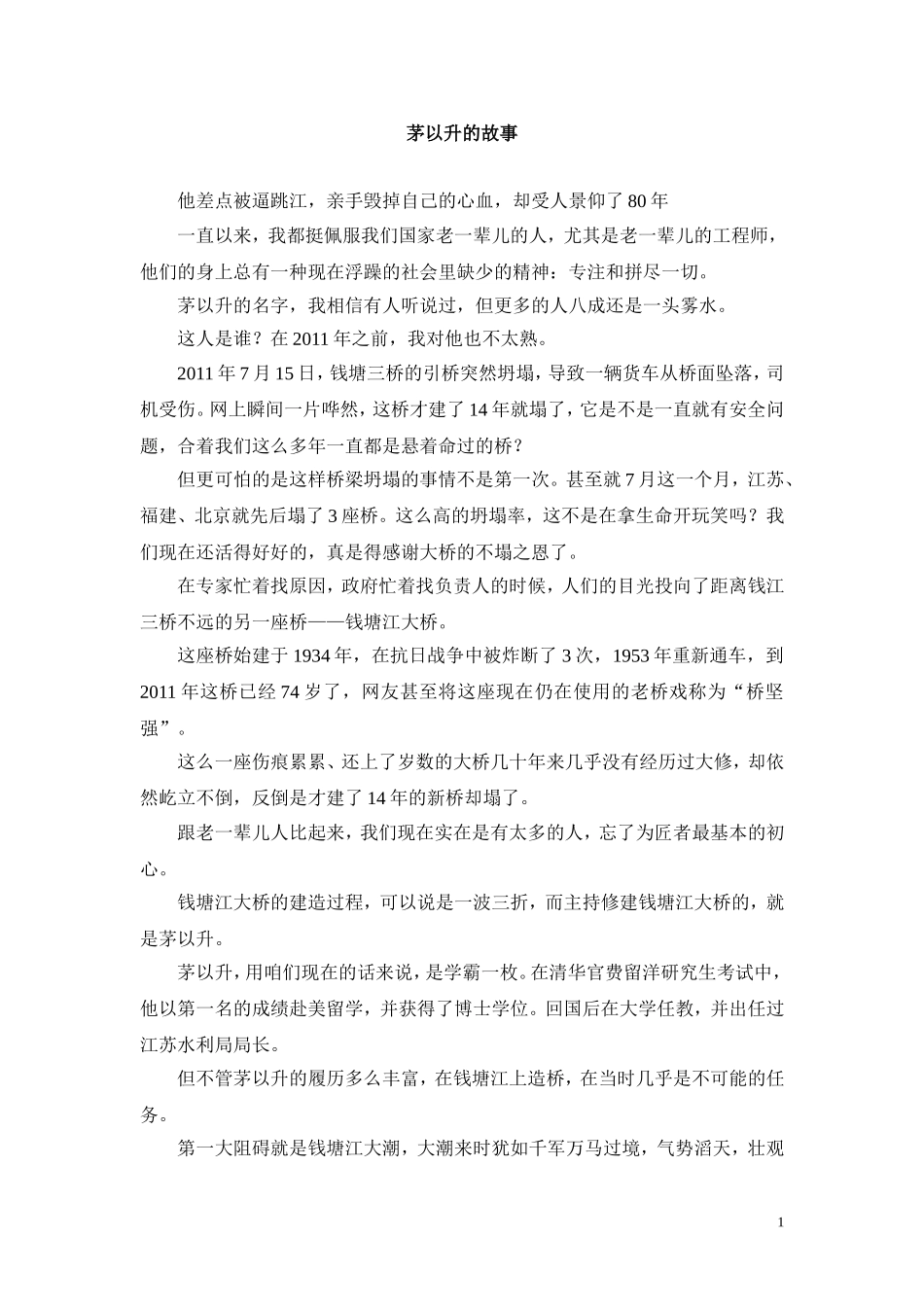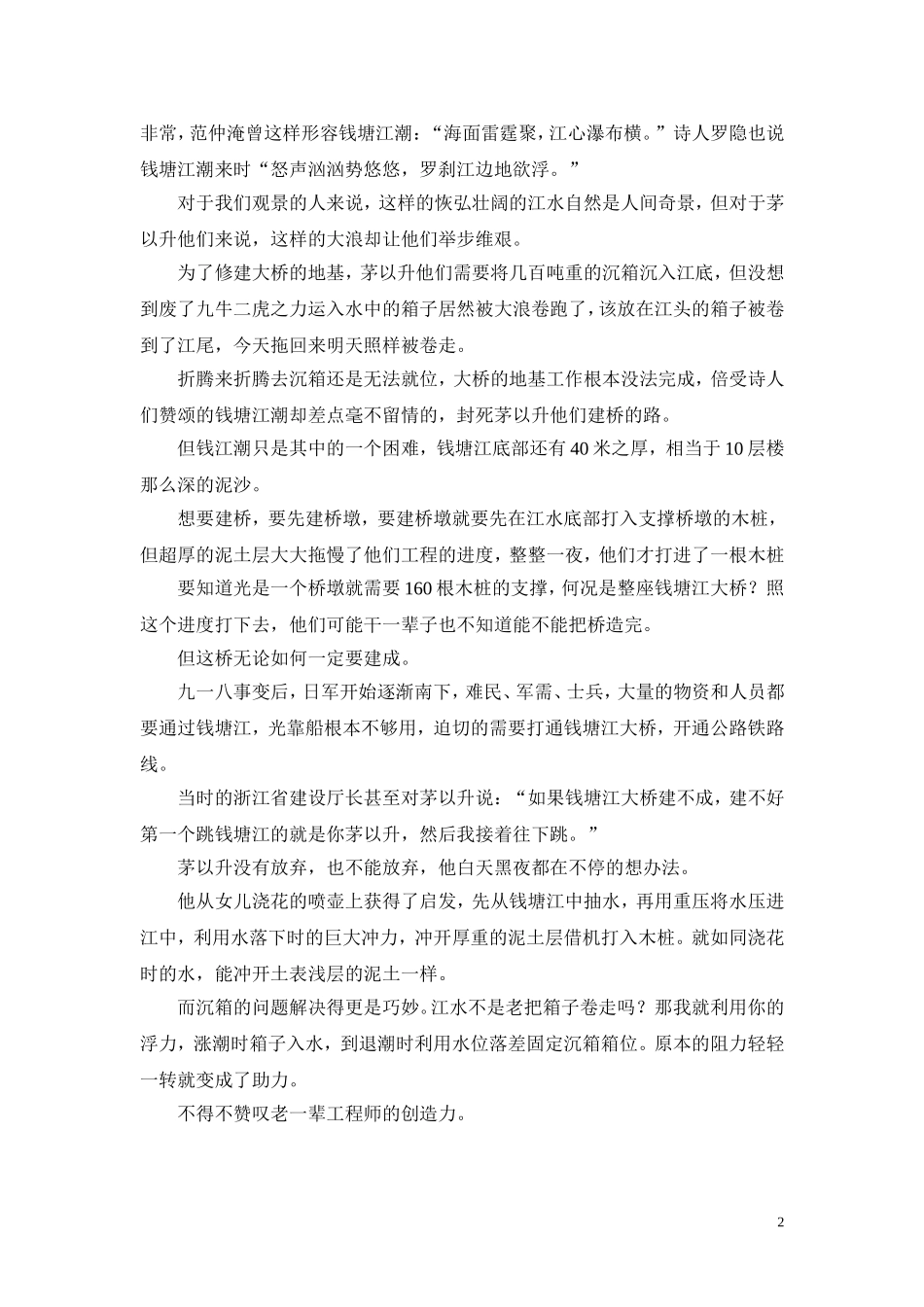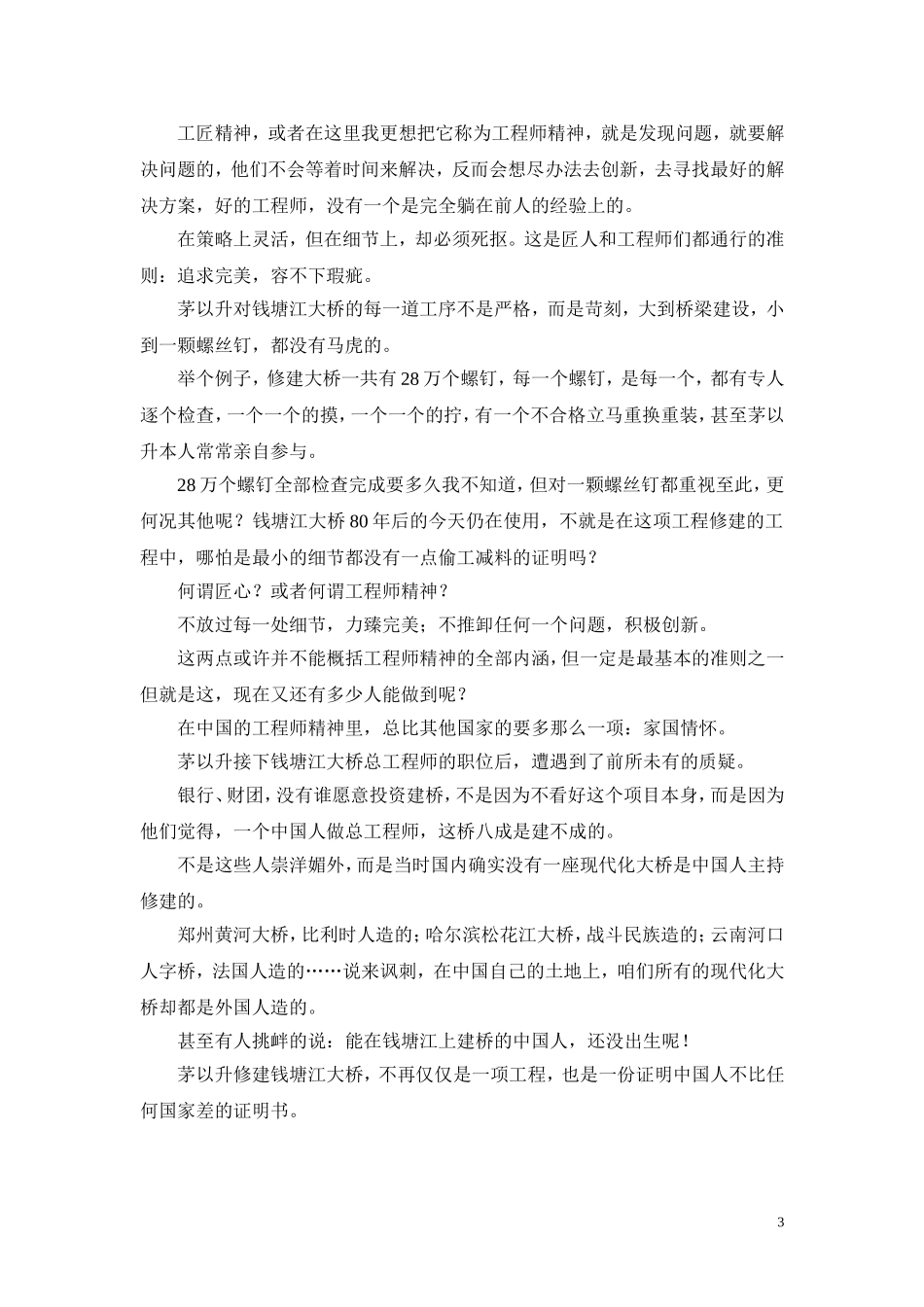茅以升的故事他差点被逼跳江,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却受人景仰了80年一直以来,我都挺佩服我们国家老一辈儿的人,尤其是老一辈儿的工程师,他们的身上总有一种现在浮躁的社会里缺少的精神:专注和拼尽一切。茅以升的名字,我相信有人听说过,但更多的人八成还是一头雾水。这人是谁?在2011年之前,我对他也不太熟。2011年7月15日,钱塘三桥的引桥突然坍塌,导致一辆货车从桥面坠落,司机受伤。网上瞬间一片哗然,这桥才建了14年就塌了,它是不是一直就有安全问题,合着我们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悬着命过的桥?但更可怕的是这样桥梁坍塌的事情不是第一次。甚至就7月这一个月,江苏、福建、北京就先后塌了3座桥。这么高的坍塌率,这不是在拿生命开玩笑吗?我们现在还活得好好的,真是得感谢大桥的不塌之恩了。在专家忙着找原因,政府忙着找负责人的时候,人们的目光投向了距离钱江三桥不远的另一座桥——钱塘江大桥。这座桥始建于1934年,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断了3次,1953年重新通车,到2011年这桥已经74岁了,网友甚至将这座现在仍在使用的老桥戏称为“桥坚强”。这么一座伤痕累累、还上了岁数的大桥几十年来几乎没有经历过大修,却依然屹立不倒,反倒是才建了14年的新桥却塌了。跟老一辈儿人比起来,我们现在实在是有太多的人,忘了为匠者最基本的初心。钱塘江大桥的建造过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的,就是茅以升。茅以升,用咱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学霸一枚。在清华官费留洋研究生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赴美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大学任教,并出任过江苏水利局局长。但不管茅以升的履历多么丰富,在钱塘江上造桥,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第一大阻碍就是钱塘江大潮,大潮来时犹如千军万马过境,气势滔天,壮观1非常,范仲淹曾这样形容钱塘江潮:“海面雷霆聚,江心瀑布横。”诗人罗隐也说钱塘江潮来时“怒声汹汹势悠悠,罗刹江边地欲浮。”对于我们观景的人来说,这样的恢弘壮阔的江水自然是人间奇景,但对于茅以升他们来说,这样的大浪却让他们举步维艰。为了修建大桥的地基,茅以升他们需要将几百吨重的沉箱沉入江底,但没想到废了九牛二虎之力运入水中的箱子居然被大浪卷跑了,该放在江头的箱子被卷到了江尾,今天拖回来明天照样被卷走。折腾来折腾去沉箱还是无法就位,大桥的地基工作根本没法完成,倍受诗人们赞颂的钱塘江潮却差点毫不留情的,封死茅以升他们建桥的路。但钱江潮只是其中的一个困难,钱塘江底部还有40米之厚,相当于10层楼那么深的泥沙。想要建桥,要先建桥墩,要建桥墩就要先在江水底部打入支撑桥墩的木桩,但超厚的泥土层大大拖慢了他们工程的进度,整整一夜,他们才打进了一根木桩要知道光是一个桥墩就需要160根木桩的支撑,何况是整座钱塘江大桥?照这个进度打下去,他们可能干一辈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把桥造完。但这桥无论如何一定要建成。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逐渐南下,难民、军需、士兵,大量的物资和人员都要通过钱塘江,光靠船根本不够用,迫切的需要打通钱塘江大桥,开通公路铁路线。当时的浙江省建设厅长甚至对茅以升说:“如果钱塘江大桥建不成,建不好第一个跳钱塘江的就是你茅以升,然后我接着往下跳。”茅以升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他白天黑夜都在不停的想办法。他从女儿浇花的喷壶上获得了启发,先从钱塘江中抽水,再用重压将水压进江中,利用水落下时的巨大冲力,冲开厚重的泥土层借机打入木桩。就如同浇花时的水,能冲开土表浅层的泥土一样。而沉箱的问题解决得更是巧妙。江水不是老把箱子卷走吗?那我就利用你的浮力,涨潮时箱子入水,到退潮时利用水位落差固定沉箱箱位。原本的阻力轻轻一转就变成了助力。不得不赞叹老一辈工程师的创造力。2工匠精神,或者在这里我更想把它称为工程师精神,就是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的,他们不会等着时间来解决,反而会想尽办法去创新,去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好的工程师,没有一个是完全躺在前人的经验上的。在策略上灵活,但在细节上,却必须死抠。这是匠人和工程师们都通行的准则:追求完美,容不下瑕疵。茅以升对钱塘江大桥的每一道工序不是严格,而是苛刻,大到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