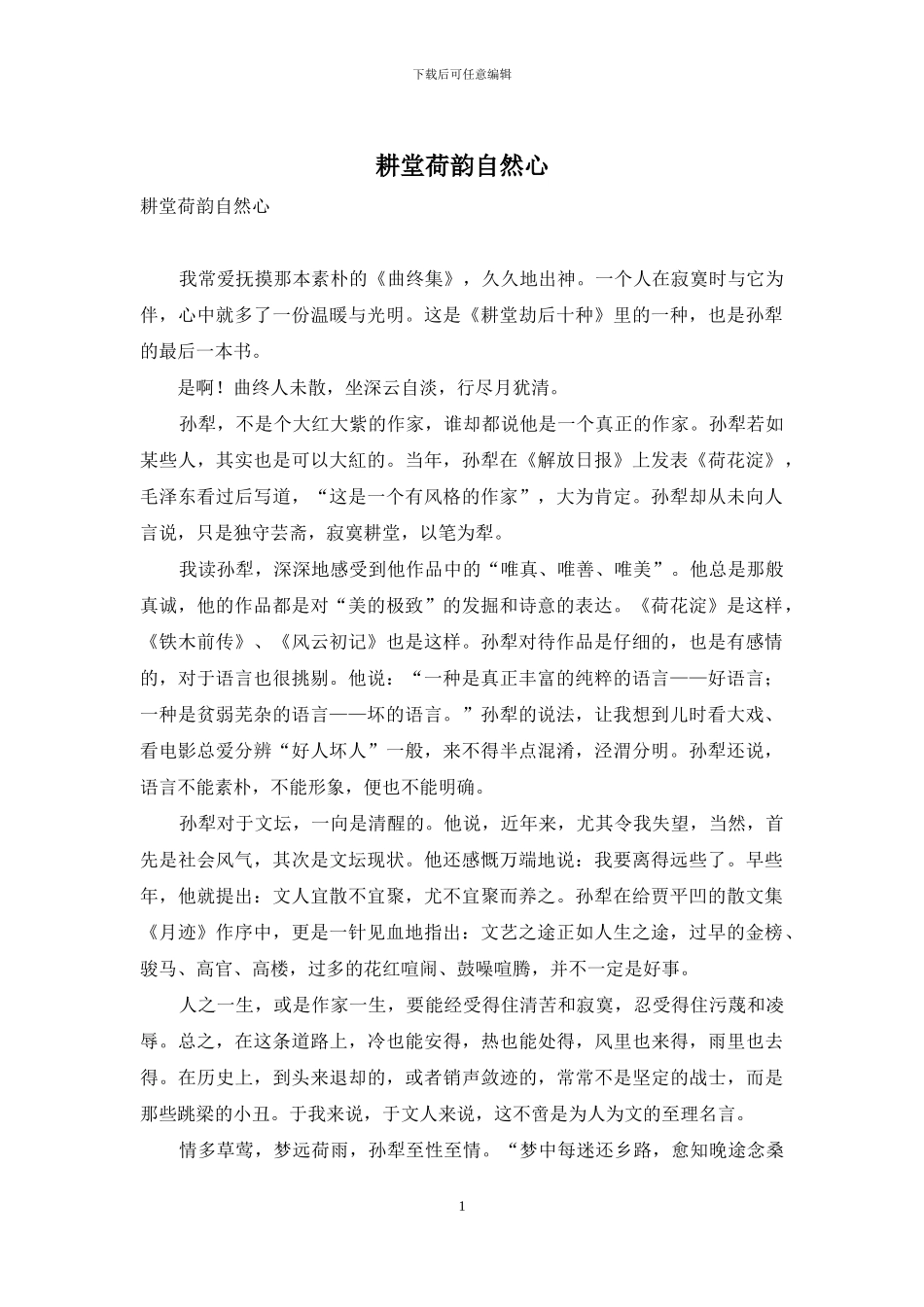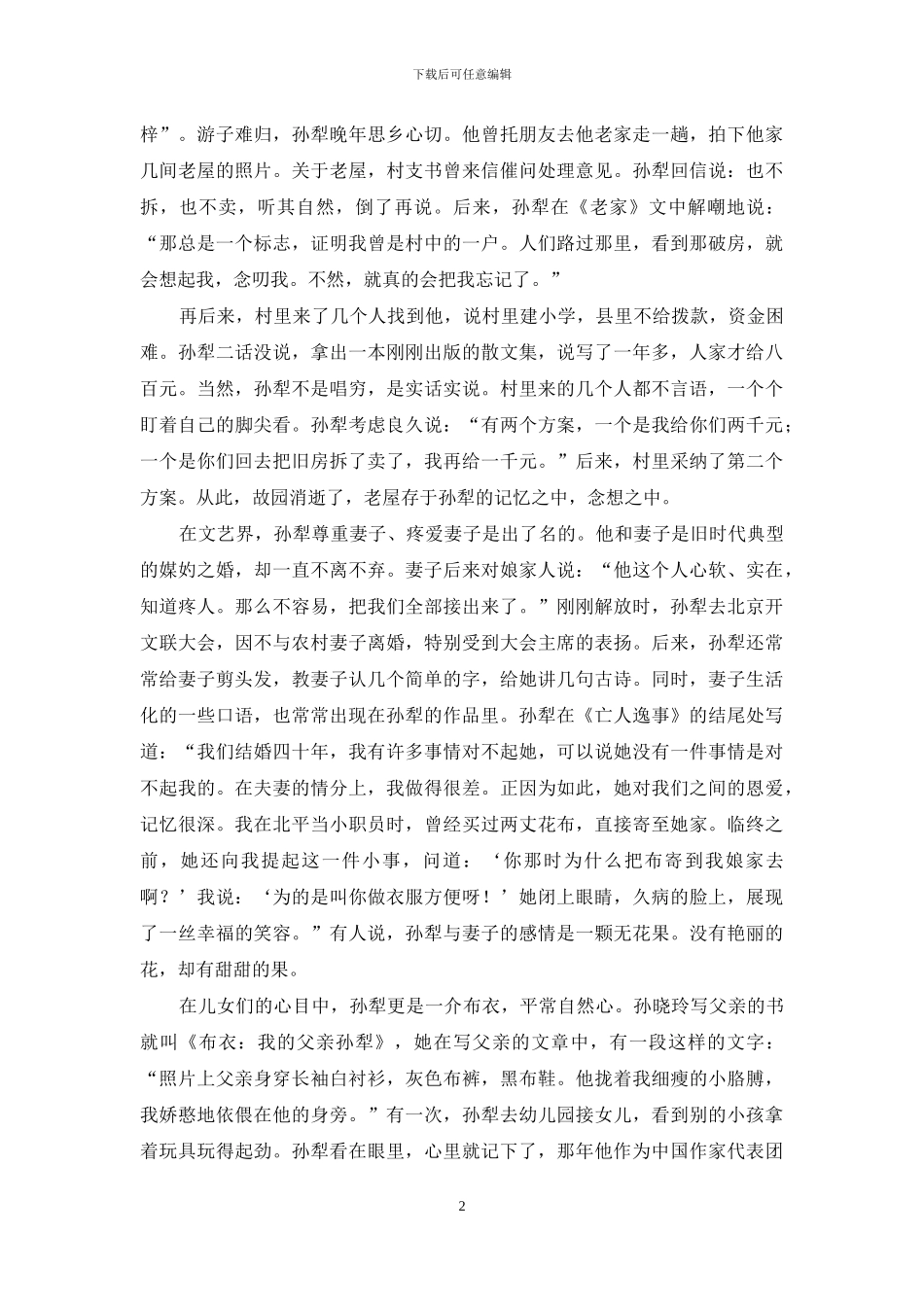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耕堂荷韵自然心耕堂荷韵自然心 我常爱抚摸那本素朴的《曲终集》,久久地出神。一个人在寂寞时与它为伴,心中就多了一份温暖与光明。这是《耕堂劫后十种》里的一种,也是孙犁的最后一本书。 是啊!曲终人未散,坐深云自淡,行尽月犹清。 孙犁,不是个大红大紫的作家,谁却都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孙犁若如某些人,其实也是可以大紅的。当年,孙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荷花淀》,毛泽东看过后写道,“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大为肯定。孙犁却从未向人言说,只是独守芸斋,寂寞耕堂,以笔为犁。 我读孙犁,深深地感受到他作品中的“唯真、唯善、唯美”。他总是那般真诚,他的作品都是对“美的极致”的发掘和诗意的表达。《荷花淀》是这样,《铁木前传》、《风云初记》也是这样。孙犁对待作品是仔细的,也是有感情的,对于语言也很挑剔。他说:“一种是真正丰富的纯粹的语言——好语言;一种是贫弱芜杂的语言——坏的语言。”孙犁的说法,让我想到儿时看大戏、看电影总爱分辨“好人坏人”一般,来不得半点混淆,泾渭分明。孙犁还说,语言不能素朴,不能形象,便也不能明确。 孙犁对于文坛,一向是清醒的。他说,近年来,尤其令我失望,当然,首先是社会风气,其次是文坛现状。他还感慨万端地说:我要离得远些了。早些年,他就提出:文人宜散不宜聚,尤不宜聚而养之。孙犁在给贾平凹的散文集《月迹》作序中,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喧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住清苦和寂寞,忍受得住污蔑和凌辱。总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销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于我来说,于文人来说,这不啻是为人为文的至理名言。 情多草莺,梦远荷雨,孙犁至性至情。“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梓”。游子难归,孙犁晚年思乡心切。他曾托朋友去他老家走一趟,拍下他家几间老屋的照片。关于老屋,村支书曾来信催问处理意见。孙犁回信说:也不拆,也不卖,听其自然,倒了再说。后来,孙犁在《老家》文中解嘲地说:“那总是一个标志,证明我曾是村中的一户。人们路过那里,看到那破房,就会想起我,念叨我。不然,就真的会把我忘记了。” 再后来,村里来了几个人找到他,说村里建小学,县里不给拨款,资金困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