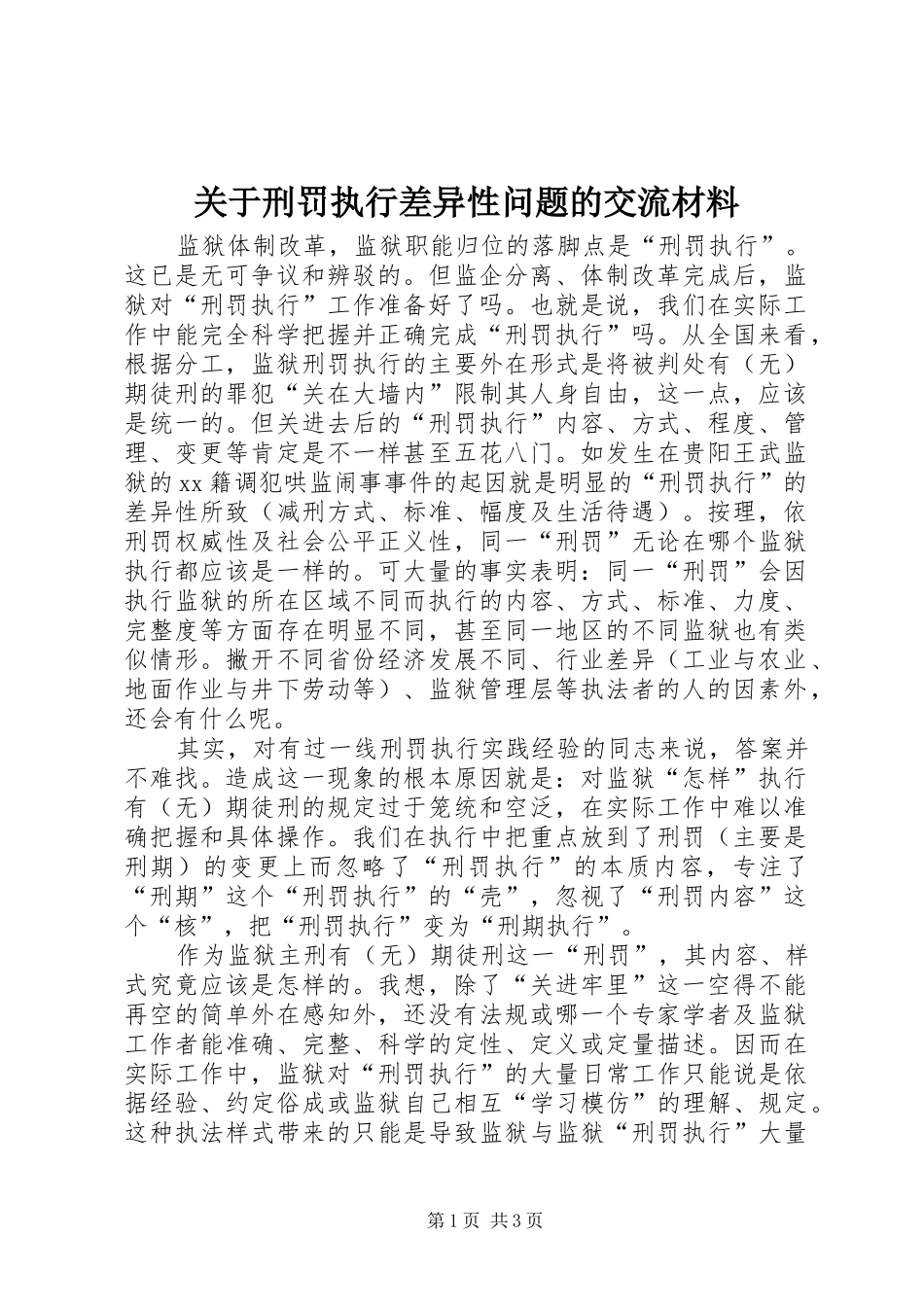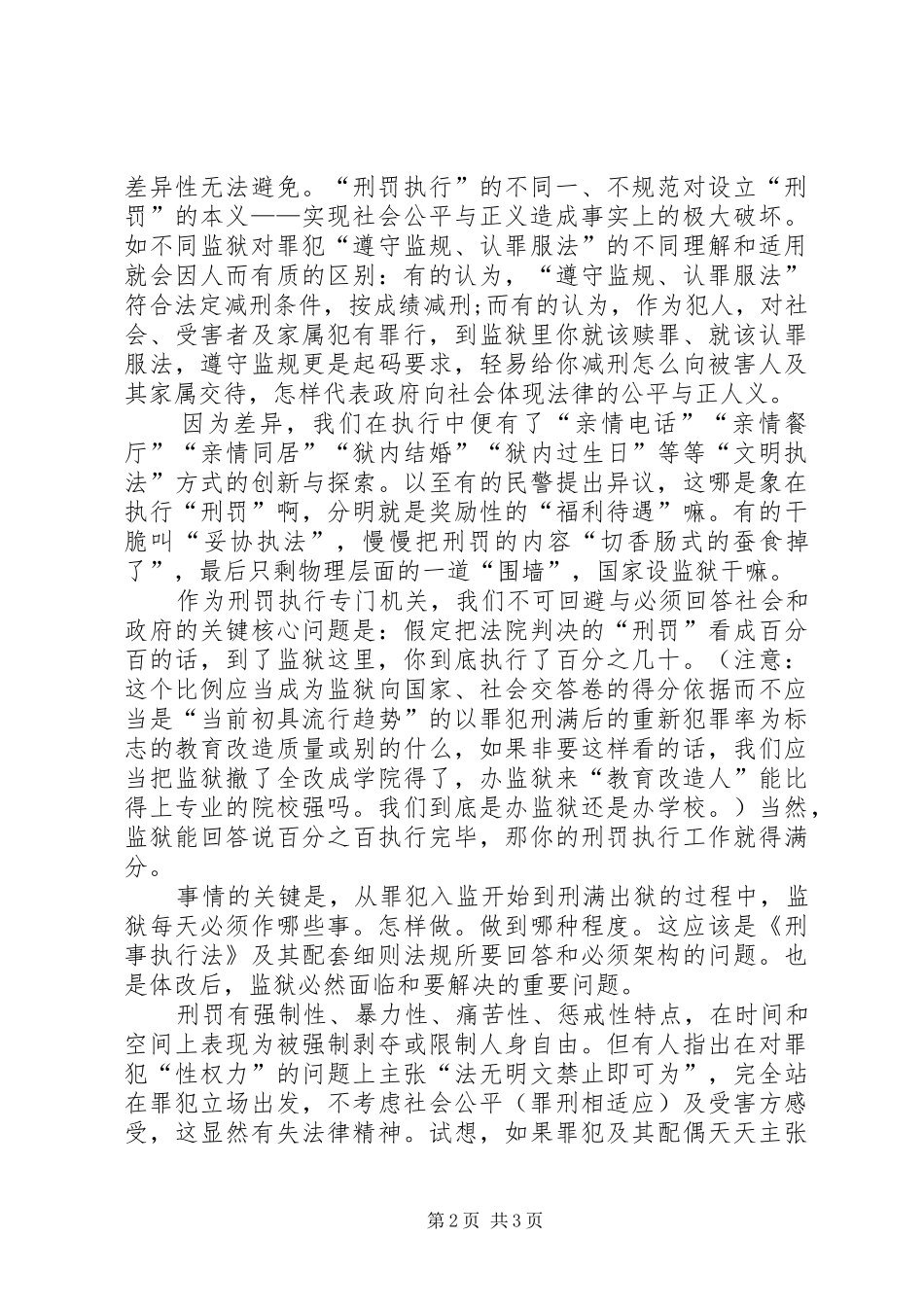关于刑罚执行差异性问题的交流材料监狱体制改革,监狱职能归位的落脚点是“刑罚执行”。这已是无可争议和辨驳的。但监企分离、体制改革完成后,监狱对“刑罚执行”工作准备好了吗。也就是说,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完全科学把握并正确完成“刑罚执行”吗。从全国来看,根据分工,监狱刑罚执行的主要外在形式是将被判处有(无)期徒刑的罪犯“关在大墙内”限制其人身自由,这一点,应该是统一的。但关进去后的“刑罚执行”内容、方式、程度、管理、变更等肯定是不一样甚至五花八门。如发生在贵阳王武监狱的xx籍调犯哄监闹事事件的起因就是明显的“刑罚执行”的差异性所致(减刑方式、标准、幅度及生活待遇)。按理,依刑罚权威性及社会公平正义性,同一“刑罚”无论在哪个监狱执行都应该是一样的。可大量的事实表明:同一“刑罚”会因执行监狱的所在区域不同而执行的内容、方式、标准、力度、完整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同,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监狱也有类似情形。撇开不同省份经济发展不同、行业差异(工业与农业、地面作业与井下劳动等)、监狱管理层等执法者的人的因素外,还会有什么呢。其实,对有过一线刑罚执行实践经验的同志来说,答案并不难找。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对监狱“怎样”执行有(无)期徒刑的规定过于笼统和空泛,在实际工作中难以准确把握和具体操作。我们在执行中把重点放到了刑罚(主要是刑期)的变更上而忽略了“刑罚执行”的本质内容,专注了“刑期”这个“刑罚执行”的“壳”,忽视了“刑罚内容”这个“核”,把“刑罚执行”变为“刑期执行”。作为监狱主刑有(无)期徒刑这一“刑罚”,其内容、样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我想,除了“关进牢里”这一空得不能再空的简单外在感知外,还没有法规或哪一个专家学者及监狱工作者能准确、完整、科学的定性、定义或定量描述。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监狱对“刑罚执行”的大量日常工作只能说是依据经验、约定俗成或监狱自己相互“学习模仿”的理解、规定。这种执法样式带来的只能是导致监狱与监狱“刑罚执行”大量第1页共3页差异性无法避免。“刑罚执行”的不同一、不规范对设立“刑罚”的本义——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造成事实上的极大破坏。如不同监狱对罪犯“遵守监规、认罪服法”的不同理解和适用就会因人而有质的区别:有的认为,“遵守监规、认罪服法”符合法定减刑条件,按成绩减刑;而有的认为,作为犯人,对社会、受害者及家属犯有罪行,到监狱里你就该赎罪、就该认罪服法,遵守监规更是起码要求,轻易给你减刑怎么向被害人及其家属交待,怎样代表政府向社会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人义。因为差异,我们在执行中便有了“亲情电话”“亲情餐厅”“亲情同居”“狱内结婚”“狱内过生日”等等“文明执法”方式的创新与探索。以至有的民警提出异议,这哪是象在执行“刑罚”啊,分明就是奖励性的“福利待遇”嘛。有的干脆叫“妥协执法”,慢慢把刑罚的内容“切香肠式的蚕食掉了”,最后只剩物理层面的一道“围墙”,国家设监狱干嘛。作为刑罚执行专门机关,我们不可回避与必须回答社会和政府的关键核心问题是:假定把法院判决的“刑罚”看成百分百的话,到了监狱这里,你到底执行了百分之几十。(注意:这个比例应当成为监狱向国家、社会交答卷的得分依据而不应当是“当前初具流行趋势”的以罪犯刑满后的重新犯罪率为标志的教育改造质量或别的什么,如果非要这样看的话,我们应当把监狱撤了全改成学院得了,办监狱来“教育改造人”能比得上专业的院校强吗。我们到底是办监狱还是办学校。)当然,监狱能回答说百分之百执行完毕,那你的刑罚执行工作就得满分。事情的关键是,从罪犯入监开始到刑满出狱的过程中,监狱每天必须作哪些事。怎样做。做到哪种程度。这应该是《刑事执行法》及其配套细则法规所要回答和必须架构的问题。也是体改后,监狱必然面临和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刑罚有强制性、暴力性、痛苦性、惩戒性特点,在时间和空间上表现为被强制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但有人指出在对罪犯“性权力”的问题上主张“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完全站在罪犯立场出发,不考虑社会公平(罪刑相适应)及受害方感受,这显然有失法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