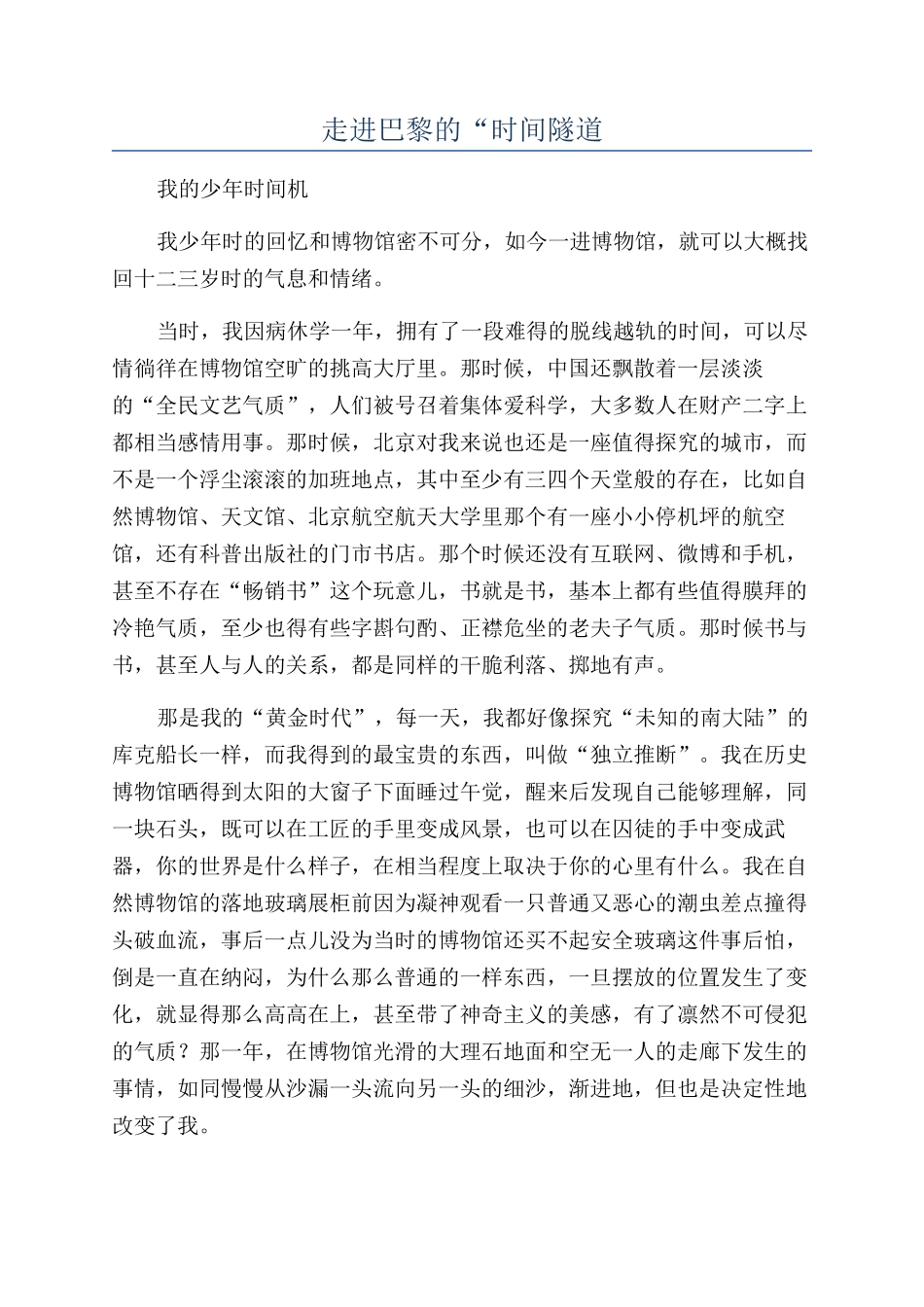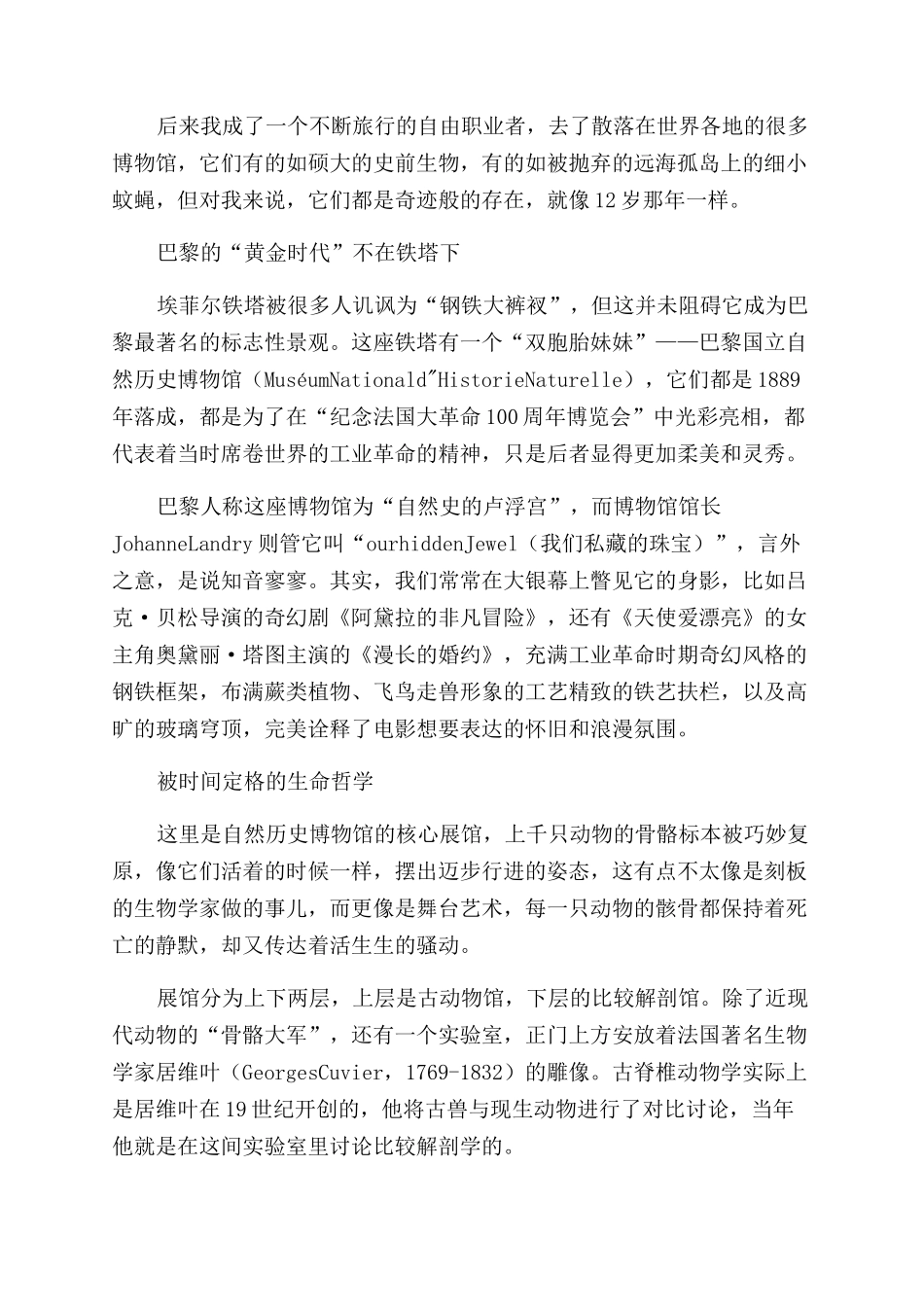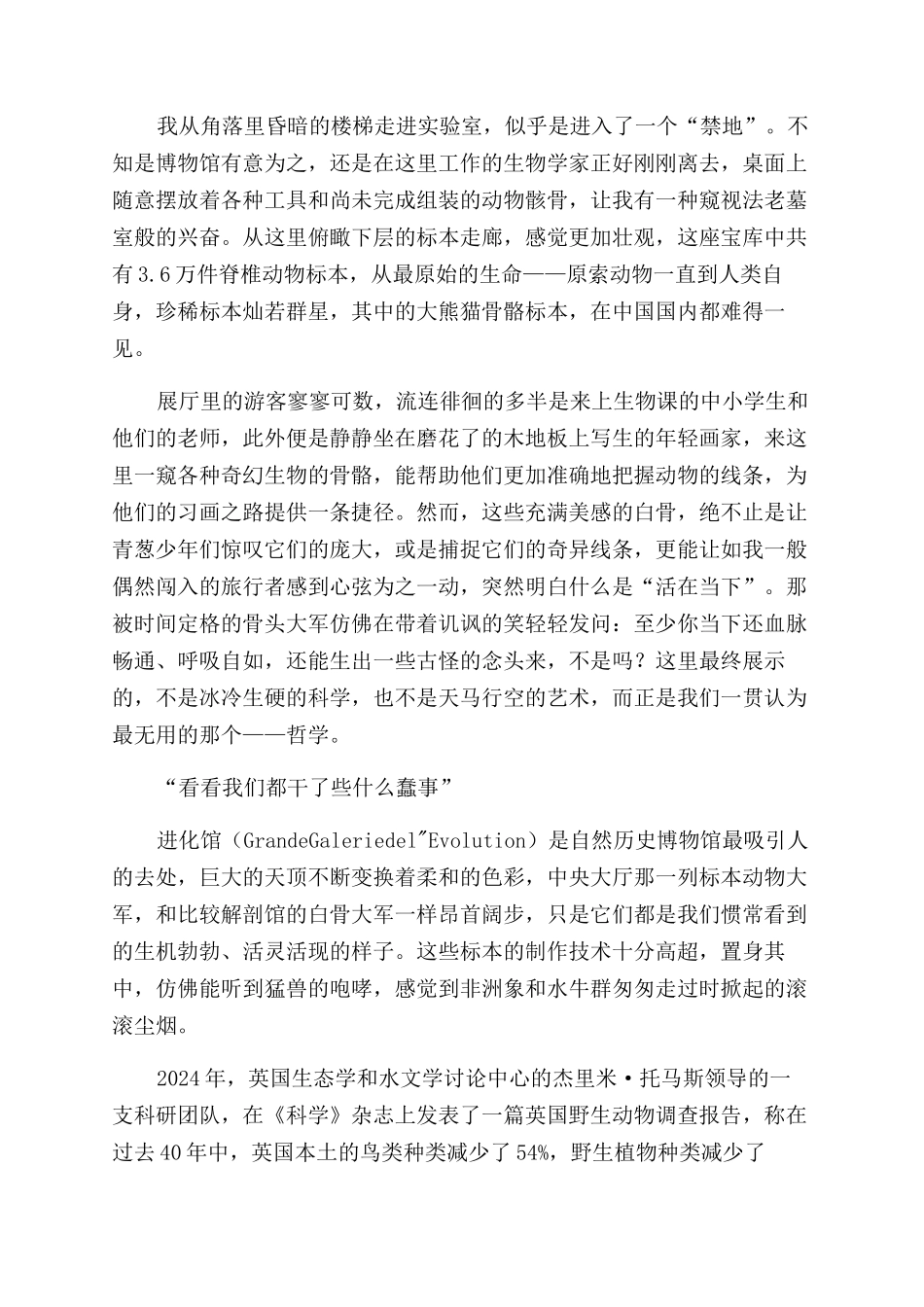走进巴黎的“时间隧道我的少年时间机我少年时的回忆和博物馆密不可分,如今一进博物馆,就可以大概找回十二三岁时的气息和情绪。当时,我因病休学一年,拥有了一段难得的脱线越轨的时间,可以尽情徜徉在博物馆空旷的挑高大厅里。那时候,中国还飘散着一层淡淡的“全民文艺气质”,人们被号召着集体爱科学,大多数人在财产二字上都相当感情用事。那时候,北京对我来说也还是一座值得探究的城市,而不是一个浮尘滚滚的加班地点,其中至少有三四个天堂般的存在,比如自然博物馆、天文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里那个有一座小小停机坪的航空馆,还有科普出版社的门市书店。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微博和手机,甚至不存在“畅销书”这个玩意儿,书就是书,基本上都有些值得膜拜的冷艳气质,至少也得有些字斟句酌、正襟危坐的老夫子气质。那时候书与书,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同样的干脆利落、掷地有声。那是我的“黄金时代”,每一天,我都好像探究“未知的南大陆”的库克船长一样,而我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叫做“独立推断”。我在历史博物馆晒得到太阳的大窗子下面睡过午觉,醒来后发现自己能够理解,同一块石头,既可以在工匠的手里变成风景,也可以在囚徒的手中变成武器,你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心里有什么。我在自然博物馆的落地玻璃展柜前因为凝神观看一只普通又恶心的潮虫差点撞得头破血流,事后一点儿没为当时的博物馆还买不起安全玻璃这件事后怕,倒是一直在纳闷,为什么那么普通的一样东西,一旦摆放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就显得那么高高在上,甚至带了神奇主义的美感,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气质?那一年,在博物馆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和空无一人的走廊下发生的事情,如同慢慢从沙漏一头流向另一头的细沙,渐进地,但也是决定性地改变了我。后来我成了一个不断旅行的自由职业者,去了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馆,它们有的如硕大的史前生物,有的如被抛弃的远海孤岛上的细小蚊蝇,但对我来说,它们都是奇迹般的存在,就像 12 岁那年一样。巴黎的“黄金时代”不在铁塔下埃菲尔铁塔被很多人讥讽为“钢铁大裤衩”,但这并未阻碍它成为巴黎最著名的标志性景观。这座铁塔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MuséumNationald"HistorieNaturelle),它们都是 1889年落成,都是为了在“纪念法国大革命 100 周年博览会”中光彩亮相,都代表着当时席卷世界的工业革命的精神,只是后者显得更加柔美和灵秀。巴黎人称这座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