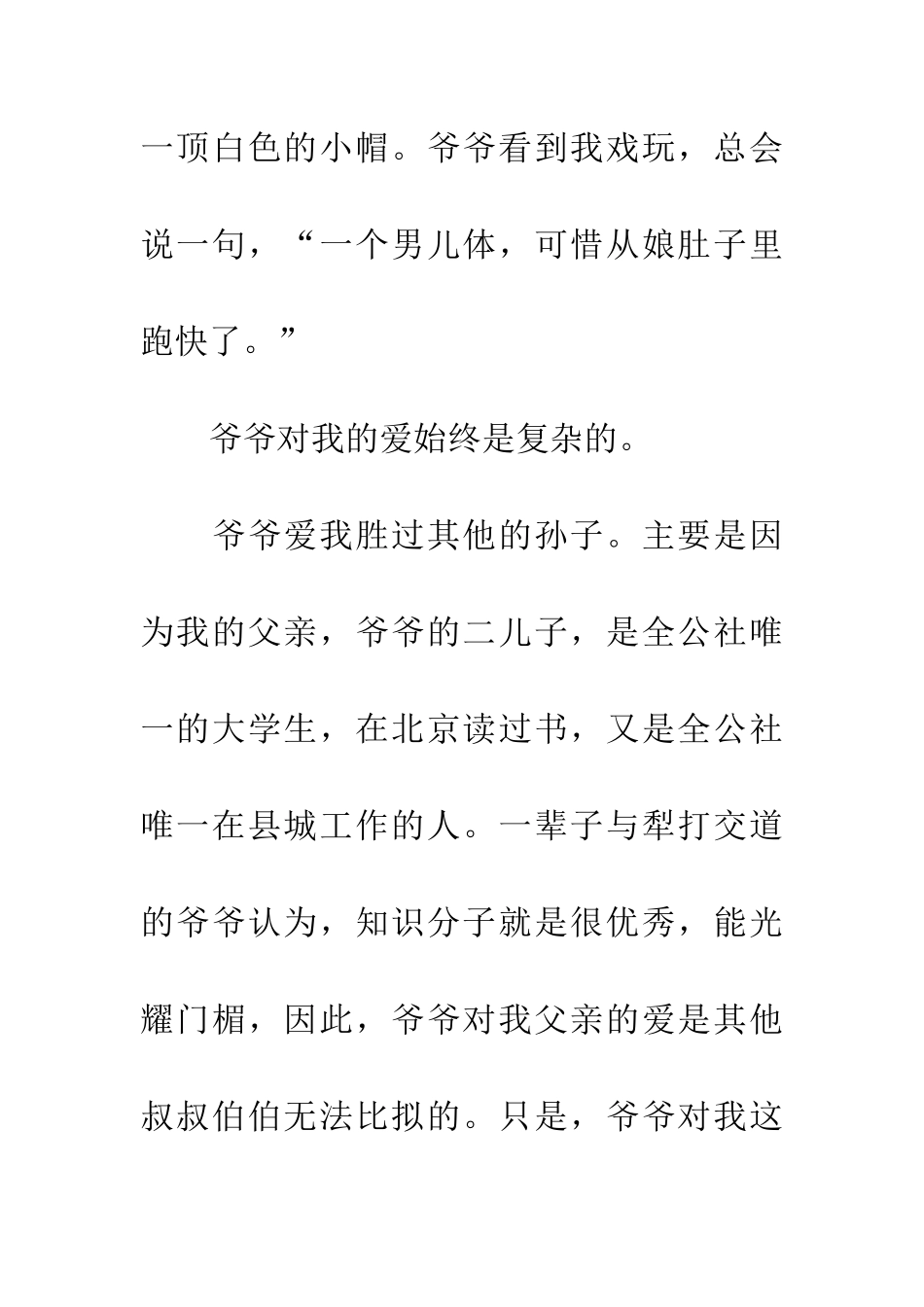老家屋檐上的冰棱 飘雪了,想起老家屋檐的长长的冰凌我不由得生出许多的留恋与悲伤。 我的故乡位于山脚,三十年前还是一个好大的宅子。曾祖父健在,小爷与爷爷的房子没有分开,叔叔、伯伯都住在宅子的右偏房,好喧闹。只要空中飘着团团雪花,我和堂兄们就会踩高跷,雪地网鸟,弹弓捉雀……在大马山守林子的爷爷也会留在家里,他穿一身白色的袍子,常年戴一顶白色的小帽。爷爷看到我戏玩,总会说一句,“一个男儿体,可惜从娘肚子里跑快了。” 爷爷对我的爱始终是复杂的。 爷爷爱我胜过其他的孙子。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爷爷的二儿子,是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在北京读过书,又是全公社唯一在县城工作的人。一辈子与犁打交道的爷爷认为,知识分子就是很优秀,能光耀门楣,因此,爷爷对我父亲的爱是其他叔叔伯伯无法比拟的。只是,爷爷对我这个孙子总感到有那么一些遗憾,或许,我真是“跑快”了。 我的爷爷还是很疼我的。他不是一个很细心的人,也不是很多话的老人,但是每次从大马山回来,一定会在衣兜里装一小把“鸡脚儿”,这是一种植物的根,很甜,清香。我的爷爷没有钱给我买一粒糖他感到很内疚,总是每天都挖这种山中的植物来表达他的爱心。 最难忘的是,我两岁多点,奶奶因为我吃了一个准备换油盐钱的柿饼打了我,爷爷知道了,马上拿一个柿饼放在我手里看我哽咽地吃着柿饼,他也落了泪…… 我的儿童时代虽然很清苦,三餐常是一碗稀粥,一大碗腌菜,由于爷爷的爱,我却感到儿时是欢乐的。 后来,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公社修水渠,开山路,爷爷跌在了施工场地的坚石上,满头鲜血。家里没有钱看病,我父亲坚持接他到县医院,他又怕花钱。那一年冬天,他只能在家中呆着,没有办法守林子了。他常常晚上因头痛而吵得几个屋都不安宁,甚至到前院的林子里乱砍。渐渐地爷爷变得爱发脾气,爱摔东西,人们都说爷爷得了精神病。但是,爷爷看到我时,从来没有发过一次火,也不摔东西他总是爱用粗糙的大手抚摸我。 爷爷的病越来越厉害,一日不如一日更难得吃一点东西。我也很少被奶奶准许接近爷爷,间或,我走到爷爷身边,听到爷爷自言自语地说一些我不太懂的话,“只有这个孙儿是不能送我走的”,随后就是一声叹息。没过多少日子,他就那么痛苦地去了。 我那时很小,看到很多人在堂屋里小声地哭泣,一些像爷爷一样穿白袍,戴白帽的“师傅”张罗着,我的堂兄妹都可以到爷爷的“床”边去,连还在吃奶的小堂妹也可以看看爷爷。可是,我却不能去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