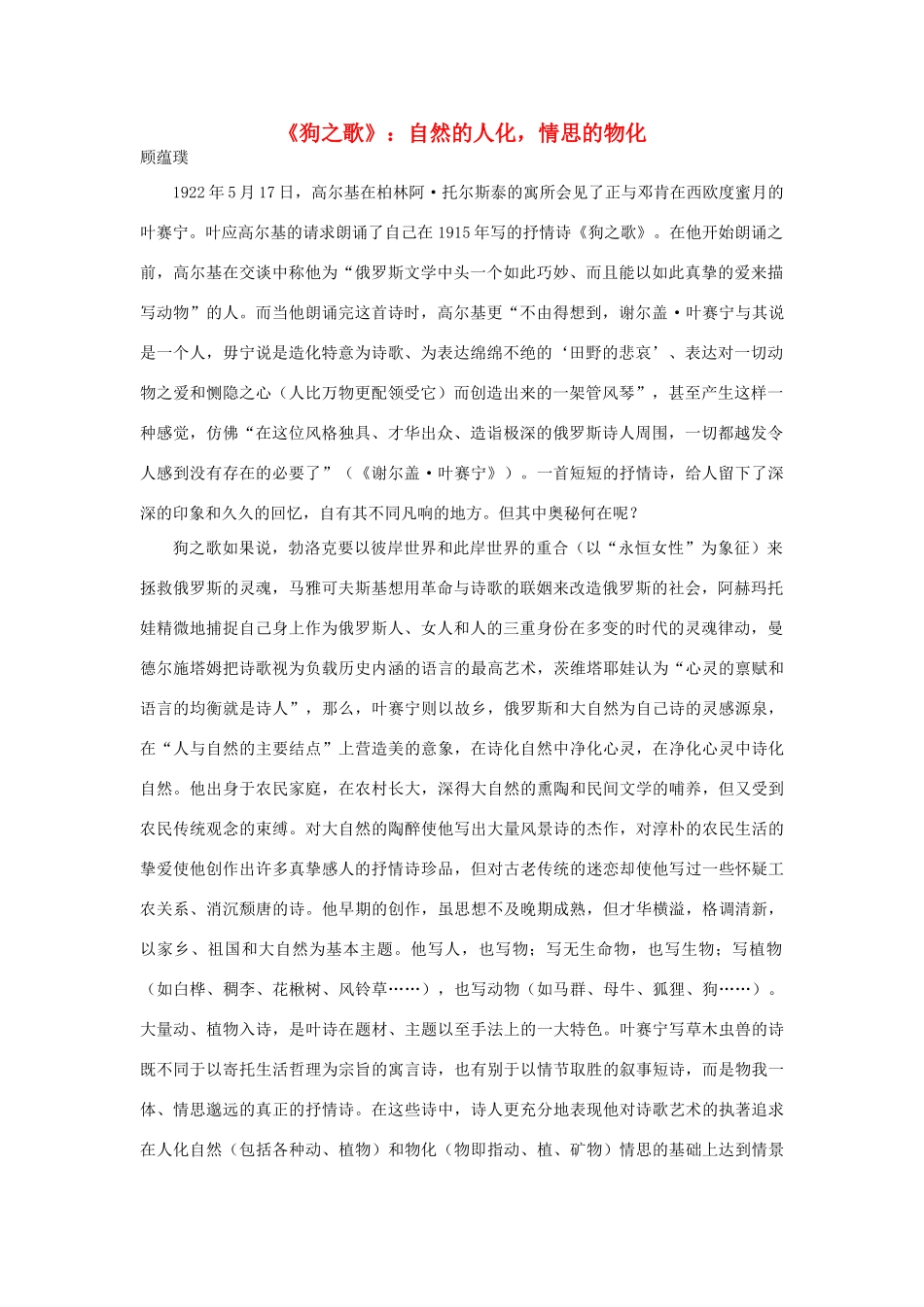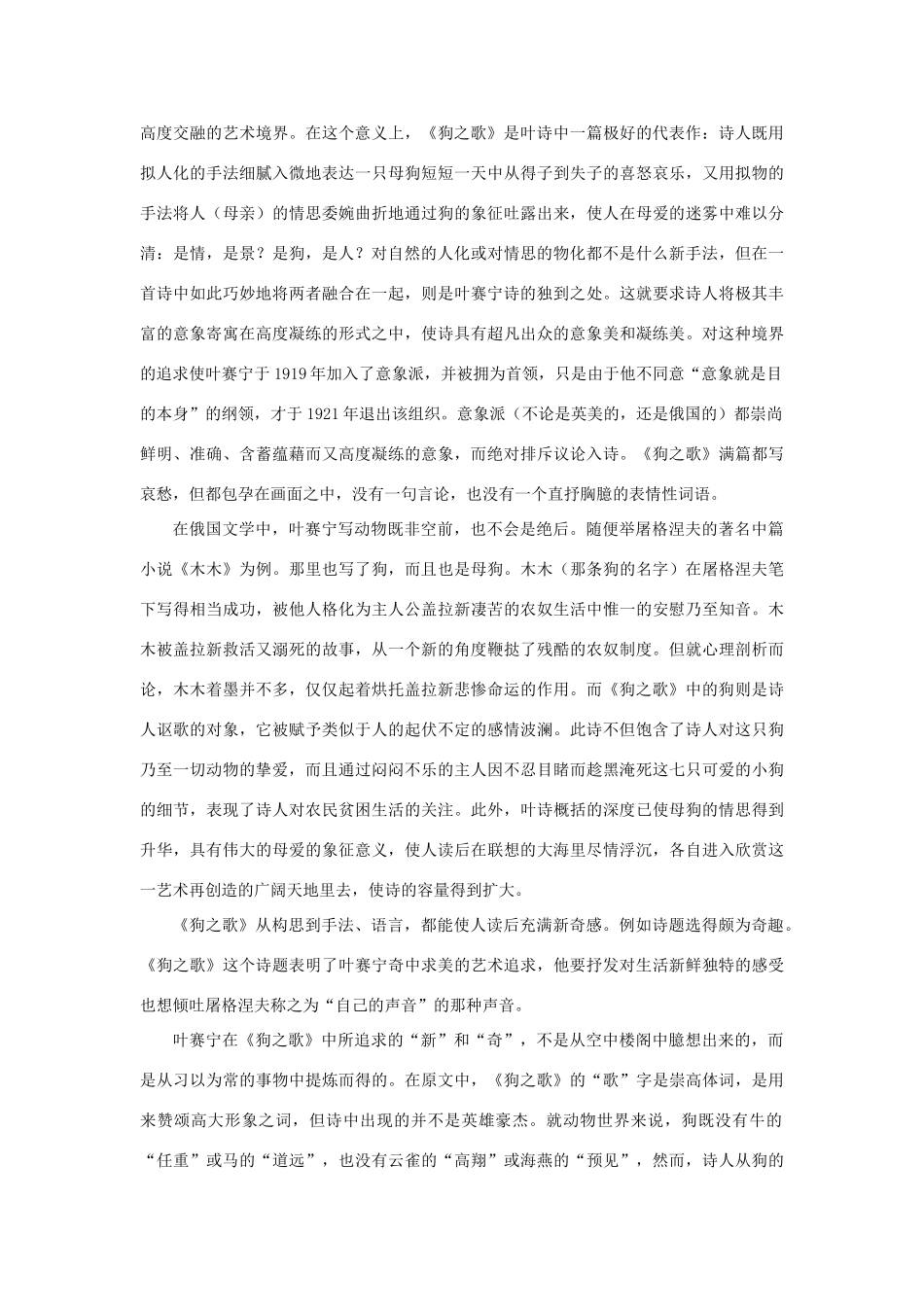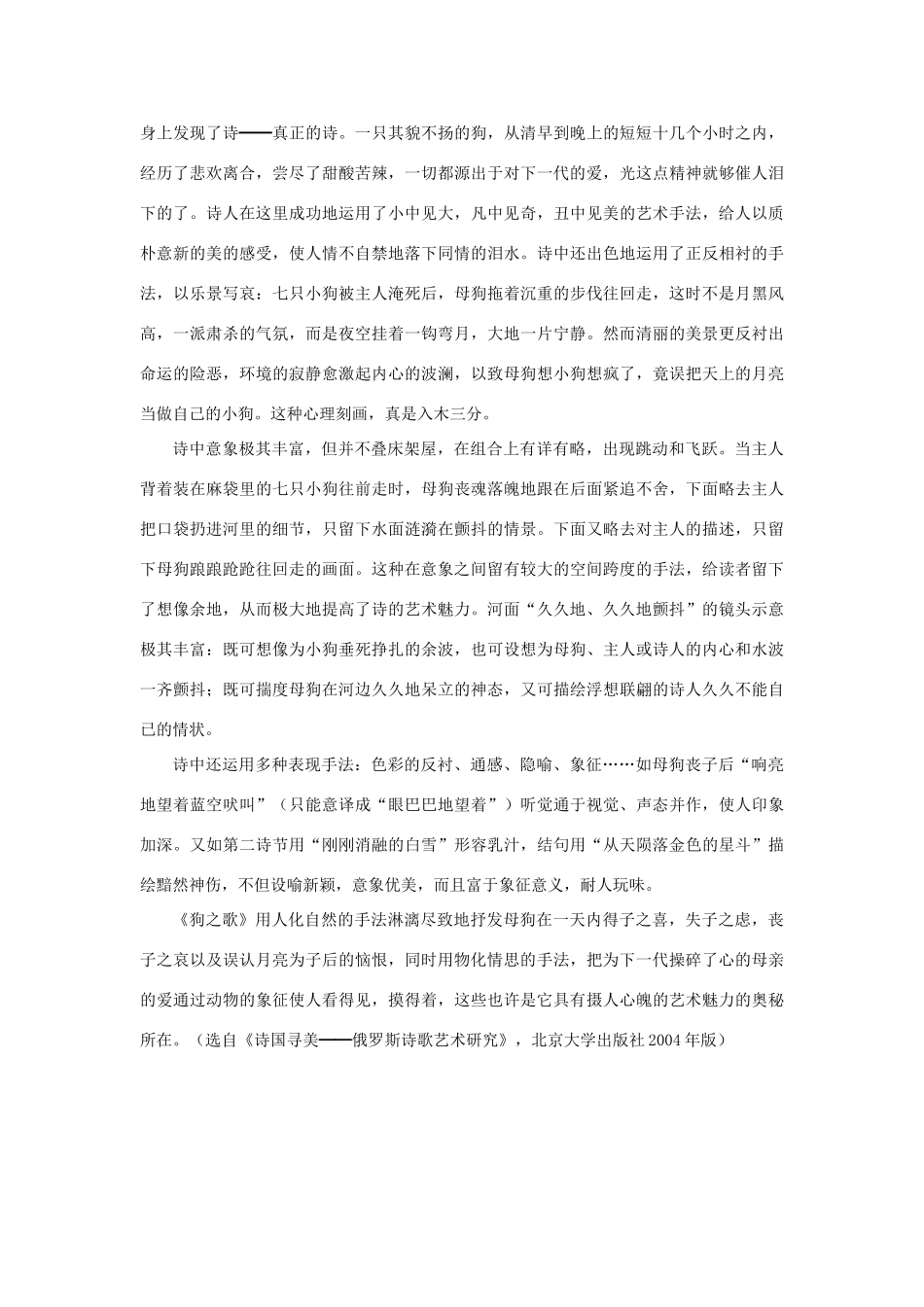《狗之歌》:自然的人化,情思的物化顾蕴璞1922 年 5 月 17 日,高尔基在柏林阿·托尔斯泰的寓所会见了正与邓肯在西欧度蜜月的叶赛宁。叶应高尔基的请求朗诵了自己在 1915 年写的抒情诗《狗之歌》。在他开始朗诵之前,高尔基在交谈中称他为“俄罗斯文学中头一个如此巧妙、而且能以如此真挚的爱来描写动物”的人。而当他朗诵完这首诗时,高尔基更“不由得想到,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毋宁说是造化特意为诗歌、为表达绵绵不绝的‘田野的悲哀’、表达对一切动物之爱和恻隐之心(人比万物更配领受它)而创造出来的一架管风琴”,甚至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在这位风格独具、才华出众、造诣极深的俄罗斯诗人周围,一切都越发令人感到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谢尔盖·叶赛宁》)。一首短短的抒情诗,给人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和久久的回忆,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但其中奥秘何在呢?狗之歌如果说,勃洛克要以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重合(以“永恒女性”为象征)来拯救俄罗斯的灵魂,马雅可夫斯基想用革命与诗歌的联姻来改造俄罗斯的社会,阿赫玛托娃精微地捕捉自己身上作为俄罗斯人、女人和人的三重身份在多变的时代的灵魂律动,曼德尔施塔姆把诗歌视为负载历史内涵的语言的最高艺术,茨维塔耶娃认为“心灵的禀赋和语言的均衡就是诗人”,那么,叶赛宁则以故乡,俄罗斯和大自然为自己诗的灵感源泉,在“人与自然的主要结点”上营造美的意象,在诗化自然中净化心灵,在净化心灵中诗化自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深得大自然的熏陶和民间文学的哺养,但又受到农民传统观念的束缚。对大自然的陶醉使他写出大量风景诗的杰作,对淳朴的农民生活的挚爱使他创作出许多真挚感人的抒情诗珍品,但对古老传统的迷恋却使他写过一些怀疑工农关系、消沉颓唐的诗。他早期的创作,虽思想不及晚期成熟,但才华横溢,格调清新,以家乡、祖国和大自然为基本主题。他写人,也写物;写无生命物,也写生物;写植物(如白桦、稠李、花楸树、风铃草……),也写动物(如马群、母牛、狐狸、狗……)。大量动、植物入诗,是叶诗在题材、主题以至手法上的一大特色。叶赛宁写草木虫兽的诗既不同于以寄托生活哲理为宗旨的寓言诗,也有别于以情节取胜的叙事短诗,而是物我一体、情思邈远的真正的抒情诗。在这些诗中,诗人更充分地表现他对诗歌艺术的执著追求在人化自然(包括各种动、植物)和物化(物即指动、植、矿物)情思的基础上达到情景高度交融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