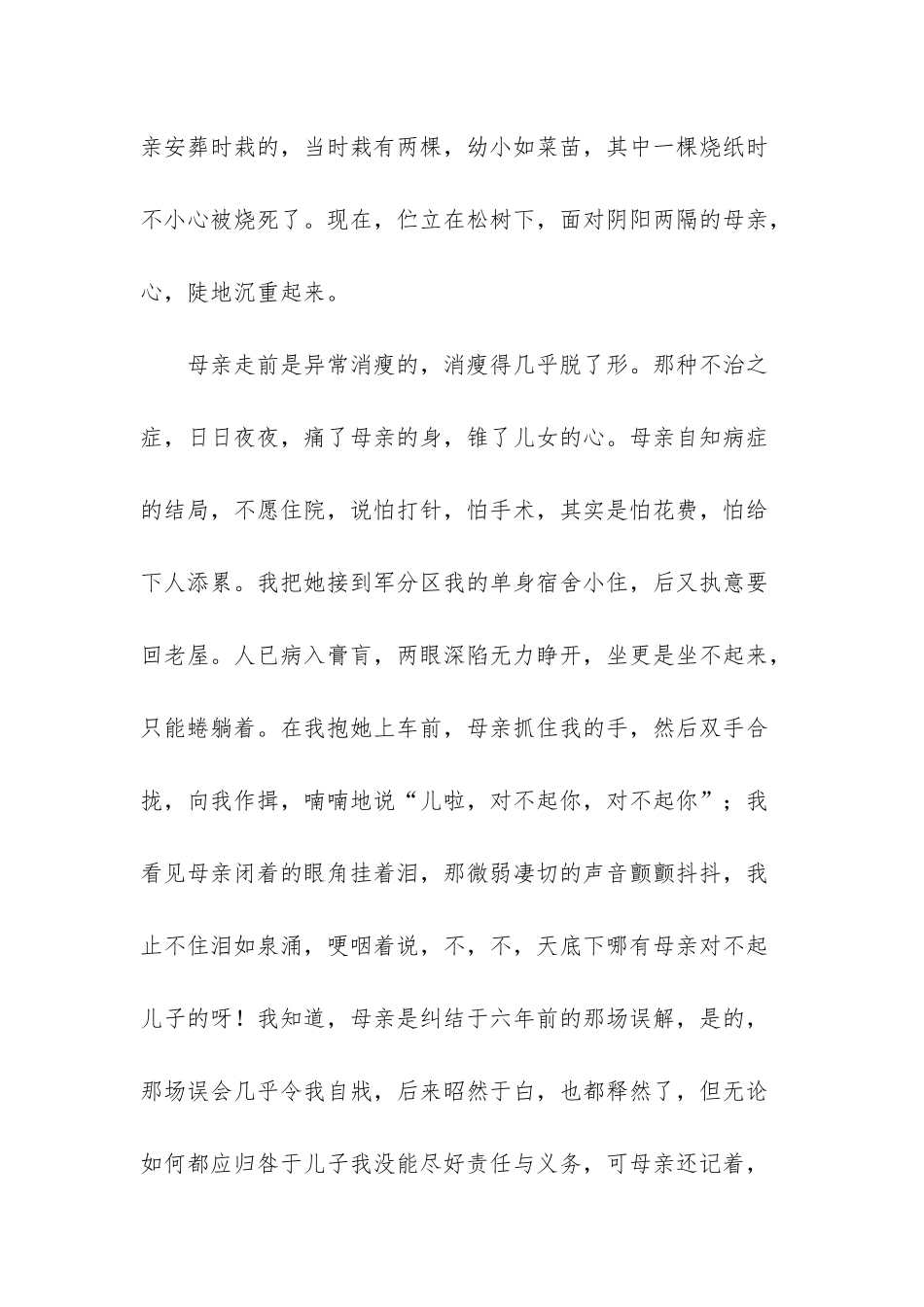【心祭的优美散文】优美的散文段落 腊月二十一,儿子开车送我去往鼓山祭祀。我的父母就安息在这座山的南坡。 祭祀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风习,是活着的人敬奉亡人的挽礼。每年的清明、冬至和春节前夕,是传统的例行祭扫时日,谁都会在心里念起。 这个冬至,辛卯年的冬至,因了琐务难脱身,亦缘于慵懒不想动,便没赴祖坟祭祀,寻思距春节反正只有一个月,合在一起办算了。这样想着,中午时分正在厨房煮饭烧菜,忽地头晕,几乎发跄,不禁心下觳觫,难道冥冥中父母在责备吗?转念一思,不觉哑然,嗨,大概是自己高血压反应吧。 虚惊归虚惊,这倒使我对春节前的祭祀益发郑重起来。早早定下了日子,预备下丰厚的冥币。可是行前出了个小意外,天气变异,将近个把月没落雨了,二十晚上却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梦里梦外老是担心次日野外燃不着火。好在翌日雨住了,谢天谢地。 车子停在一个叫莲蓬嘴的村头,我让儿子留在亲戚家等候,独自向墓地方向走去。 山坡平缓,遍地的野草茂密如絮,深可没膝;丛丛簇簇的灌木和杂树星罗棋布,毫无规则,恣意而又张扬;曾经的小路只能透过稍稍凹陷的草沟线条,依稀辨别。二十多年前绝非此番景象,那时乡下困扰于贫,山上的荒草和灌木成了半壁的燃料来源,然而现如今,农村普遍烧起了液化气,连煤炭也舍而弃之,对荒草之类就更不屑一顾了,于是自然渐渐回到原始状貌,蓬勃起了它原有的野性与生命。那些曾经凸显的大大小小的坟茔,悄然隐没在草木间,似乎沉底于历史深处。 我先到母亲的墓地祭祀。母亲的坟和其他的坟一样,不到近前是看不见的,但坟边有一个标记——一棵足有四丈多高的松树,比周围的树都高,老远就可辨认得清。松树是 1990 年母亲安葬时栽的,当时栽有两棵,幼小如菜苗,其中一棵烧纸时不小心被烧死了。现在,伫立在松树下,面对阴阳两隔的母亲,心,陡地沉重起来。 母亲走前是异常消瘦的,消瘦得几乎脱了形。那种不治之症,日日夜夜,痛了母亲的身,锥了儿女的心。母亲自知病症的结局,不愿住院,说怕打针,怕手术,其实是怕花费,怕给下人添累。我把她接到军分区我的单身宿舍小住,后又执意要回老屋。人已病入膏肓,两眼深陷无力睁开,坐更是坐不起来,只能蜷躺着。在我抱她上车前,母亲抓住我的手,然后双手合拢,向我作揖,喃喃地说“儿啦,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我看见母亲闭着的眼角挂着泪,那微弱凄切的声音颤颤抖抖,我止不住泪如泉涌,哽咽着说,不,不,天底下哪有母亲对不起儿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