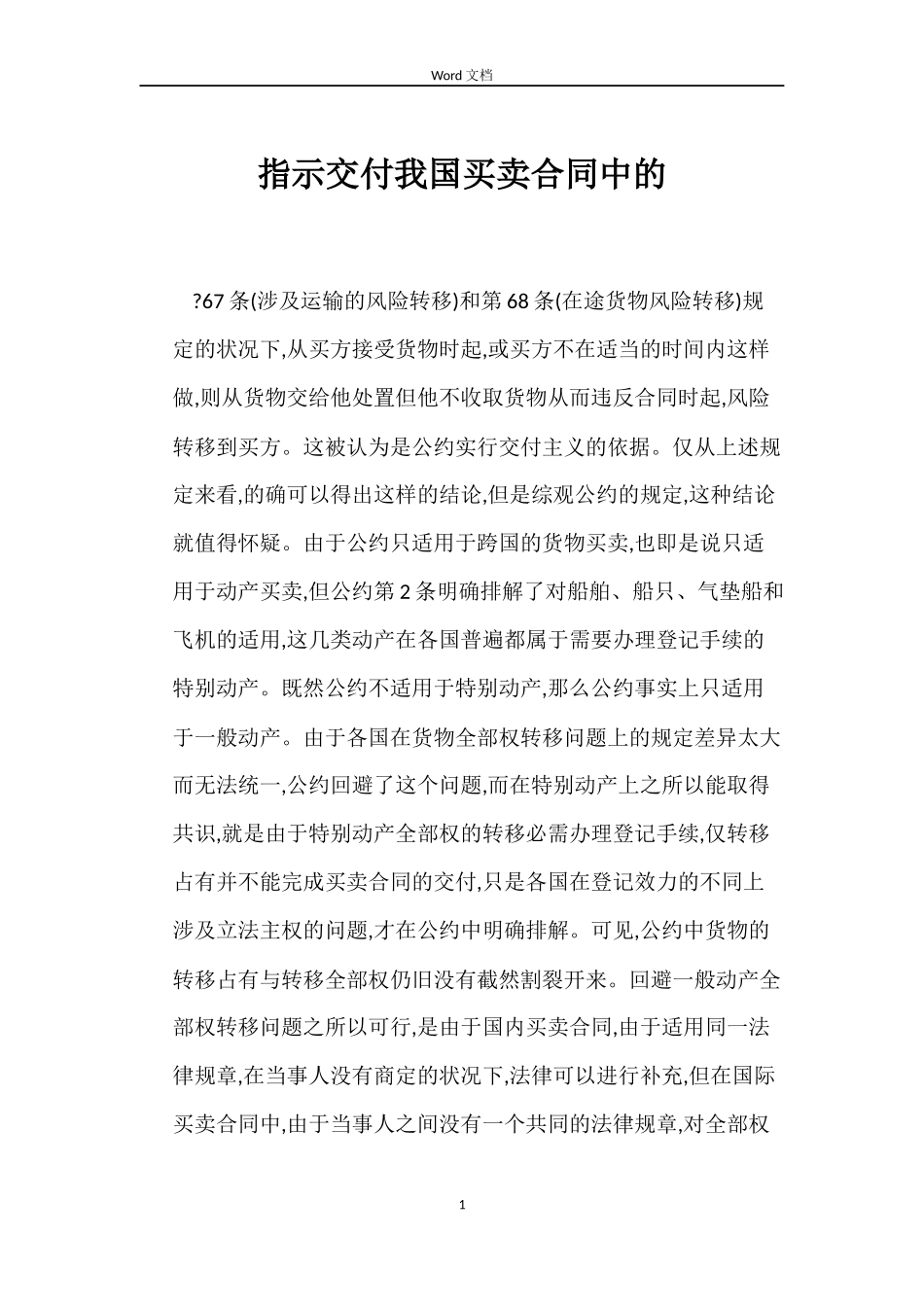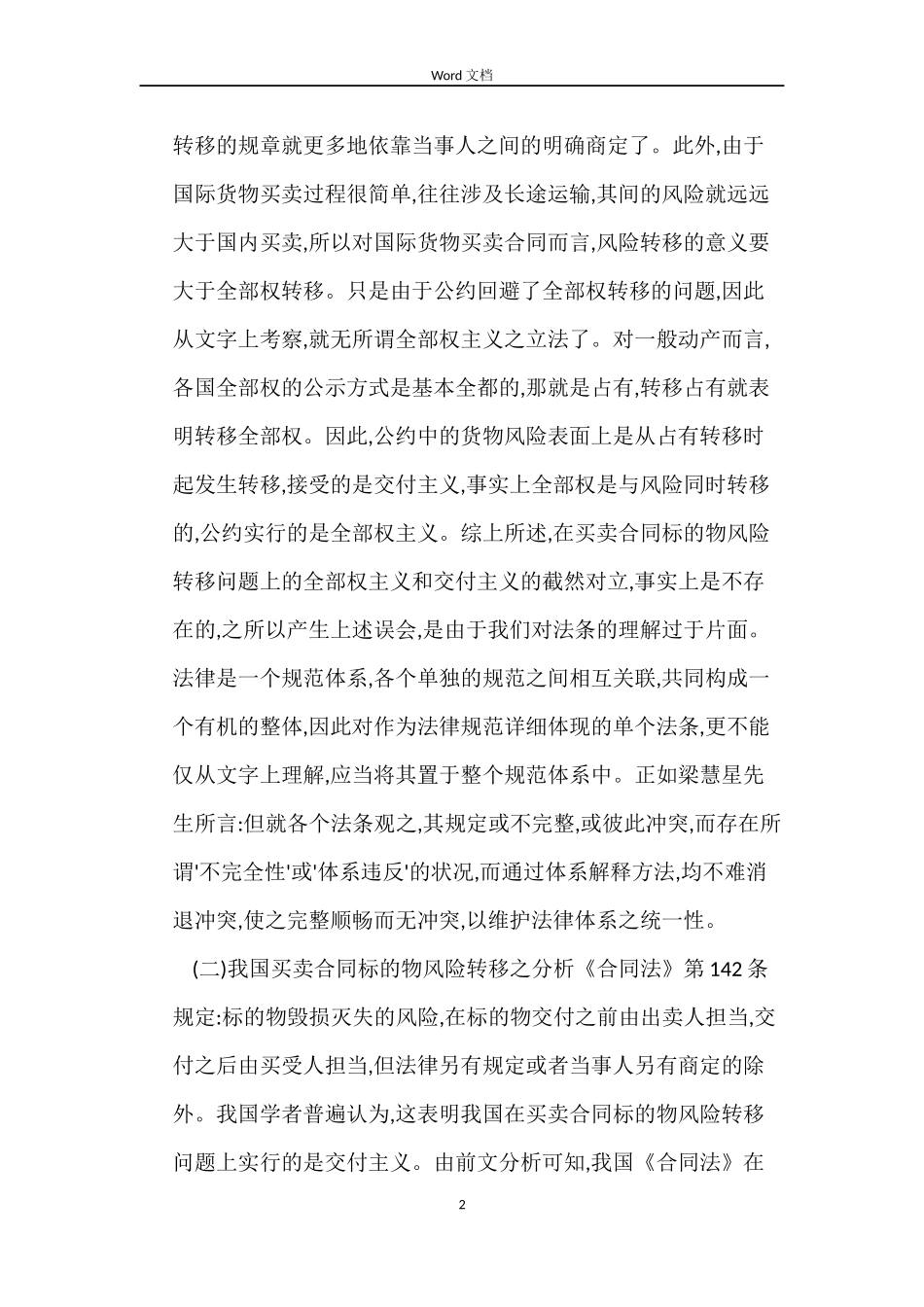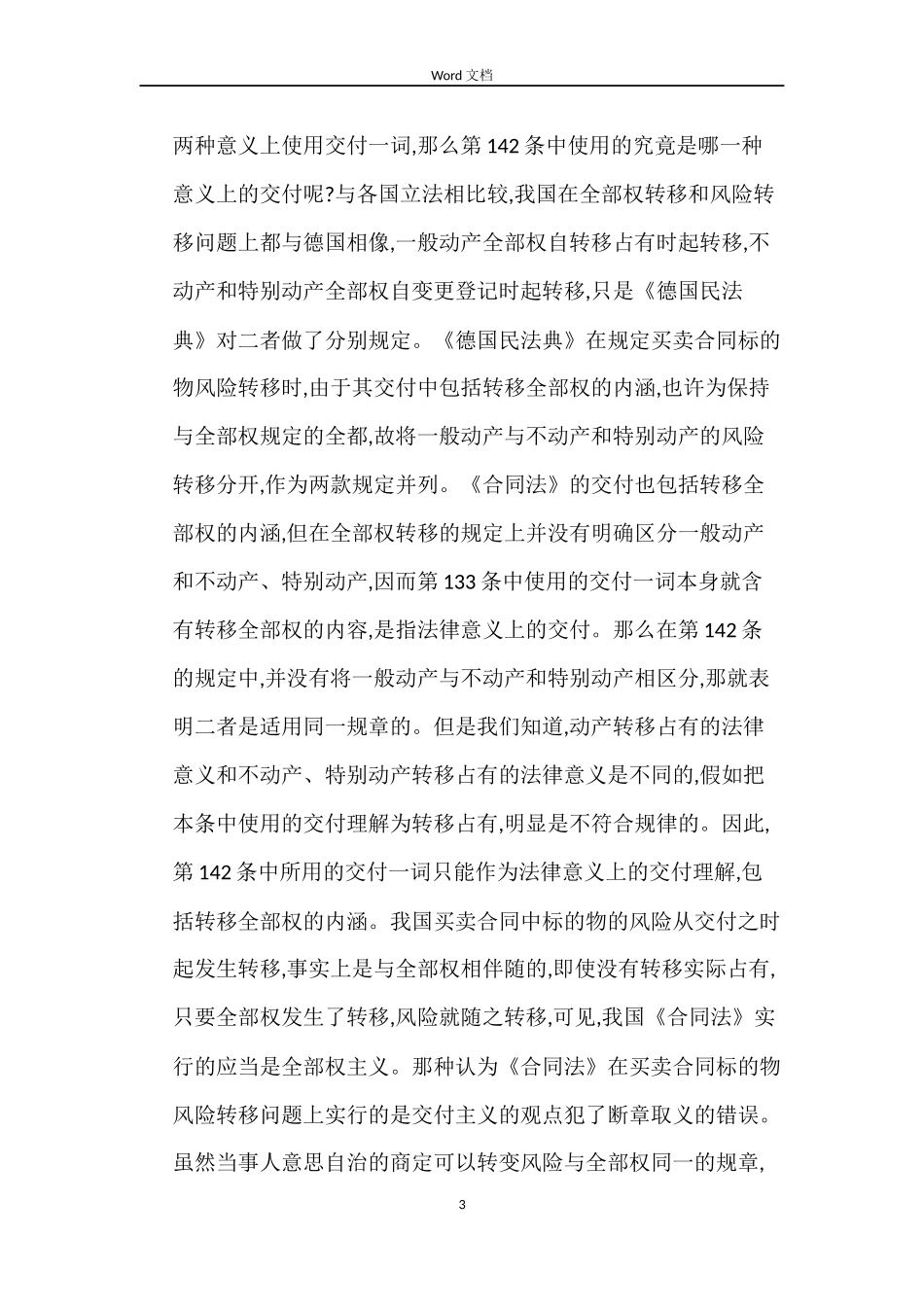Word文档指示交付我国买卖合同中的?67条(涉及运输的风险转移)和第68条(在途货物风险转移)规定的状况下,从买方接受货物时起,或买方不在适当的时间内这样做,则从货物交给他处置但他不收取货物从而违反合同时起,风险转移到买方。这被认为是公约实行交付主义的依据。仅从上述规定来看,的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综观公约的规定,这种结论就值得怀疑。由于公约只适用于跨国的货物买卖,也即是说只适用于动产买卖,但公约第2条明确排解了对船舶、船只、气垫船和飞机的适用,这几类动产在各国普遍都属于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特别动产。既然公约不适用于特别动产,那么公约事实上只适用于一般动产。由于各国在货物全部权转移问题上的规定差异太大而无法统一,公约回避了这个问题,而在特别动产上之所以能取得共识,就是由于特别动产全部权的转移必需办理登记手续,仅转移占有并不能完成买卖合同的交付,只是各国在登记效力的不同上涉及立法主权的问题,才在公约中明确排解。可见,公约中货物的转移占有与转移全部权仍旧没有截然割裂开来。回避一般动产全部权转移问题之所以可行,是由于国内买卖合同,由于适用同一法律规章,在当事人没有商定的状况下,法律可以进行补充,但在国际买卖合同中,由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法律规章,对全部权1Word文档转移的规章就更多地依靠当事人之间的明确商定了。此外,由于国际货物买卖过程很简单,往往涉及长途运输,其间的风险就远远大于国内买卖,所以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而言,风险转移的意义要大于全部权转移。只是由于公约回避了全部权转移的问题,因此从文字上考察,就无所谓全部权主义之立法了。对一般动产而言,各国全部权的公示方式是基本全都的,那就是占有,转移占有就表明转移全部权。因此,公约中的货物风险表面上是从占有转移时起发生转移,接受的是交付主义,事实上全部权是与风险同时转移的,公约实行的是全部权主义。综上所述,在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问题上的全部权主义和交付主义的截然对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之所以产生上述误会,是由于我们对法条的理解过于片面。法律是一个规范体系,各个单独的规范之间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作为法律规范详细体现的单个法条,更不能仅从文字上理解,应当将其置于整个规范体系中。正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但就各个法条观之,其规定或不完整,或彼此冲突,而存在所谓'不完全性'或'体系违反'的状况,而通过体系解释方法,均不难消退冲突,使之完整顺畅而无冲突,以维护法律体系之统一性。(二)我国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之分析《合同法》第142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担当,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担当,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商定的除外。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表明我国在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问题上实行的是交付主义。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合同法》在2Word文档两种意义上使用交付一词,那么第142条中使用的究竟是哪一种意义上的交付呢?与各国立法相比较,我国在全部权转移和风险转移问题上都与德国相像,一般动产全部权自转移占有时起转移,不动产和特别动产全部权自变更登记时起转移,只是《德国民法典》对二者做了分别规定。《德国民法典》在规定买卖合同标的物风险转移时,由于其交付中包括转移全部权的内涵,也许为保持与全部权规定的全都,故将一般动产与不动产和特别动产的风险转移分开,作为两款规定并列。《合同法》的交付也包括转移全部权的内涵,但在全部权转移的规定上并没有明确区分一般动产和不动产、特别动产,因而第133条中使用的交付一词本身就含有转移全部权的内容,是指法律意义上的交付。那么在第142条的规定中,并没有将一般动产与不动产和特别动产相区分,那就表明二者是适用同一规章的。但是我们知道,动产转移占有的法律意义和不动产、特别动产转移占有的法律意义是不同的,假如把本条中使用的交付理解为转移占有,明显是不符合规律的。因此,第142条中所用的交付一词只能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交付理解,包括转移全部权的内涵。我国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从交付之时起发生转移,事实上是与全部权相伴随的,即使没有转移实际占有,只要全部权发生了转移,风险就随之转移,可见,我国《合同法》实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