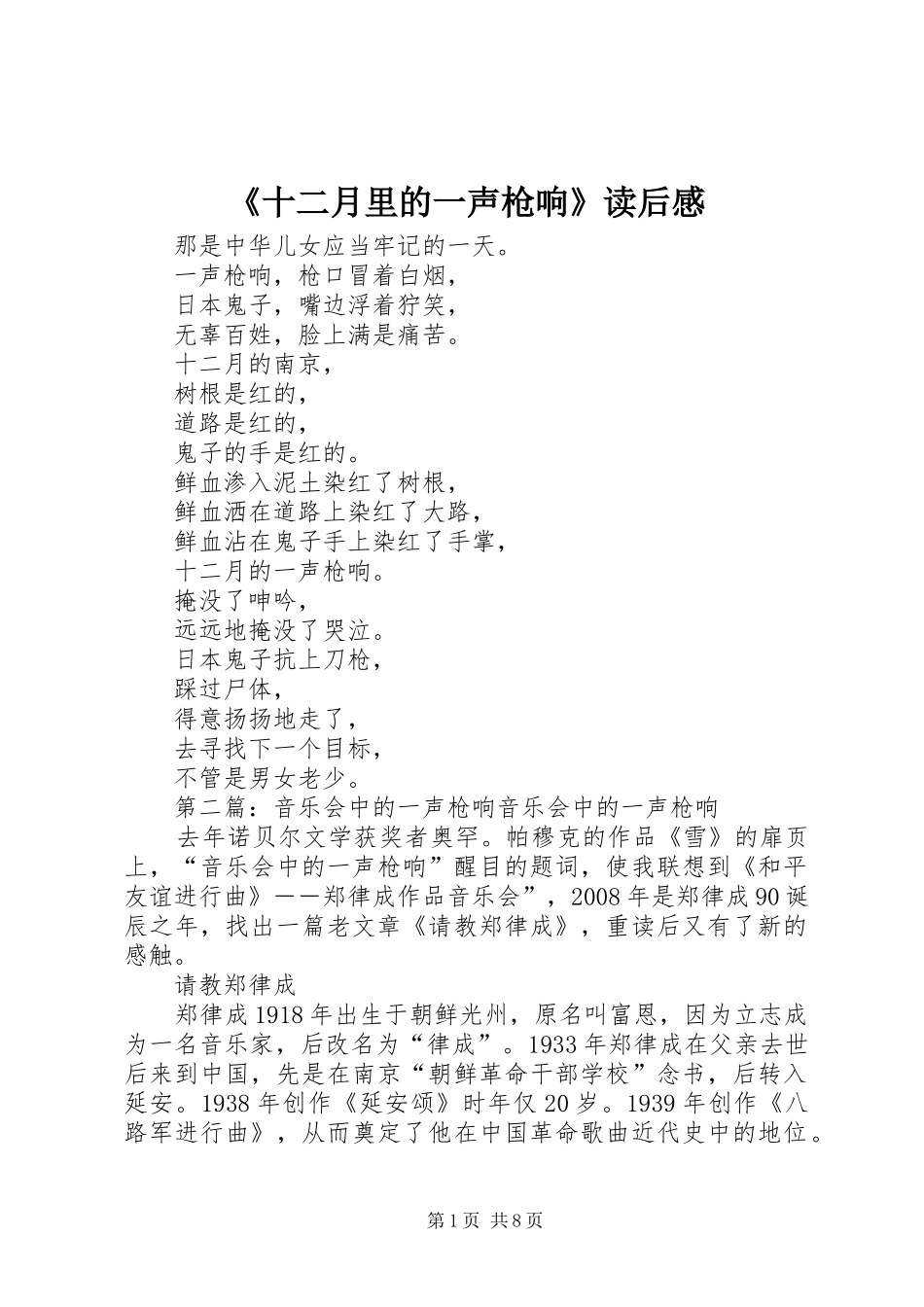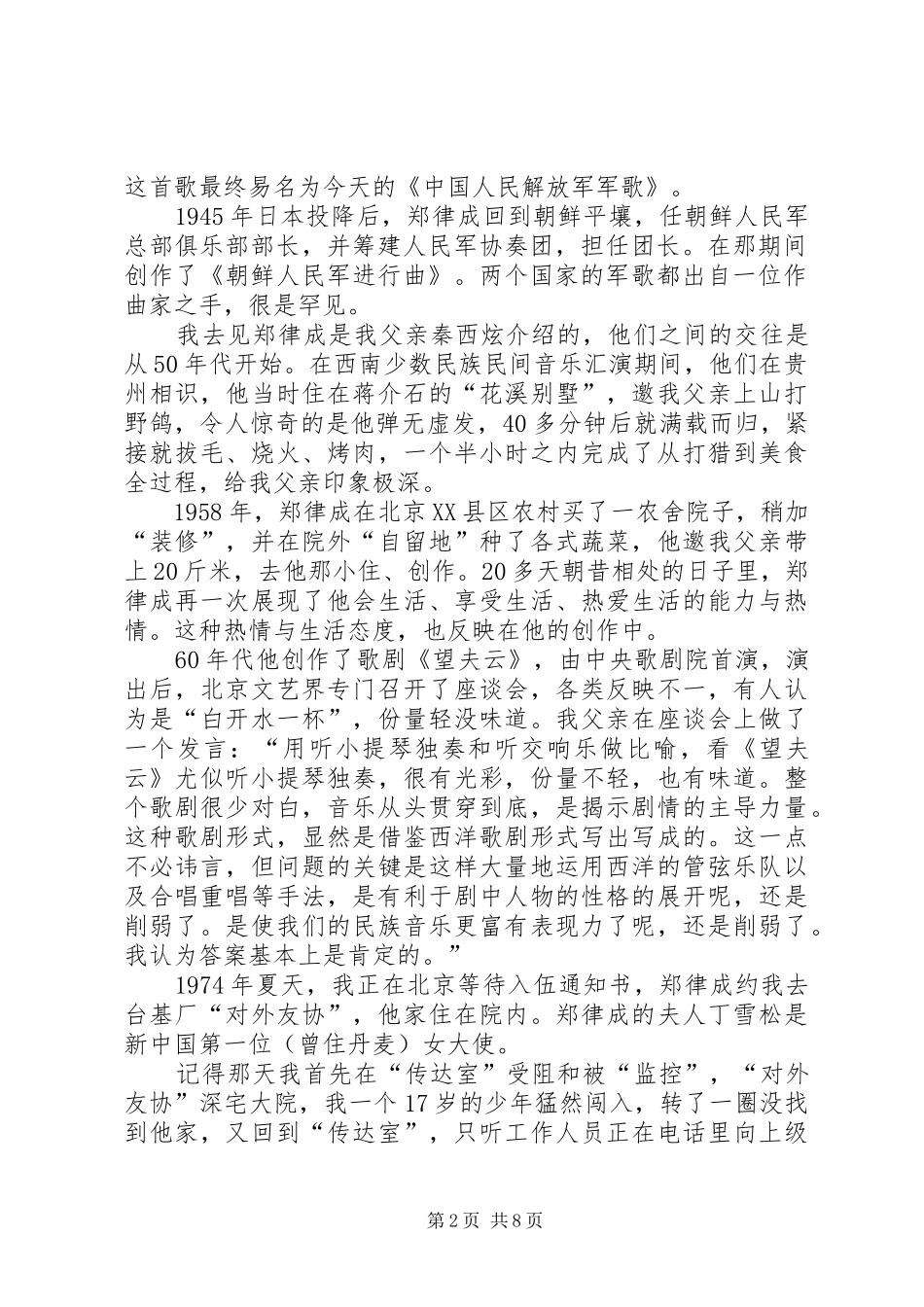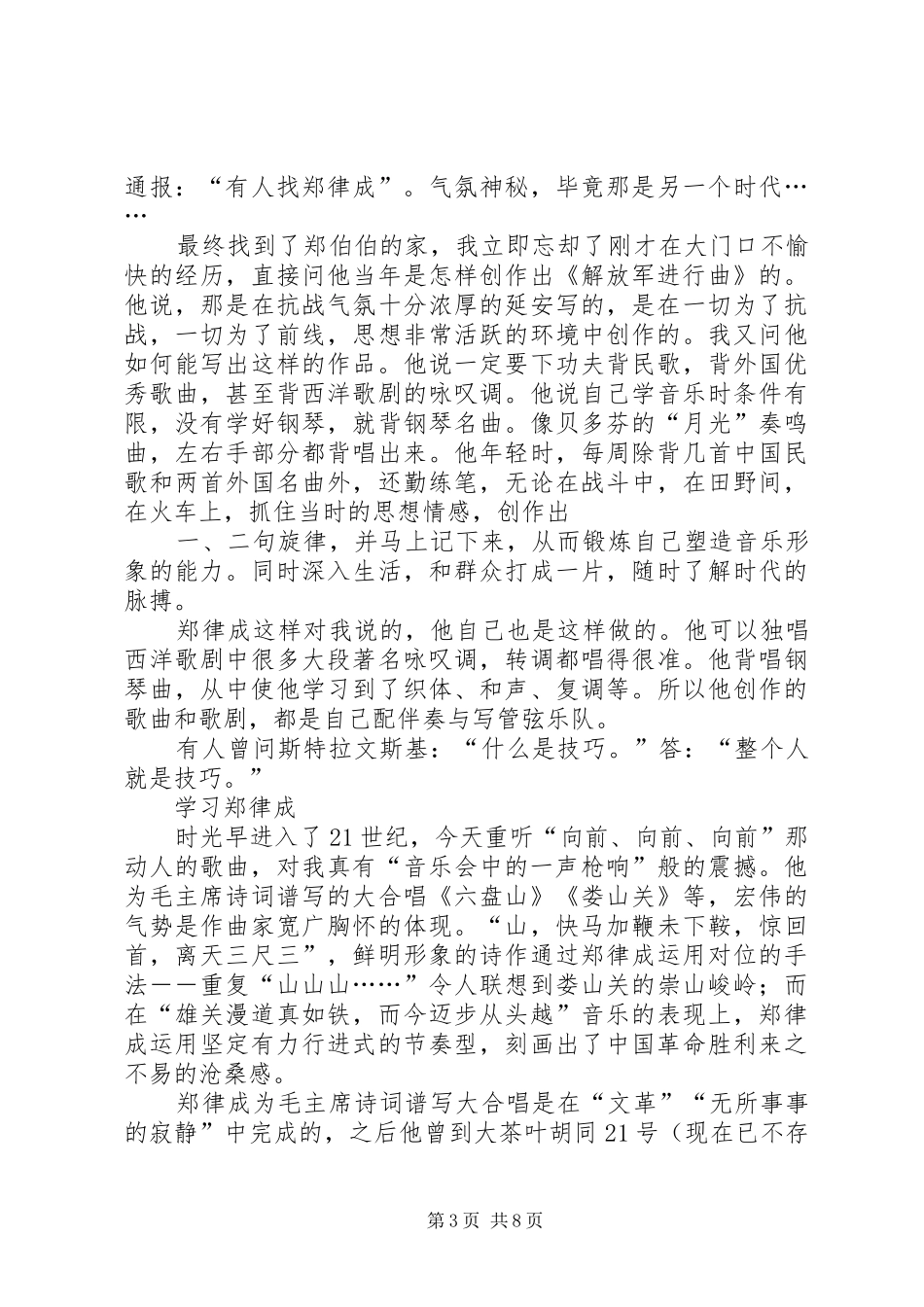《十二月里的一声枪响》读后感那是中华儿女应当牢记的一天。一声枪响,枪口冒着白烟,日本鬼子,嘴边浮着狞笑,无辜百姓,脸上满是痛苦。十二月的南京,树根是红的,道路是红的,鬼子的手是红的。鲜血渗入泥土染红了树根,鲜血洒在道路上染红了大路,鲜血沾在鬼子手上染红了手掌,十二月的一声枪响。掩没了呻吟,远远地掩没了哭泣。日本鬼子抗上刀枪,踩过尸体,得意扬扬地走了,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不管是男女老少。第二篇: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去年诺贝尔文学获奖者奥罕。帕穆克的作品《雪》的扉页上,“音乐会中的一声枪响”醒目的题词,使我联想到《和平友谊进行曲》――郑律成作品音乐会”,2008年是郑律成90诞辰之年,找出一篇老文章《请教郑律成》,重读后又有了新的感触。请教郑律成郑律成1918年出生于朝鲜光州,原名叫富恩,因为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家,后改名为“律成”。1933年郑律成在父亲去世后来到中国,先是在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念书,后转入延安。1938年创作《延安颂》时年仅20岁。1939年创作《八路军进行曲》,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革命歌曲近代史中的地位。第1页共8页这首歌最终易名为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1945年日本投降后,郑律成回到朝鲜平壤,任朝鲜人民军总部俱乐部部长,并筹建人民军协奏团,担任团长。在那期间创作了《朝鲜人民军进行曲》。两个国家的军歌都出自一位作曲家之手,很是罕见。我去见郑律成是我父亲秦西炫介绍的,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从50年代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汇演期间,他们在贵州相识,他当时住在蒋介石的“花溪别墅”,邀我父亲上山打野鸽,令人惊奇的是他弹无虚发,40多分钟后就满载而归,紧接就拔毛、烧火、烤肉,一个半小时之内完成了从打猎到美食全过程,给我父亲印象极深。1958年,郑律成在北京XX县区农村买了一农舍院子,稍加“装修”,并在院外“自留地”种了各式蔬菜,他邀我父亲带上20斤米,去他那小住、创作。20多天朝昔相处的日子里,郑律成再一次展现了他会生活、享受生活、热爱生活的能力与热情。这种热情与生活态度,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60年代他创作了歌剧《望夫云》,由中央歌剧院首演,演出后,北京文艺界专门召开了座谈会,各类反映不一,有人认为是“白开水一杯”,份量轻没味道。我父亲在座谈会上做了一个发言:“用听小提琴独奏和听交响乐做比喻,看《望夫云》尤似听小提琴独奏,很有光彩,份量不轻,也有味道。整个歌剧很少对白,音乐从头贯穿到底,是揭示剧情的主导力量。这种歌剧形式,显然是借鉴西洋歌剧形式写出写成的。这一点不必讳言,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大量地运用西洋的管弦乐队以及合唱重唱等手法,是有利于剧中人物的性格的展开呢,还是削弱了。是使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富有表现力了呢,还是削弱了。我认为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1974年夏天,我正在北京等待入伍通知书,郑律成约我去台基厂“对外友协”,他家住在院内。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曾住丹麦)女大使。记得那天我首先在“传达室”受阻和被“监控”,“对外友协”深宅大院,我一个17岁的少年猛然闯入,转了一圈没找到他家,又回到“传达室”,只听工作人员正在电话里向上级第2页共8页通报:“有人找郑律成”。气氛神秘,毕竟那是另一个时代……最终找到了郑伯伯的家,我立即忘却了刚才在大门口不愉快的经历,直接问他当年是怎样创作出《解放军进行曲》的。他说,那是在抗战气氛十分浓厚的延安写的,是在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前线,思想非常活跃的环境中创作的。我又问他如何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说一定要下功夫背民歌,背外国优秀歌曲,甚至背西洋歌剧的咏叹调。他说自己学音乐时条件有限,没有学好钢琴,就背钢琴名曲。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左右手部分都背唱出来。他年轻时,每周除背几首中国民歌和两首外国名曲外,还勤练笔,无论在战斗中,在田野间,在火车上,抓住当时的思想情感,创作出一、二句旋律,并马上记下来,从而锻炼自己塑造音乐形象的能力。同时深入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随时了解时代的脉搏。郑律成这样对我说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可以独唱西洋歌剧中很多大段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