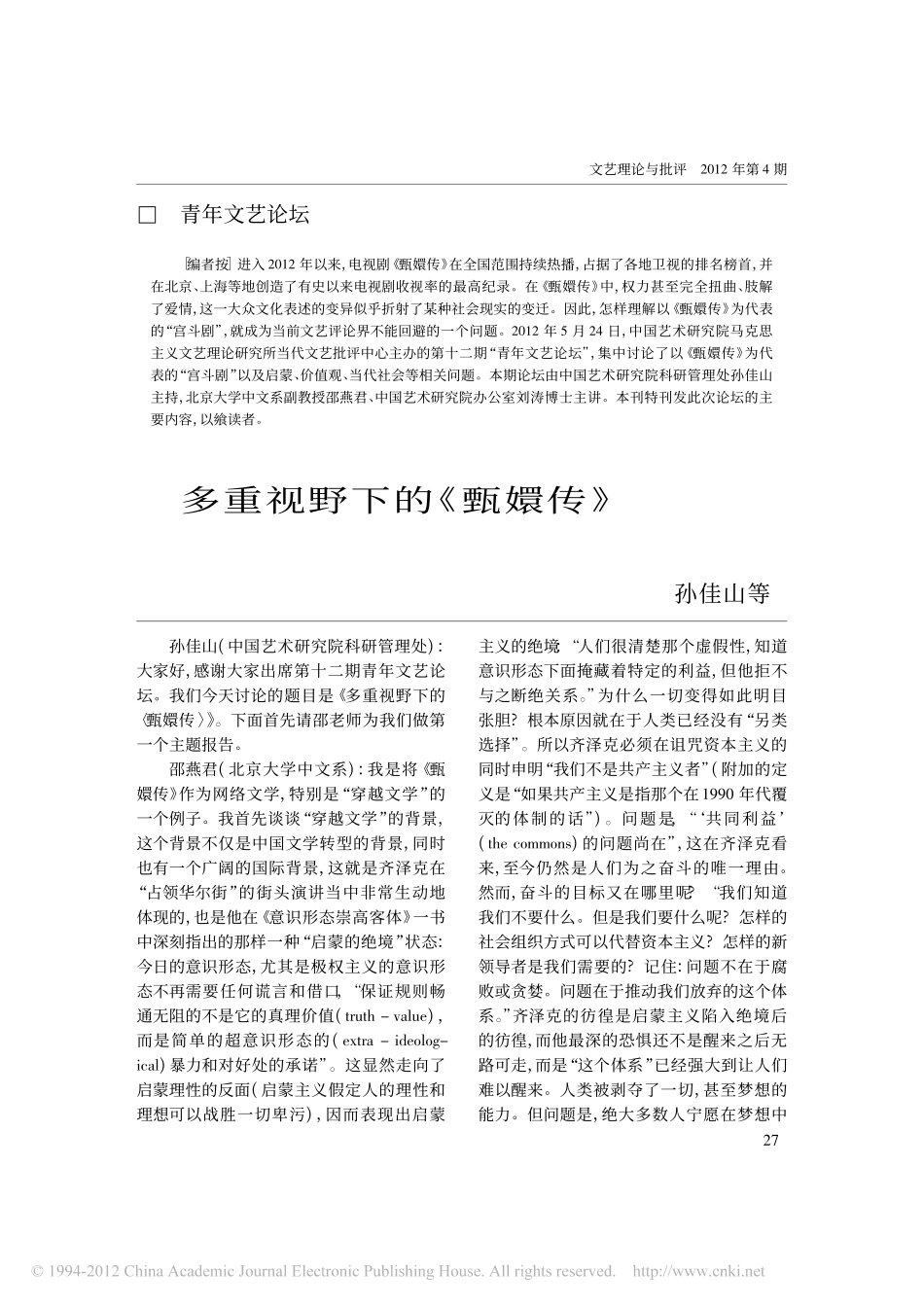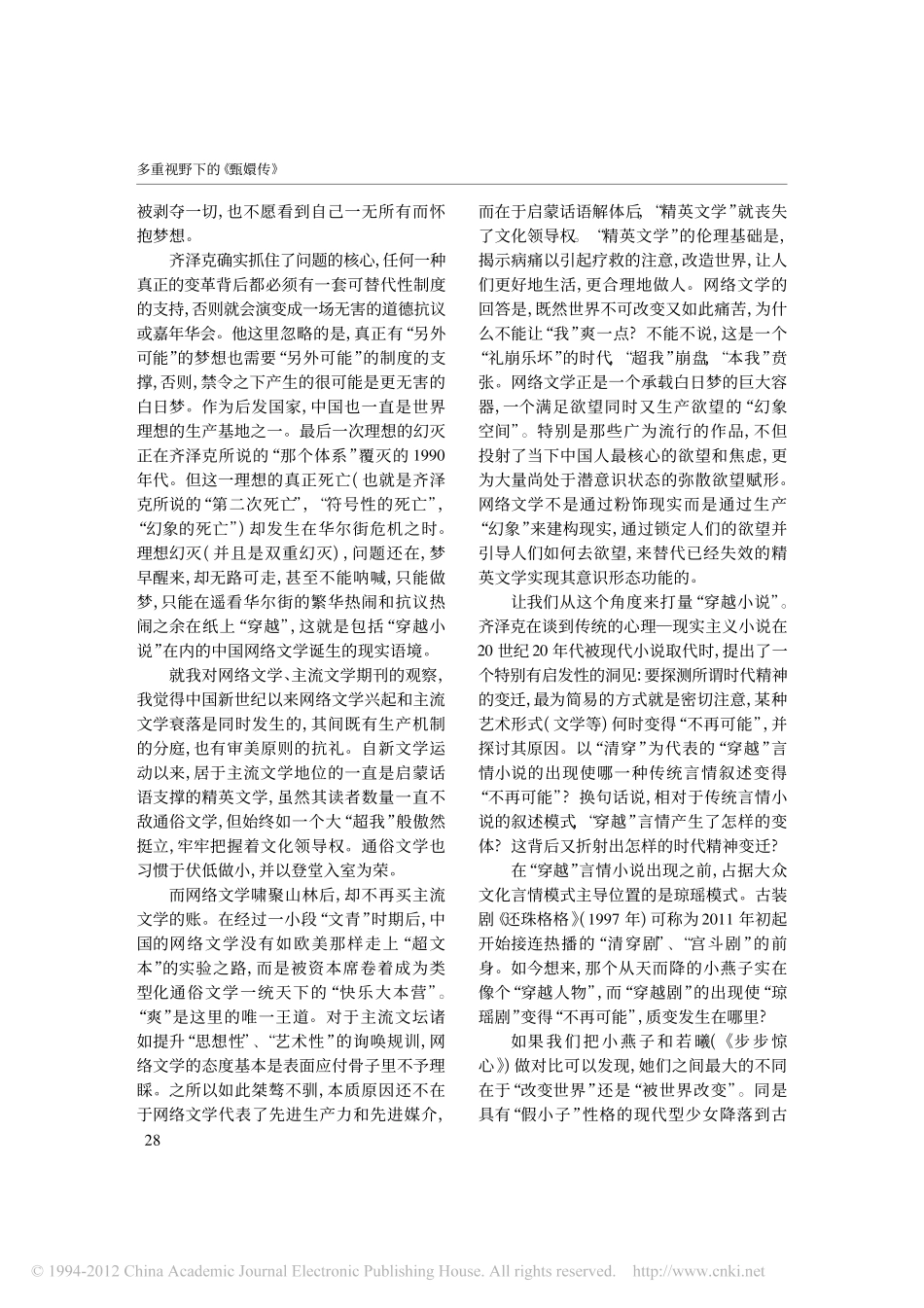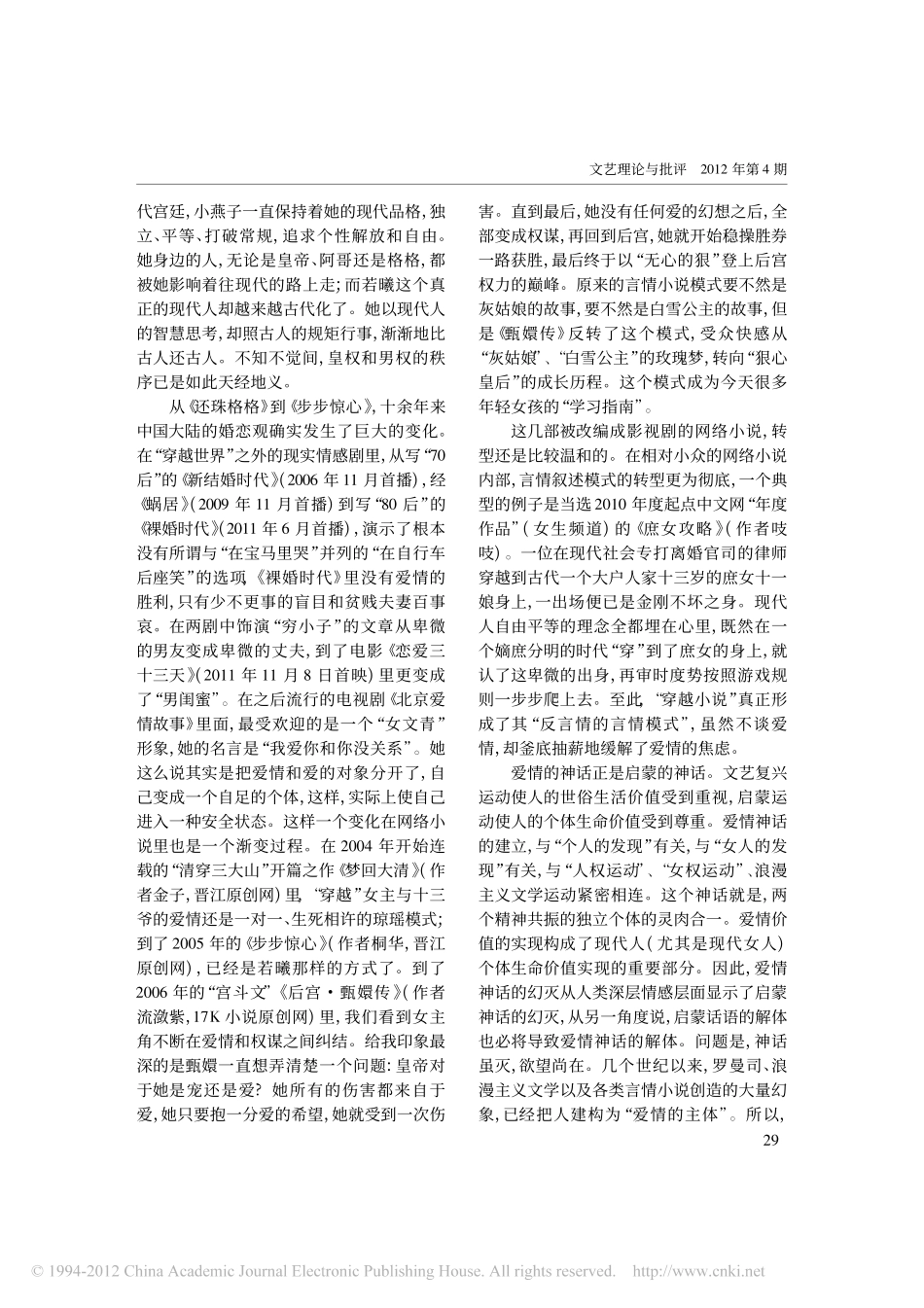□青年文艺论坛[编者按]进入2012年以来,电视剧《甄嬛传》在全国范围持续热播,占据了各地卫视的排名榜首,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创造了有史以来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纪录。在《甄嬛传》中,权力甚至完全扭曲、肢解了爱情,这一大众文化表述的变异似乎折射了某种社会现实的变迁。因此,怎样理解以《甄嬛传》为代表的“宫斗剧”,就成为当前文艺评论界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2012年5月24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主办的第十二期“青年文艺论坛”,集中讨论了以《甄嬛传》为代表的“宫斗剧”以及启蒙、价值观、当代社会等相关问题。本期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孙佳山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刘涛博士主讲。本刊特刊发此次论坛的主要内容,以飨读者。多重视野下的《甄嬛传》孙佳山等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科研管理处):大家好,感谢大家出席第十二期青年文艺论坛。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多重视野下的〈甄嬛传〉》。下面首先请邵老师为我们做第一个主题报告。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我是将《甄嬛传》作为网络文学,特别是“穿越文学”的一个例子。我首先谈谈“穿越文学”的背景,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文学转型的背景,同时也有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这就是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的街头演讲当中非常生动地体现的,也是他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一书中深刻指出的那样一种“启蒙的绝境”状态:今日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需要任何谎言和借口,“保证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这显然走向了启蒙理性的反面(启蒙主义假定人的理性和理想可以战胜一切卑污),因而表现出启蒙主义的绝境:“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为什么一切变得如此明目张胆?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已经没有“另类选择”。所以齐泽克必须在诅咒资本主义的同时申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附加的定义是“如果共产主义是指那个在1990年代覆灭的体制的话”)。问题是,“‘共同利益’(thecommons)的问题尚在”,这在齐泽克看来,至今仍然是人们为之奋斗的唯一理由。然而,奋斗的目标又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但是我们要什么呢?怎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可以代替资本主义?怎样的新领导者是我们需要的?记住:问题不在于腐败或贪婪。问题在于推动我们放弃的这个体系。”齐泽克的彷徨是启蒙主义陷入绝境后的彷徨,而他最深的恐惧还不是醒来之后无路可走,而是“这个体系”已经强大到让人们难以醒来。人类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梦想的能力。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宁愿在梦想中72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4期被剥夺一切,也不愿看到自己一无所有而怀抱梦想。齐泽克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任何一种真正的变革背后都必须有一套可替代性制度的支持,否则就会演变成一场无害的道德抗议或嘉年华会。他这里忽略的是,真正有“另外可能”的梦想也需要“另外可能”的制度的支撑,否则,禁令之下产生的很可能是更无害的白日梦。作为后发国家,中国也一直是世界理想的生产基地之一。最后一次理想的幻灭正在齐泽克所说的“那个体系”覆灭的1990年代。但这一理想的真正死亡(也就是齐泽克所说的“第二次死亡”,“符号性的死亡”,“幻象的死亡”)却发生在华尔街危机之时。理想幻灭(并且是双重幻灭),问题还在,梦早醒来,却无路可走,甚至不能呐喊,只能做梦,只能在遥看华尔街的繁华热闹和抗议热闹之余在纸上“穿越”,这就是包括“穿越小说”在内的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现实语境。就我对网络文学、主流文学期刊的观察,我觉得中国新世纪以来网络文学兴起和主流文学衰落是同时发生的,其间既有生产机制的分庭,也有审美原则的抗礼。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居于主流文学地位的一直是启蒙话语支撑的精英文学,虽然其读者数量一直不敌通俗文学,但始终如一个大“超我”般傲然挺立,牢牢把握着文化领导权。通俗文学也习惯于伏低做小,并以登堂入室为荣。而网络文学啸聚山林后,却不再买主流文学的账。在经过一小段“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