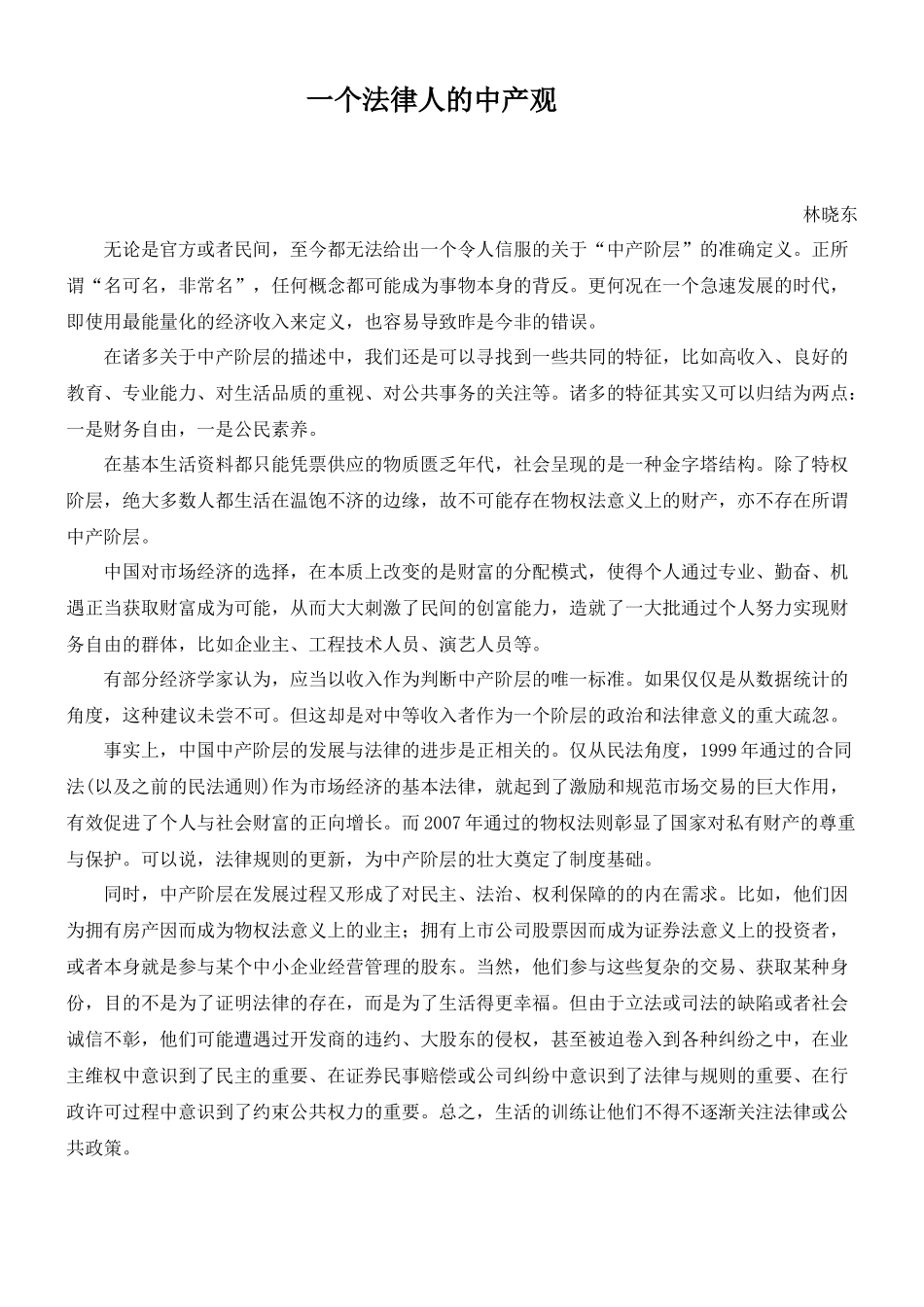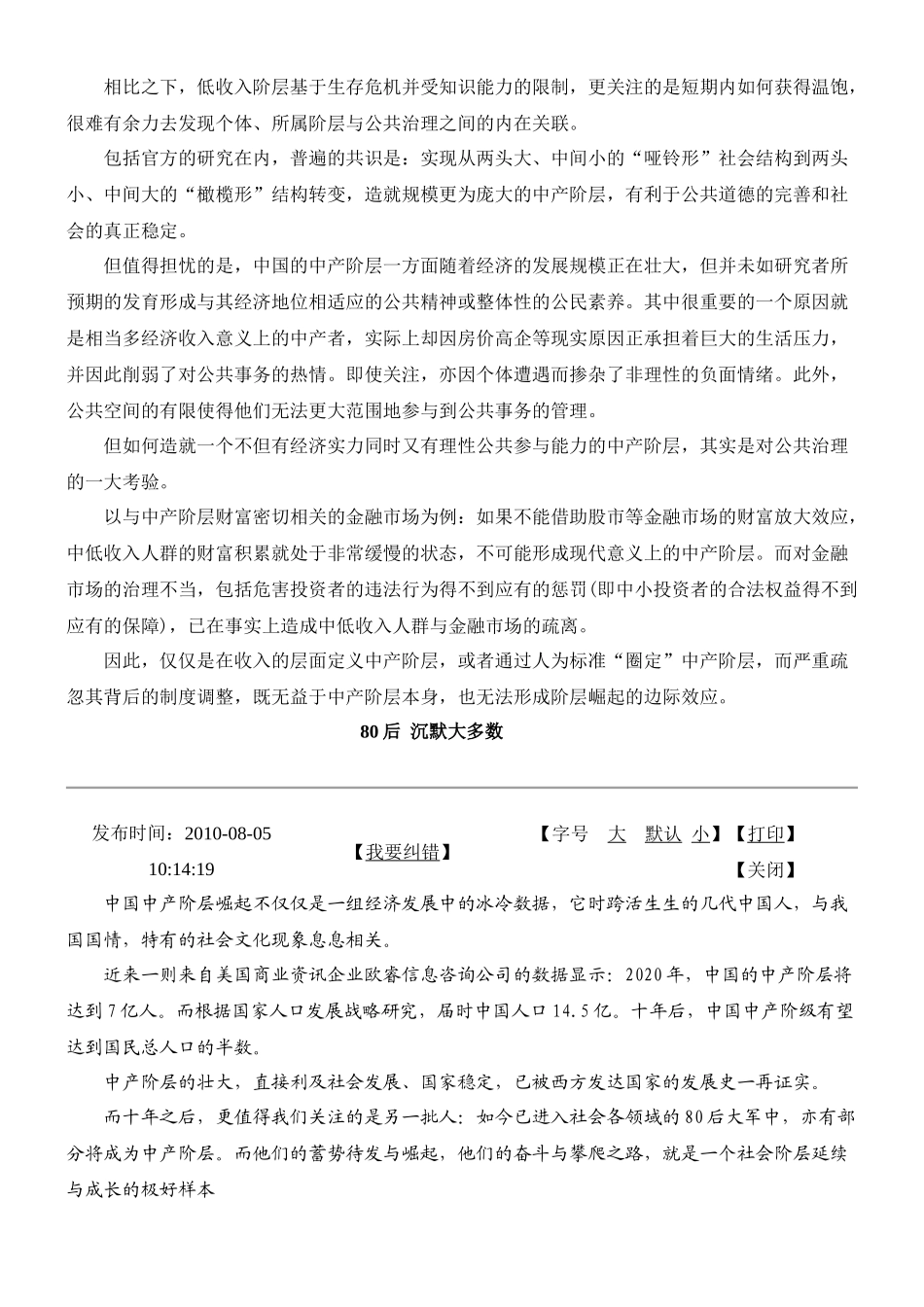一个法律人的中产观 林晓东 无论是官方或者民间,至今都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关于“中产阶层”的准确定义。正所谓“名可名,非常名”,任何概念都可能成为事物本身的背反。更何况在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即使用最能量化的经济收入来定义,也容易导致昨是今非的错误。 在诸多关于中产阶层的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寻找到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高收入、良好的教育、专业能力、对生活品质的重视、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等。诸多的特征其实又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财务自由,一是公民素养。 在基本生活资料都只能凭票供应的物质匮乏年代,社会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结构。除了特权阶层,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温饱不济的边缘,故不可能存在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亦不存在所谓中产阶层。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选择,在本质上改变的是财富的分配模式,使得个人通过专业、勤奋、机遇正当获取财富成为可能,从而大大刺激了民间的创富能力,造就了一大批通过个人努力实现财务自由的群体,比如企业主、工程技术人员、演艺人员等。 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以收入作为判断中产阶层的唯一标准。如果仅仅是从数据统计的角度,这种建议未尝不可。但这却是对中等收入者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和法律意义的重大疏忽。 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与法律的进步是正相关的。仅从民法角度,1999 年通过的合同法(以及之前的民法通则)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就起到了激励和规范市场交易的巨大作用,有效促进了个人与社会财富的正向增长。而 2007 年通过的物权法则彰显了国家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与保护。可以说,法律规则的更新,为中产阶层的壮大奠定了制度基础。 同时,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又形成了对民主、法治、权利保障的的内在需求。比如,他们因为拥有房产因而成为物权法意义上的业主;拥有上市公司股票因而成为证券法意义上的投资者,或者本身就是参与某个中小企业经营管理的股东。当然,他们参与这些复杂的交易、获取某种身份,目的不是为了证明法律的存在,而是为了生活得更幸福。但由于立法或司法的缺陷或者社会诚信不彰,他们可能遭遇过开发商的违约、大股东的侵权,甚至被迫卷入到各种纠纷之中,在业主维权中意识到了民主的重要、在证券民事赔偿或公司纠纷中意识到了法律与规则的重要、在行政许可过程中意识到了约束公共权力的重要。总之,生活的训练让他们不得不逐渐关注法律或公共政策。 相比之下,低收入阶层基于生存危机并受知识能力的限制,更关注的是短期内如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