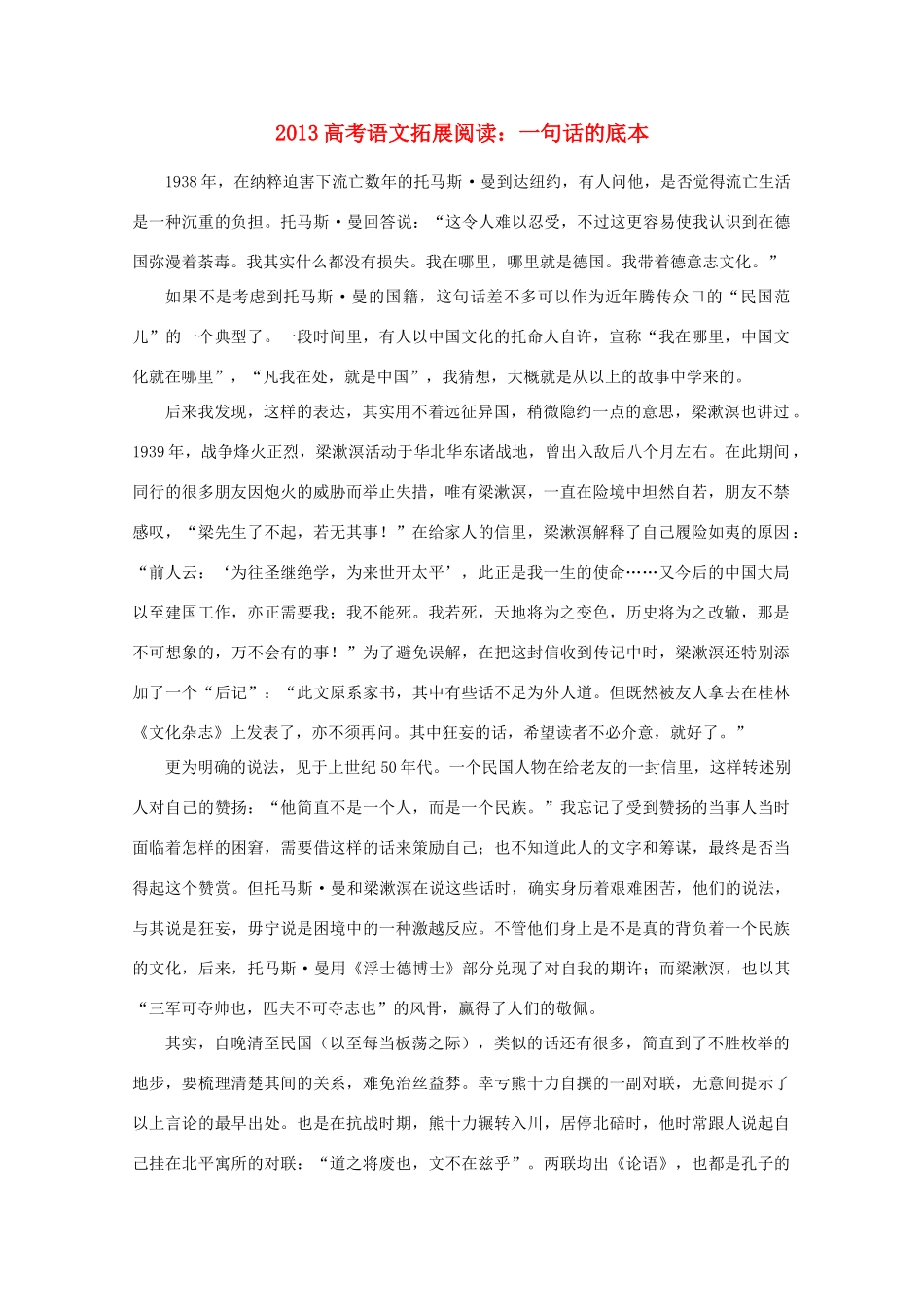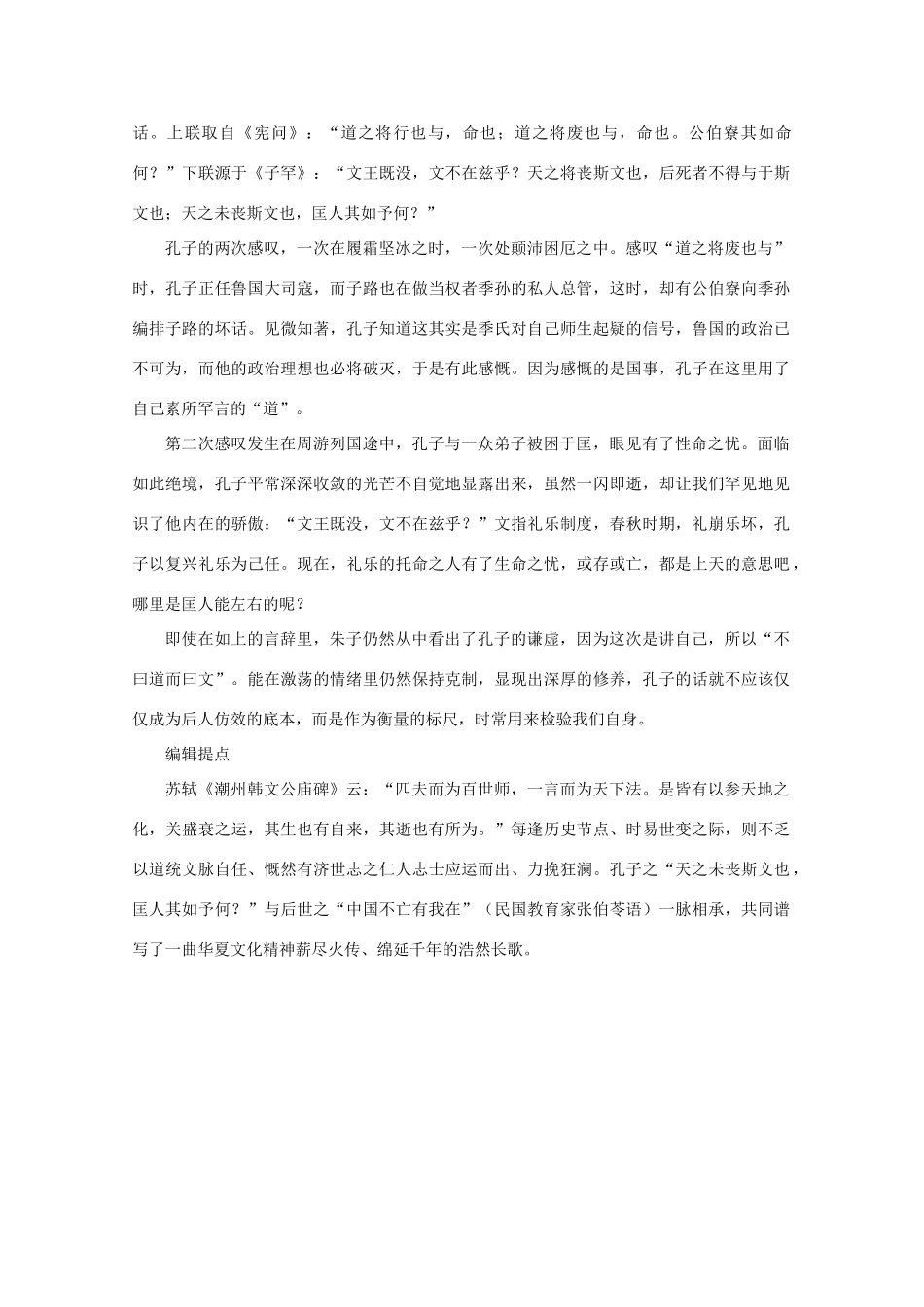2013 高考语文拓展阅读:一句话的底本1938 年,在纳粹迫害下流亡数年的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有人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托马斯·曼回答说:“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如果不是考虑到托马斯·曼的国籍,这句话差不多可以作为近年腾传众口的“民国范儿”的一个典型了。一段时间里,有人以中国文化的托命人自许,宣称“我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凡我在处,就是中国”,我猜想,大概就是从以上的故事中学来的。后来我发现,这样的表达,其实用不着远征异国,稍微隐约一点的意思,梁漱溟也讲过 。1939 年,战争烽火正烈,梁漱溟活动于华北华东诸战地,曾出入敌后八个月左右。在此期间,同行的很多朋友因炮火的威胁而举止失措,唯有梁漱溟,一直在险境中坦然自若,朋友不禁感叹,“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在给家人的信里,梁漱溟解释了自己履险如夷的原因:“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为了避免误解,在把这封信收到传记中时,梁漱溟还特别添加了一个“后记”:“此文原系家书,其中有些话不足为外人道。但既然被友人拿去在桂林《文化杂志》上发表了,亦不须再问。其中狂妄的话,希望读者不必介意,就好了。”更为明确的说法,见于上世纪 50 年代。一个民国人物在给老友的一封信里,这样转述别人对自己的赞扬:“他简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我忘记了受到赞扬的当事人当时面临着怎样的困窘,需要借这样的话来策励自己;也不知道此人的文字和筹谋,最终是否当得起这个赞赏。但托马斯·曼和梁漱溟在说这些话时,确实身历着艰难困苦,他们的说法,与其说是狂妄,毋宁说是困境中的一种激越反应。不管他们身上是不是真的背负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后来,托马斯·曼用《浮士德博士》部分兑现了对自我的期许;而梁漱溟,也以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风骨,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其实,自晚清至民国(以至每当板荡之际),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简直到了不胜枚举的地步,要梳理清楚其间的关系,难免治丝益棼。幸亏熊十力自撰的一副对联,无意间提示了以上言论的最早出处。也是在抗战时期,熊十力辗转入川,居停北碚时,他时常跟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