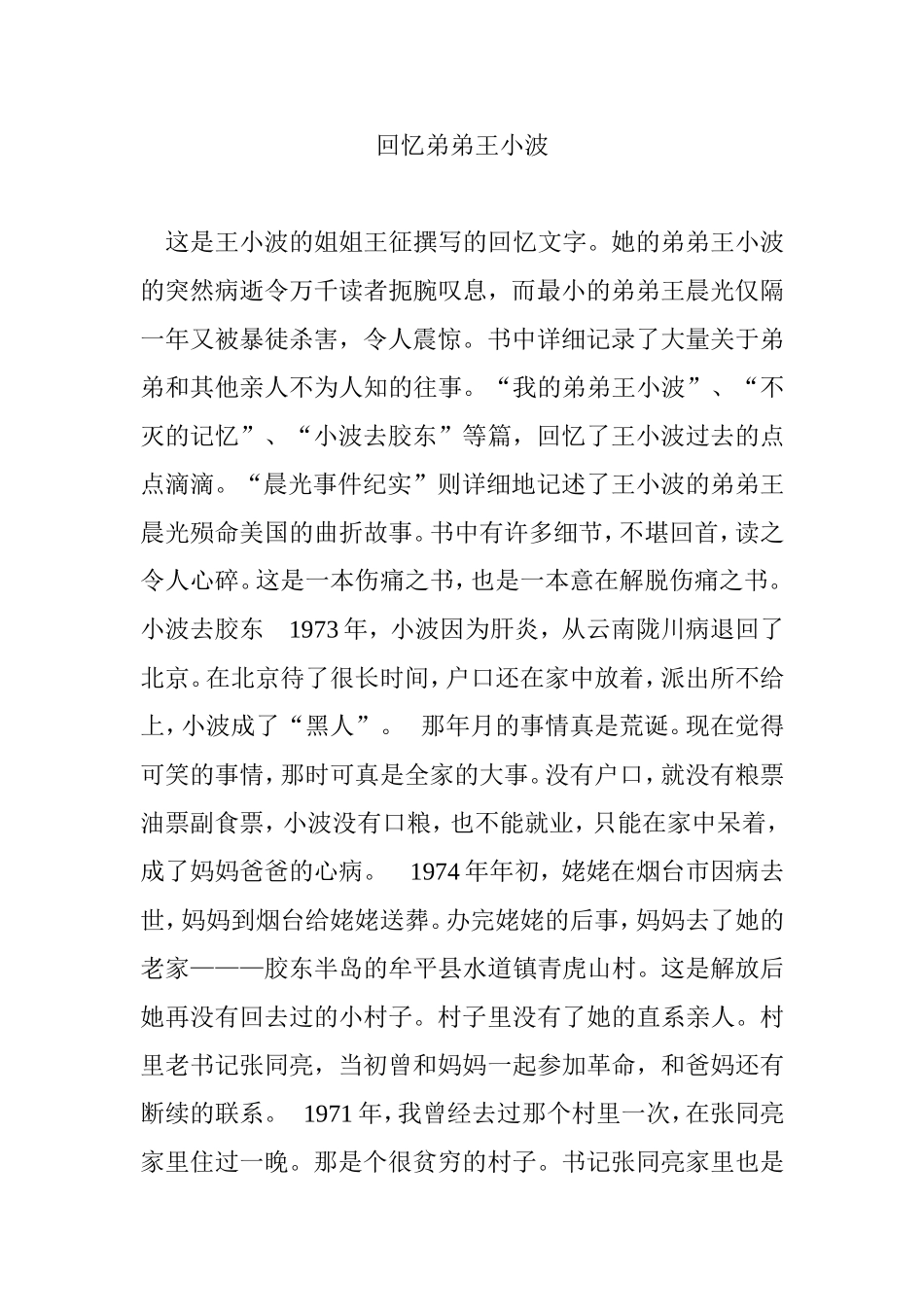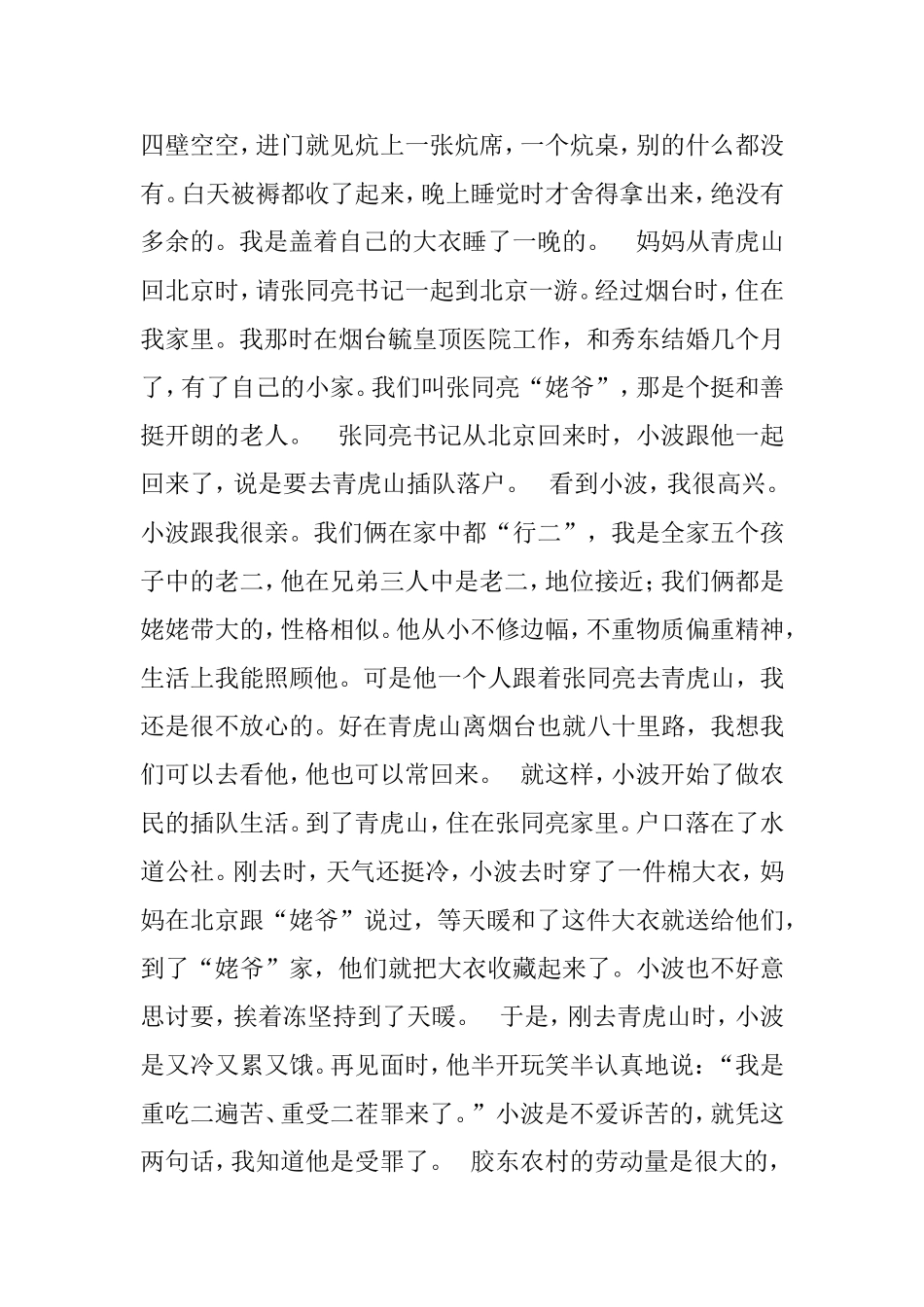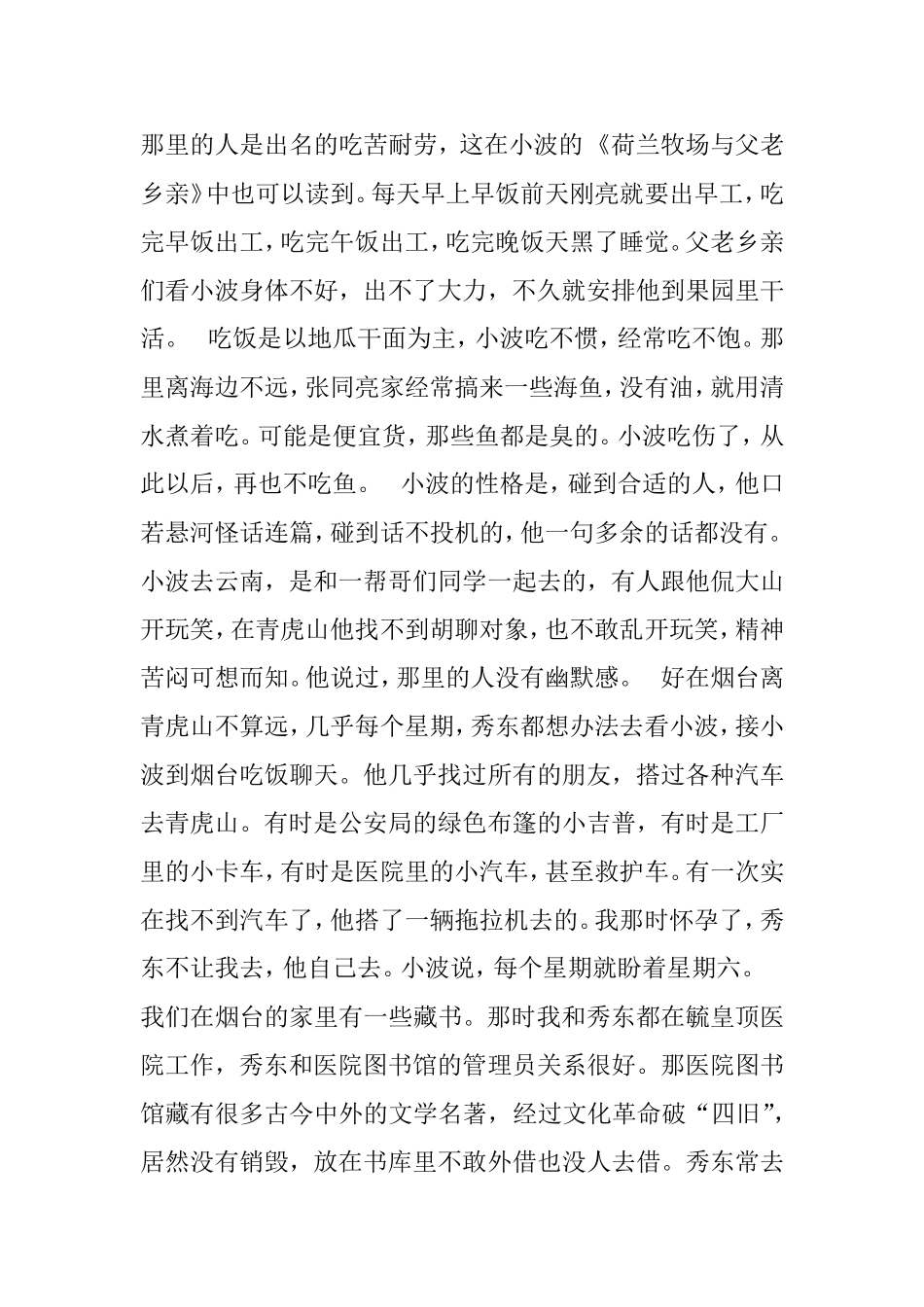回忆弟弟王小波这是王小波的姐姐王征撰写的回忆文字。她的弟弟王小波的突然病逝令万千读者扼腕叹息,而最小的弟弟王晨光仅隔一年又被暴徒杀害,令人震惊。书中详细记录了大量关于弟弟和其他亲人不为人知的往事。“我的弟弟王小波”、“不灭的记忆”、“小波去胶东”等篇,回忆了王小波过去的点点滴滴。“晨光事件纪实”则详细地记述了王小波的弟弟王晨光殒命美国的曲折故事。书中有许多细节,不堪回首,读之令人心碎。这是一本伤痛之书,也是一本意在解脱伤痛之书。小波去胶东1973年,小波因为肝炎,从云南陇川病退回了北京。在北京待了很长时间,户口还在家中放着,派出所不给上,小波成了“黑人”。那年月的事情真是荒诞。现在觉得可笑的事情,那时可真是全家的大事。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油票副食票,小波没有口粮,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中呆着,成了妈妈爸爸的心病。1974年年初,姥姥在烟台市因病去世,妈妈到烟台给姥姥送葬。办完姥姥的后事,妈妈去了她的老家———胶东半岛的牟平县水道镇青虎山村。这是解放后她再没有回去过的小村子。村子里没有了她的直系亲人。村里老书记张同亮,当初曾和妈妈一起参加革命,和爸妈还有断续的联系。1971年,我曾经去过那个村里一次,在张同亮家里住过一晚。那是个很贫穷的村子。书记张同亮家里也是四壁空空,进门就见炕上一张炕席,一个炕桌,别的什么都没有。白天被褥都收了起来,晚上睡觉时才舍得拿出来,绝没有多余的。我是盖着自己的大衣睡了一晚的。妈妈从青虎山回北京时,请张同亮书记一起到北京一游。经过烟台时,住在我家里。我那时在烟台毓皇顶医院工作,和秀东结婚几个月了,有了自己的小家。我们叫张同亮“姥爷”,那是个挺和善挺开朗的老人。张同亮书记从北京回来时,小波跟他一起回来了,说是要去青虎山插队落户。看到小波,我很高兴。小波跟我很亲。我们俩在家中都“行二”,我是全家五个孩子中的老二,他在兄弟三人中是老二,地位接近;我们俩都是姥姥带大的,性格相似。他从小不修边幅,不重物质偏重精神,生活上我能照顾他。可是他一个人跟着张同亮去青虎山,我还是很不放心的。好在青虎山离烟台也就八十里路,我想我们可以去看他,他也可以常回来。就这样,小波开始了做农民的插队生活。到了青虎山,住在张同亮家里。户口落在了水道公社。刚去时,天气还挺冷,小波去时穿了一件棉大衣,妈妈在北京跟“姥爷”说过,等天暖和了这件大衣就送给他们,到了“姥爷”家,他们就把大衣收藏起来了。小波也不好意思讨要,挨着冻坚持到了天暖。于是,刚去青虎山时,小波是又冷又累又饿。再见面时,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我是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来了。”小波是不爱诉苦的,就凭这两句话,我知道他是受罪了。胶东农村的劳动量是很大的,那里的人是出名的吃苦耐劳,这在小波的《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也可以读到。每天早上早饭前天刚亮就要出早工,吃完早饭出工,吃完午饭出工,吃完晚饭天黑了睡觉。父老乡亲们看小波身体不好,出不了大力,不久就安排他到果园里干活。吃饭是以地瓜干面为主,小波吃不惯,经常吃不饱。那里离海边不远,张同亮家经常搞来一些海鱼,没有油,就用清水煮着吃。可能是便宜货,那些鱼都是臭的。小波吃伤了,从此以后,再也不吃鱼。小波的性格是,碰到合适的人,他口若悬河怪话连篇,碰到话不投机的,他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小波去云南,是和一帮哥们同学一起去的,有人跟他侃大山开玩笑,在青虎山他找不到胡聊对象,也不敢乱开玩笑,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他说过,那里的人没有幽默感。好在烟台离青虎山不算远,几乎每个星期,秀东都想办法去看小波,接小波到烟台吃饭聊天。他几乎找过所有的朋友,搭过各种汽车去青虎山。有时是公安局的绿色布篷的小吉普,有时是工厂里的小卡车,有时是医院里的小汽车,甚至救护车。有一次实在找不到汽车了,他搭了一辆拖拉机去的。我那时怀孕了,秀东不让我去,他自己去。小波说,每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六。我们在烟台的家里有一些藏书。那时我和秀东都在毓皇顶医院工作,秀东和医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关系很好。那医院图书馆藏有很多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经过文化革命破“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