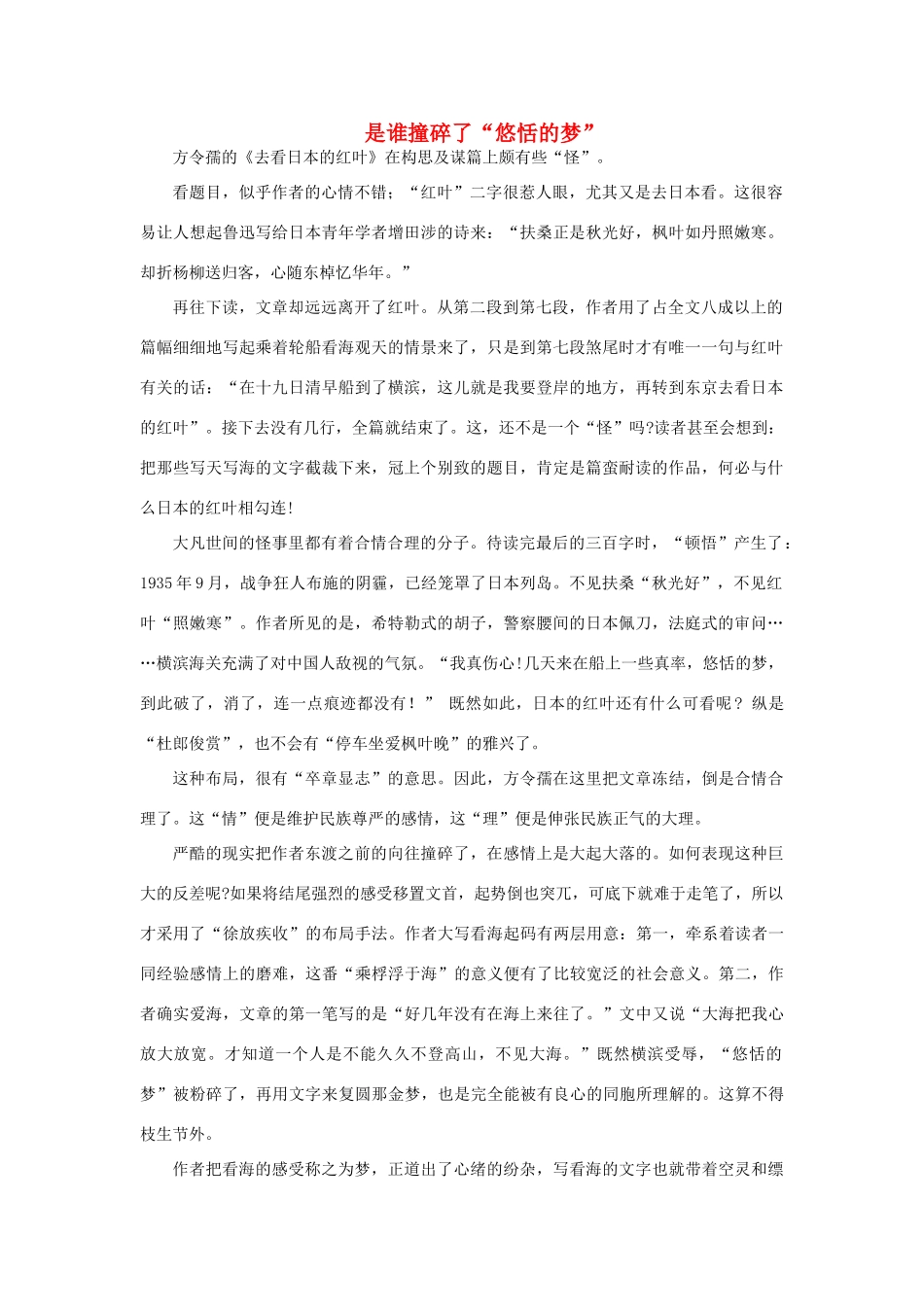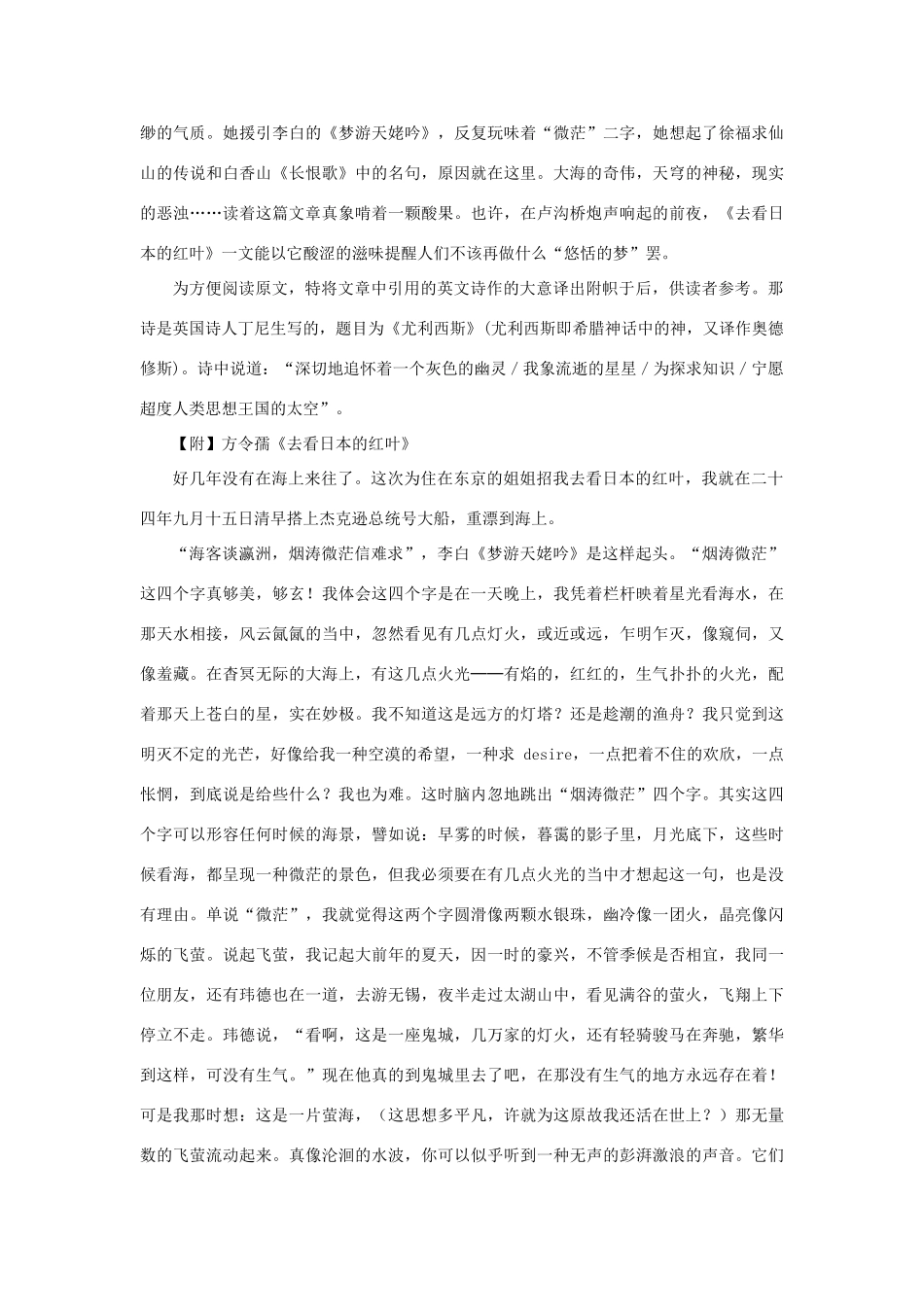是谁撞碎了“悠恬的梦”方令孺的《去看日本的红叶》在构思及谋篇上颇有些“怪”。看题目,似乎作者的心情不错;“红叶”二字很惹人眼,尤其又是去日本看。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写给日本青年学者增田涉的诗来:“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杨柳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再往下读,文章却远远离开了红叶。从第二段到第七段,作者用了占全文八成以上的篇幅细细地写起乘着轮船看海观天的情景来了,只是到第七段煞尾时才有唯一一句与红叶有关的话:“在十九日清早船到了横滨,这儿就是我要登岸的地方,再转到东京去看日本的红叶”。接下去没有几行,全篇就结束了。这,还不是一个“怪”吗?读者甚至会想到:把那些写天写海的文字截裁下来,冠上个别致的题目,肯定是篇蛮耐读的作品,何必与什么日本的红叶相勾连!大凡世间的怪事里都有着合情合理的分子。待读完最后的三百字时,“顿悟”产生了:1935 年 9 月,战争狂人布施的阴霾,已经笼罩了日本列岛。不见扶桑“秋光好”,不见红叶“照嫩寒”。作者所见的是,希特勒式的胡子,警察腰间的日本佩刀,法庭式的审问……横滨海关充满了对中国人敌视的气氛。“我真伤心!几天来在船上一些真率,悠恬的梦,到此破了,消了,连一点痕迹都没有!” 既然如此,日本的红叶还有什么可看呢? 纵是“杜郎俊赏”,也不会有“停车坐爱枫叶晚”的雅兴了。这种布局,很有“卒章显志”的意思。因此,方令孺在这里把文章冻结,倒是合情合理了。这“情”便是维护民族尊严的感情,这“理”便是伸张民族正气的大理。严酷的现实把作者东渡之前的向往撞碎了,在感情上是大起大落的。如何表现这种巨大的反差呢?如果将结尾强烈的感受移置文首,起势倒也突兀,可底下就难于走笔了,所以才采用了“徐放疾收”的布局手法。作者大写看海起码有两层用意:第一,牵系着读者一同经验感情上的磨难,这番“乘桴浮于海”的意义便有了比较宽泛的社会意义。第二,作者确实爱海,文章的第一笔写的是“好几年没有在海上来往了。”文中又说“大海把我心放大放宽。才知道一个人是不能久久不登高山,不见大海。”既然横滨受辱,“悠恬的梦”被粉碎了,再用文字来复圆那金梦,也是完全能被有良心的同胞所理解的。这算不得枝生节外。作者把看海的感受称之为梦,正道出了心绪的纷杂,写看海的文字也就带着空灵和缥缈的气质。她援引李白的《梦游天姥吟》,反复玩味着“微茫”二字,她想起了徐福求仙山的传说和白香山《长恨歌》中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