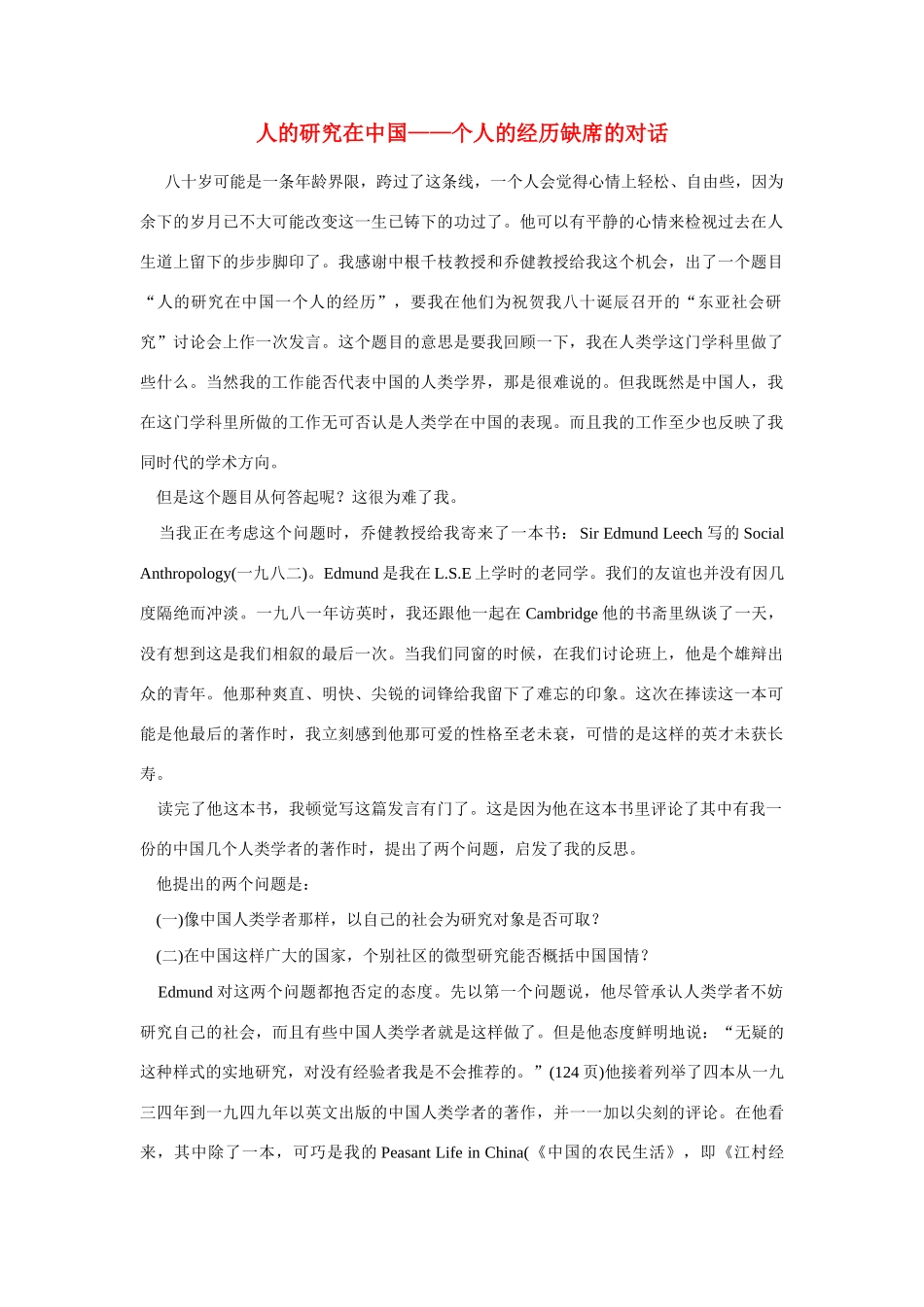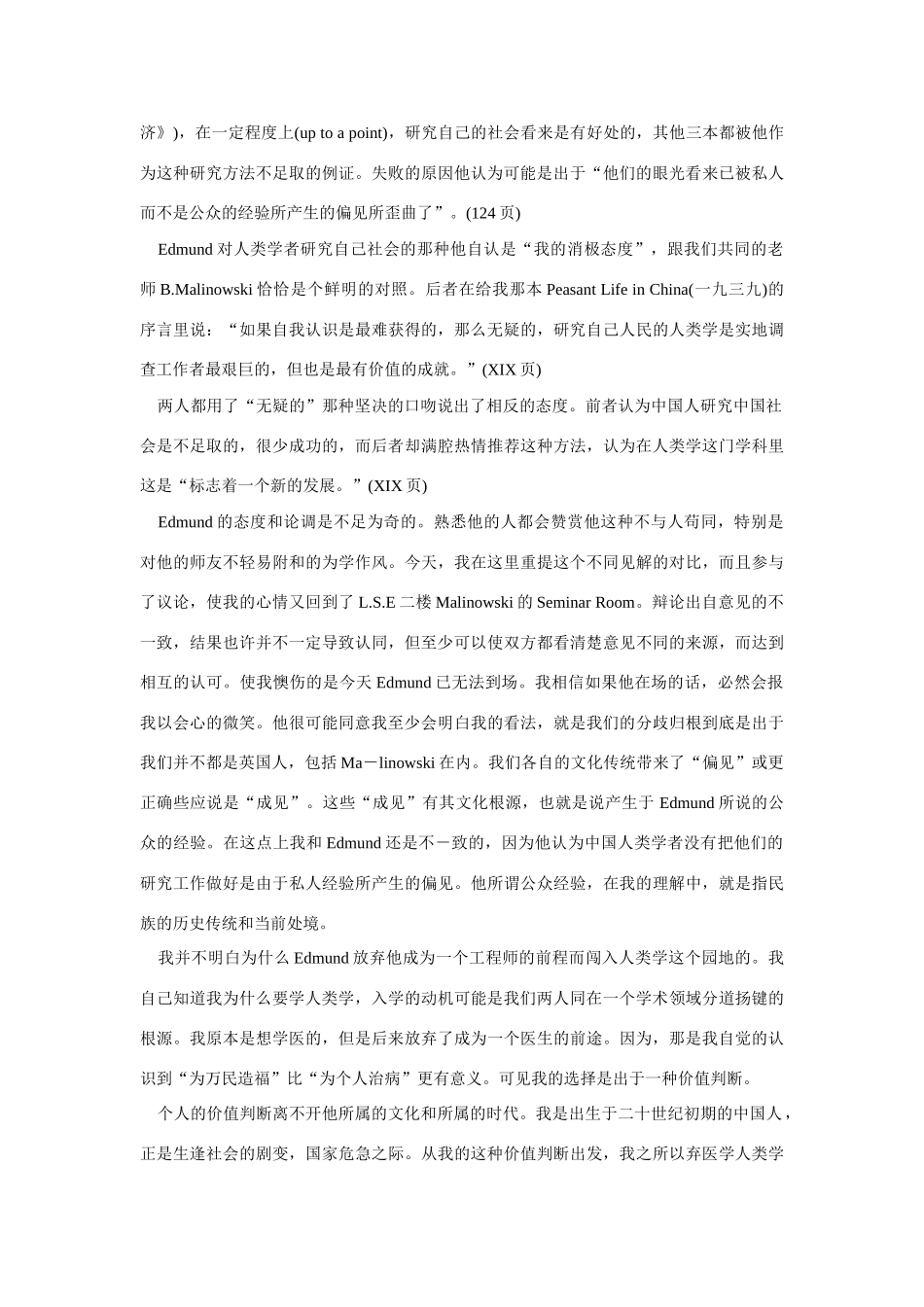人的研究在中国——个人的经历缺席的对话 八十岁可能是一条年龄界限,跨过了这条线,一个人会觉得心情上轻松、自由些,因为余下的岁月已不大可能改变这一生已铸下的功过了。他可以有平静的心情来检视过去在人生道上留下的步步脚印了。我感谢中根千枝教授和乔健教授给我这个机会,出了一个题目“人的研究在中国一个人的经历”,要我在他们为祝贺我八十诞辰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作一次发言。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要我回顾一下,我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做了些什么。当然我的工作能否代表中国的人类学界,那是很难说的。但我既然是中国人,我在这门学科里所做的工作无可否认是人类学在中国的表现。而且我的工作至少也反映了我同时代的学术方向。 但是这个题目从何答起呢?这很为难了我。 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乔健教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 Sir Edmund Leech 写的 Social Anthropology(一九八二)。Edmund 是我在 L.S.E 上学时的老同学。我们的友谊也并没有因几度隔绝而冲淡。一九八一年访英时,我还跟他一起在 Cambridge 他的书斋里纵谈了一天,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相叙的最后一次。当我们同窗的时候,在我们讨论班上,他是个雄辩出众的青年。他那种爽直、明快、尖锐的词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次在捧读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著作时,我立刻感到他那可爱的性格至老未衰,可惜的是这样的英才未获长寿。 读完了他这本书,我顿觉写这篇发言有门了。这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评论了其中有我一份的中国几个人类学者的著作时,提出了两个问题,启发了我的反思。 他提出的两个问题是: (一)像中国人类学者那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 (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 Edmund 对这两个问题都抱否定的态度。先以第一个问题说,他尽管承认人类学者不妨研究自己的社会,而且有些中国人类学者就是这样做了。但是他态度鲜明地说:“无疑的这种样式的实地研究,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124 页)他接着列举了四本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国人类学者的著作,并一一加以尖刻的评论。在他看来,其中除了一本,可巧是我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的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在一定程度上(up to a point),研究自己的社会看来是有好处的,其他三本都被他作为这种研究方法不足取的例证。失败的原因他认为可能是出于“他们的眼光看来已被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经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