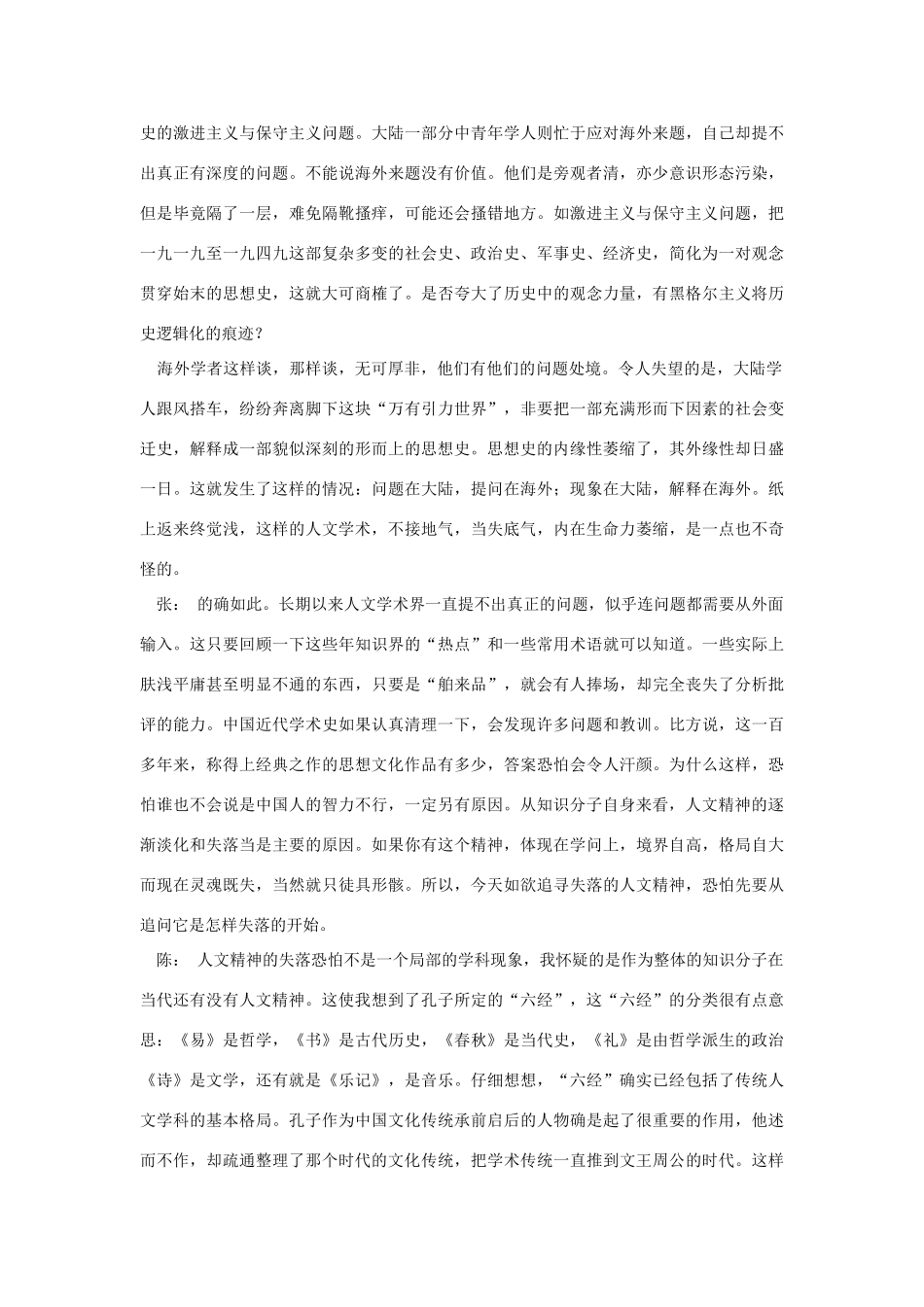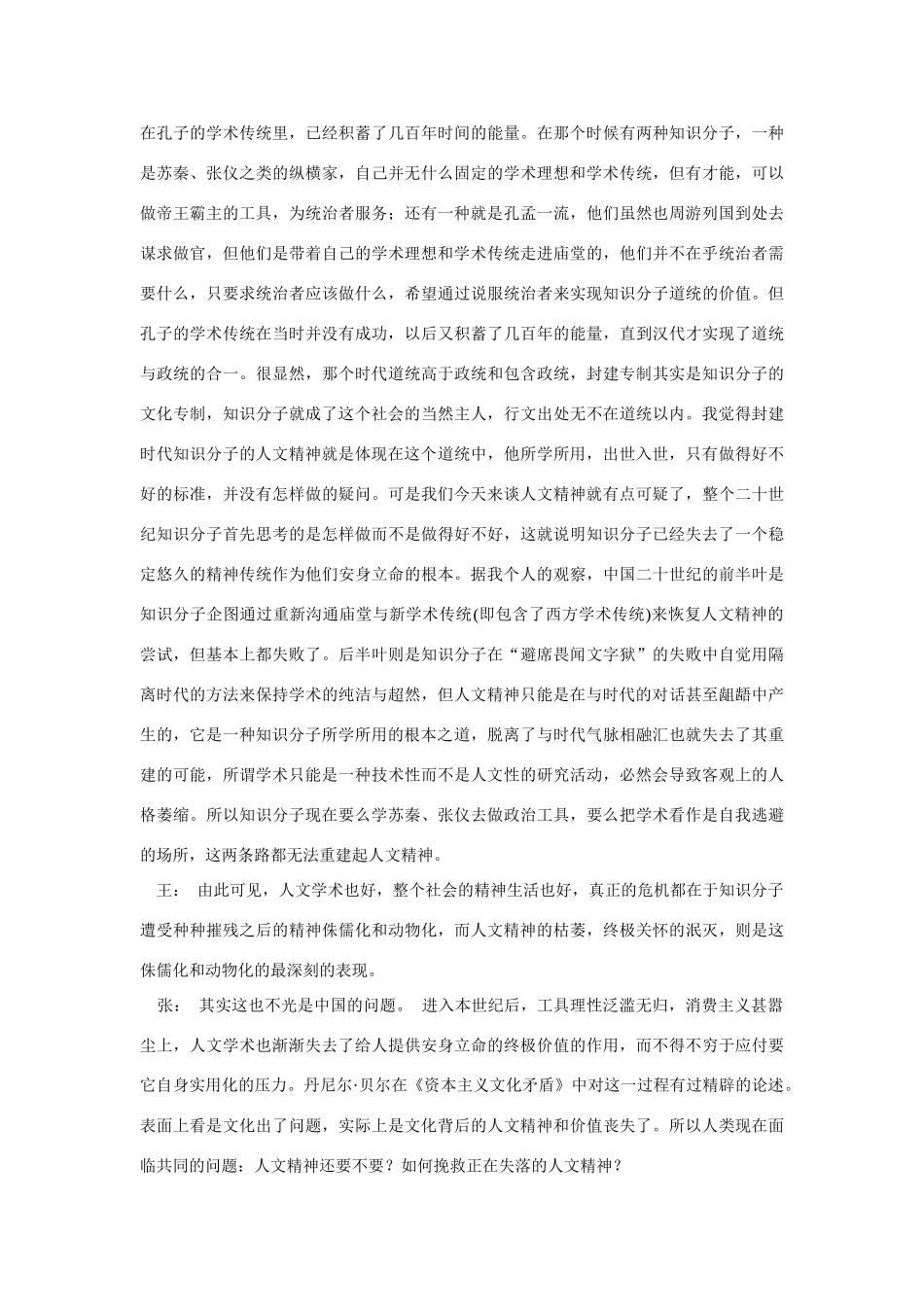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 张: 今天在座的都是从事人文学科教学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文史哲三大学科都有。我们大家都切身体会到,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因素很多。一般大家较多看到的是外在因素:在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但人文学术的危机还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 拿哲学来说,它发展的动力在于怀疑和批判,但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和批判。哲学作为爱智之学追求的是人生的智慧,作为形上之学又必然要有深切的终极关怀这种智慧与终极关怀构成了哲学真理的主要特征和内涵,体现的则是所谓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人文精神是一切人文学术的内在基础和根据。正是由于人文精神意识的逐渐淡薄乃至消失,使得智慧与真理的追求失去了内在的支撑和动力,使得终极关怀远不如现金关怀那么激动人心。 王: 文学批评的现状也是如此。许多人都觉得今天的批评界太沉闷,缺乏生气,我想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批评家丧失了对批评的根本意义的确信。你说批评是政治和社会解放的先声,是思想启蒙的利器吧,今天大家都懂得了,这只是批评的一种效应,而不是它的出发点,更不能构成它存在的充分依据。那么批评是否能够阐发文学的真谛,像自然科学那样求“真”?现在也可以看得清楚,自然科学所求取的那种“真”,在文学世界里并不存在,批评既是一种人文学术,它应该有自己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存在依据。可这依据是什么?如果连这个根本依据都不清楚,批评的激情又从何而来?自然就只好吞吞吐吐,言不及义,或者干脆闭嘴,甚至借批评以营私。 朱: 晓明所说的,是否可归纳为“底气不足”?这可能与“地气不接”有关。这一点,思想史研究领域也有突出表现。 “地气”,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处于一个人文地理环境,能够比局外研究者更真切感受研究对象的脉动流变。大陆学者研究大陆思想史,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即处于“接地气”位置,本来是应该能以自己的语言,提出自己的问题的。遗憾的是,这些年的思想史问题大多是从海外输入,如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五四”的反传统问题、中国现代史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问题。大陆一部分中青年学人则忙于应对海外来题,自己却提不出真正有深度的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