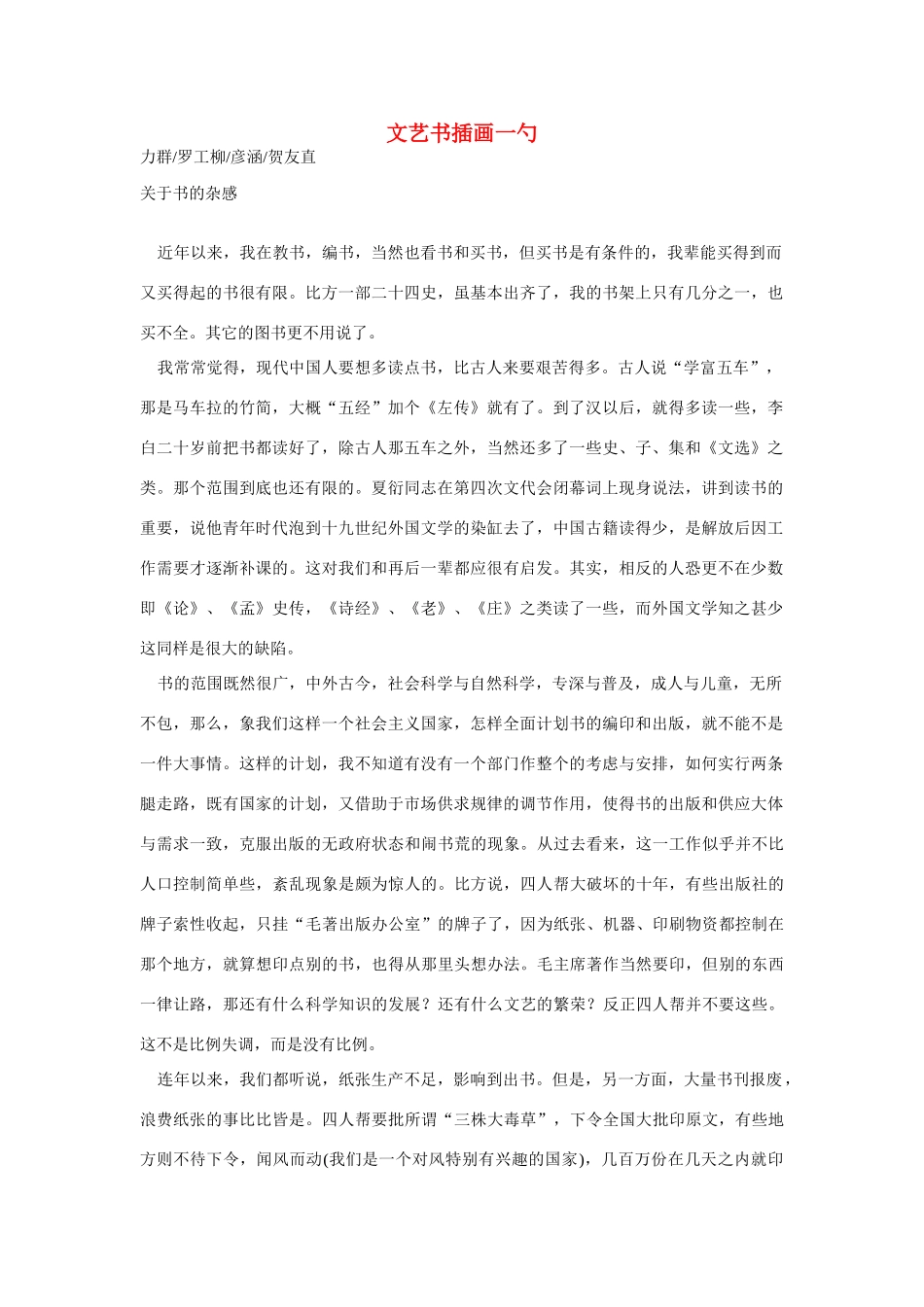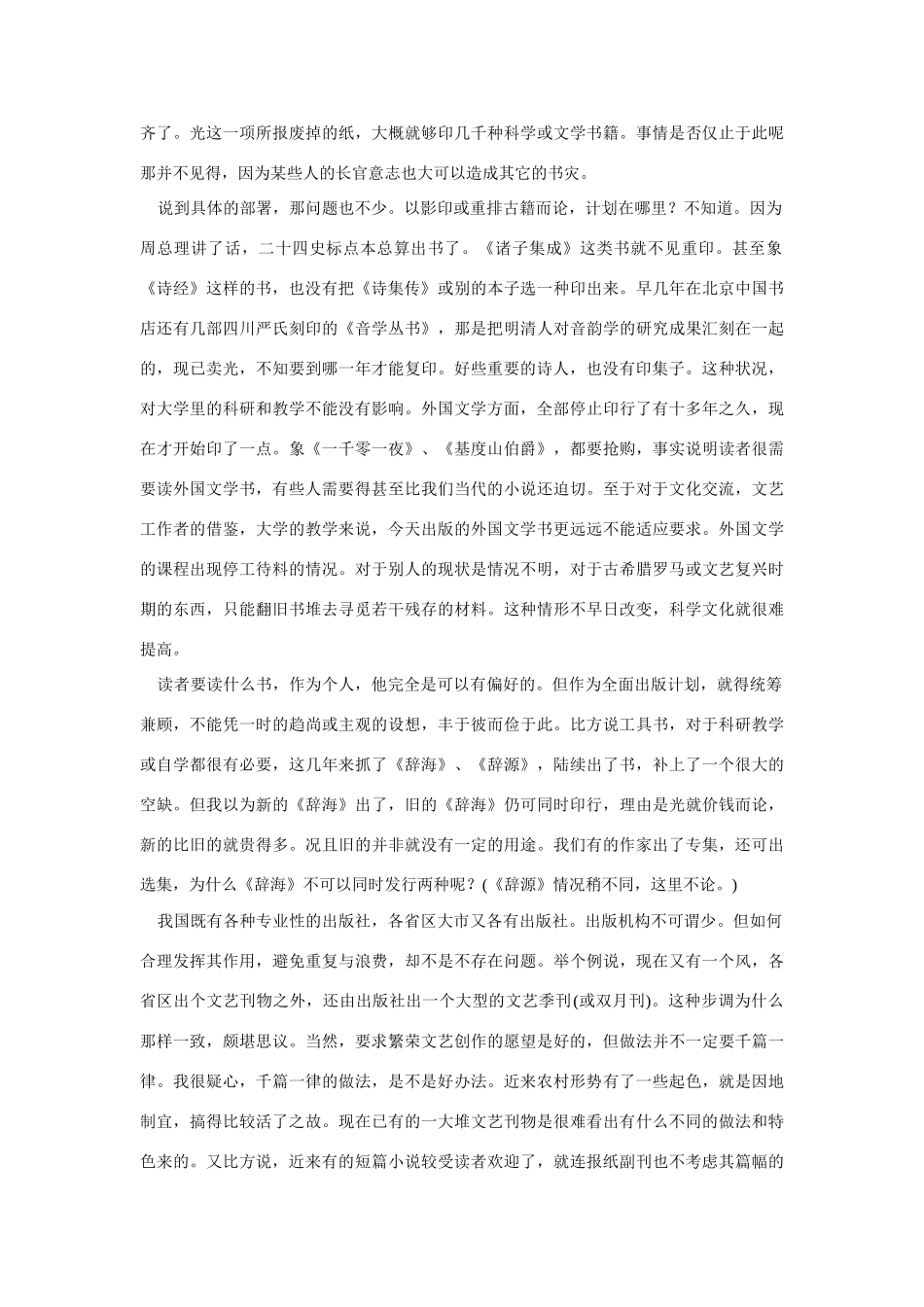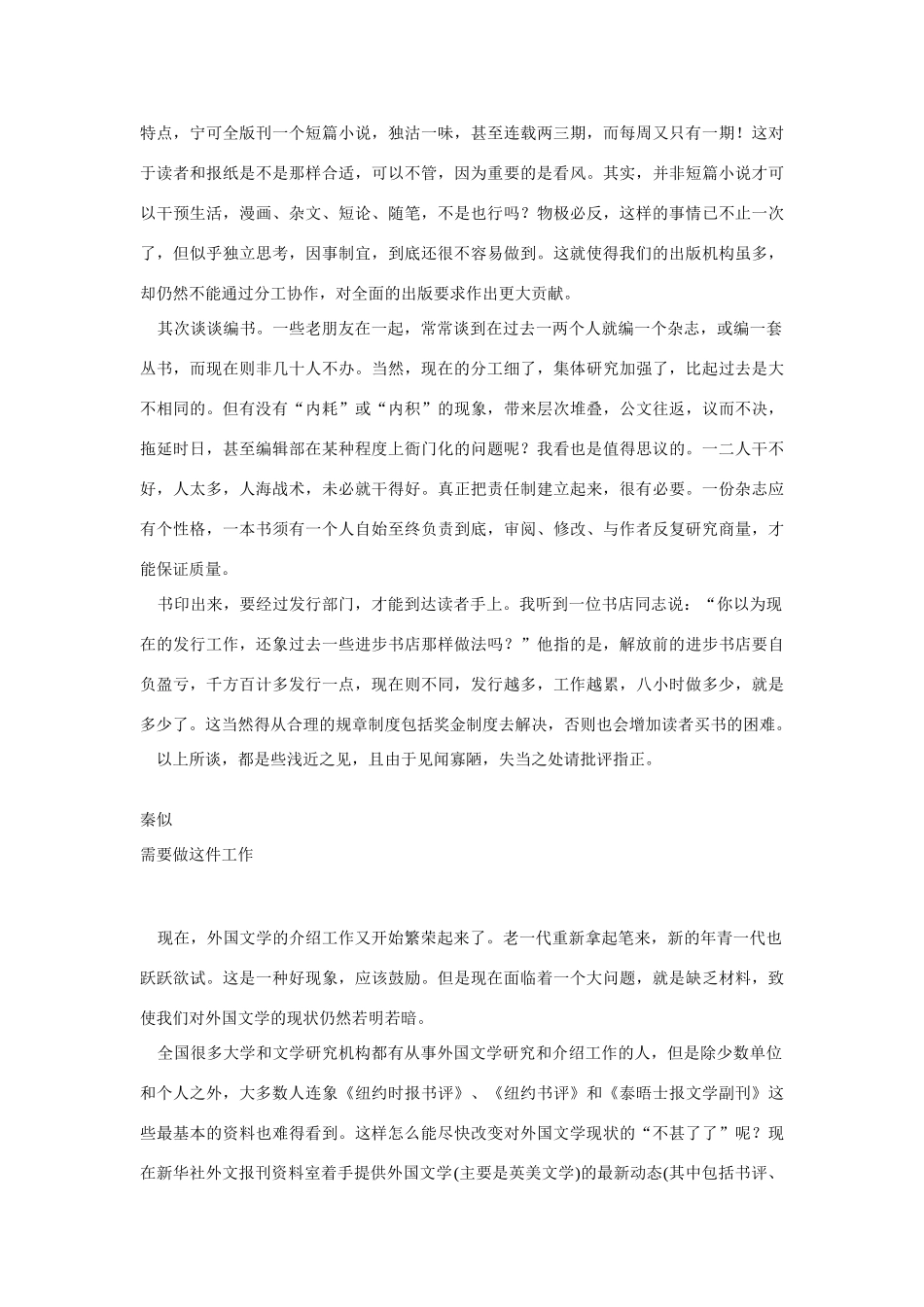文艺书插画一勺力群/罗工柳/彦涵/贺友直关于书的杂感 近年以来,我在教书,编书,当然也看书和买书,但买书是有条件的,我辈能买得到而又买得起的书很有限。比方一部二十四史,虽基本出齐了,我的书架上只有几分之一,也买不全。其它的图书更不用说了。 我常常觉得,现代中国人要想多读点书,比古人来要艰苦得多。古人说“学富五车”,那是马车拉的竹简,大概“五经”加个《左传》就有了。到了汉以后,就得多读一些,李白二十岁前把书都读好了,除古人那五车之外,当然还多了一些史、子、集和《文选》之类。那个范围到底也还有限的。夏衍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词上现身说法,讲到读书的重要,说他青年时代泡到十九世纪外国文学的染缸去了,中国古籍读得少,是解放后因工作需要才逐渐补课的。这对我们和再后一辈都应很有启发。其实,相反的人恐更不在少数即《论》、《孟》史传,《诗经》、《老》、《庄》之类读了一些,而外国文学知之甚少这同样是很大的缺陷。 书的范围既然很广,中外古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专深与普及,成人与儿童,无所不包,那么,象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全面计划书的编印和出版,就不能不是一件大事情。这样的计划,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部门作整个的考虑与安排,如何实行两条腿走路,既有国家的计划,又借助于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作用,使得书的出版和供应大体与需求一致,克服出版的无政府状态和闹书荒的现象。从过去看来,这一工作似乎并不比人口控制简单些,紊乱现象是颇为惊人的。比方说,四人帮大破坏的十年,有些出版社的牌子索性收起,只挂“毛著出版办公室”的牌子了,因为纸张、机器、印刷物资都控制在那个地方,就算想印点别的书,也得从那里头想办法。毛主席著作当然要印,但别的东西一律让路,那还有什么科学知识的发展?还有什么文艺的繁荣?反正四人帮并不要这些。这不是比例失调,而是没有比例。 连年以来,我们都听说,纸张生产不足,影响到出书。但是,另一方面,大量书刊报废,浪费纸张的事比比皆是。四人帮要批所谓“三株大毒草”,下令全国大批印原文,有些地方则不待下令,闻风而动(我们是一个对风特别有兴趣的国家),几百万份在几天之内就印齐了。光这一项所报废掉的纸,大概就够印几千种科学或文学书籍。事情是否仅止于此呢那并不见得,因为某些人的长官意志也大可以造成其它的书灾。 说到具体的部署,那问题也不少。以影印或重排古籍而论,计划在哪里?不知道。因为周总理讲了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