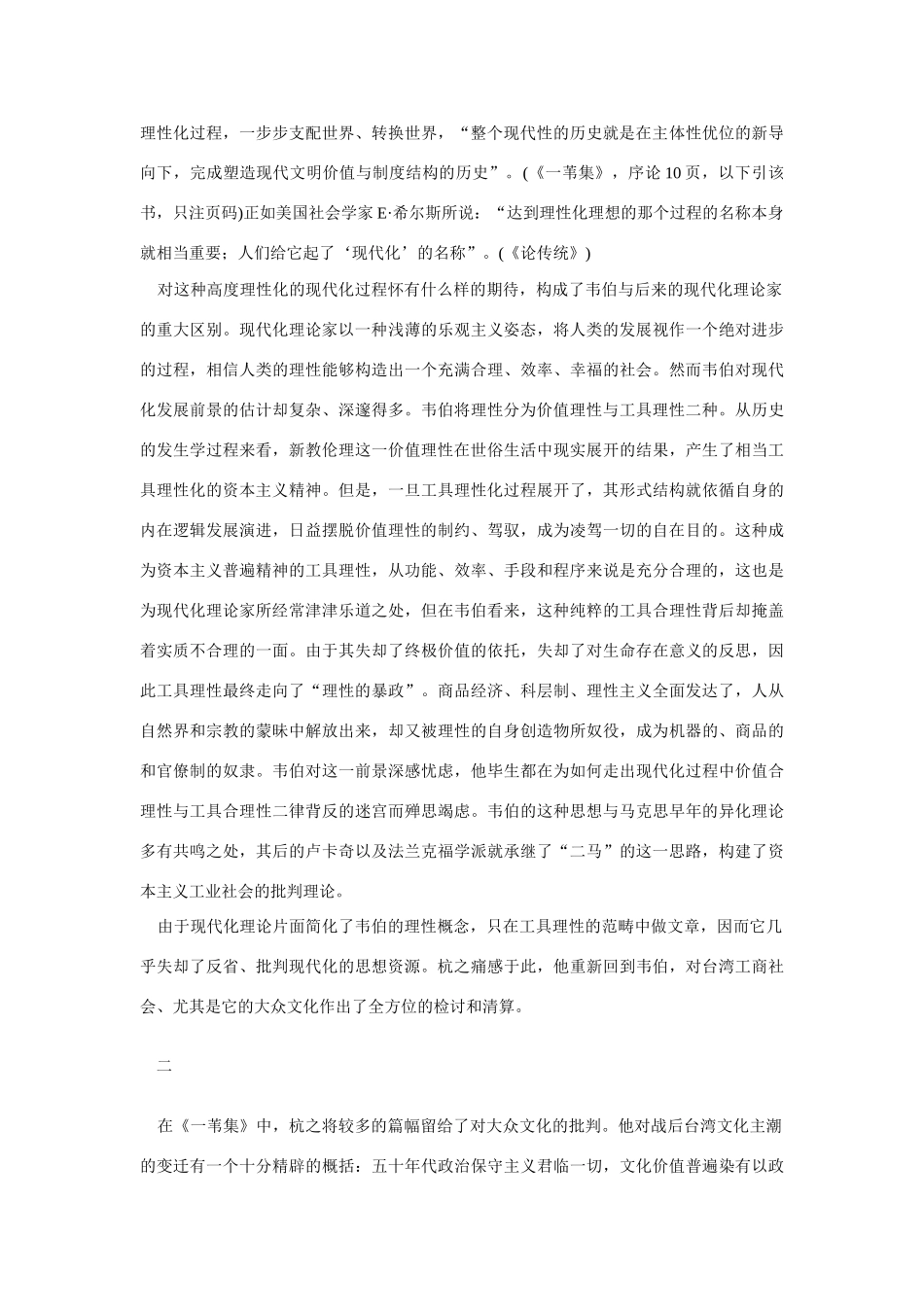现代性的反省 在台湾学者同行之中,我一向比较喜欢杭之的文字。他的社会文化评论,不似有些人写得那般潇洒、飘逸,见灵性,但看得出是下过苦功、苦力、苦思,凭借这些年努力积累的深厚思想资源,慢慢琢磨出来的。因此他的文字要比一般人厚实、深邃,也格外耐读。年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一苇集》,搜集了杭之在八十年代陆陆续续撰写的二十多篇评论乍看上去,内容似乎很散,从学术、教育、文化到公害,无所不谈。通览之后,便会凸现出一个清晰的主题:在现代化四面凯歌的社会中,如何对现代性本身保持冷峻的反省? 一 自欧美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似乎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无可置疑的参照示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崛起的现代化理论,就是试图为不发达地区移植西方经验建构一套目标一行动系统。这一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上,尽管在理论表述上具有结构功能主义的种种“价值中立”的表征,但在其整个分析系统的背后却涵含着明确的价值取向,即将“传统”等同于落后,将“现代”理解为发展这样的二元化思路;将整个世界分为“中心”(欧美)与“边缘”(亚非拉)两个等级,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就是朝着西方世界已经显现的若干“现代性”变量(如城市化、契约化、科层化、理性化、民主化等等)靠拢接近的过程。 杭之在序论中指出,这是帕森斯之流对韦伯思想的最大误读。马克斯·韦伯是最早对现代社会作出深刻、精微分析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现代化理论的主要思想渊源。然而帕森斯这些美国社会学家却将韦伯丰富复杂的思想庸俗化、简单化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现代化真正的思想启动点在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基础,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根据这种革命性的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颠覆与裂变,人不再是世界的一部分或世界的产物,而是成为以自我量度世界、征服世界的独立主体。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也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而只不过是一个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机制。现代人日益从迷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去迷魅”(Die Entzauberungder Welt)。人类可以通过系统的、有目的的、持续的理性化过程,一步步支配世界、转换世界,“整个现代性的历史就是在主体性优位的新导向下,完成塑造现代文明价值与制度结构的历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