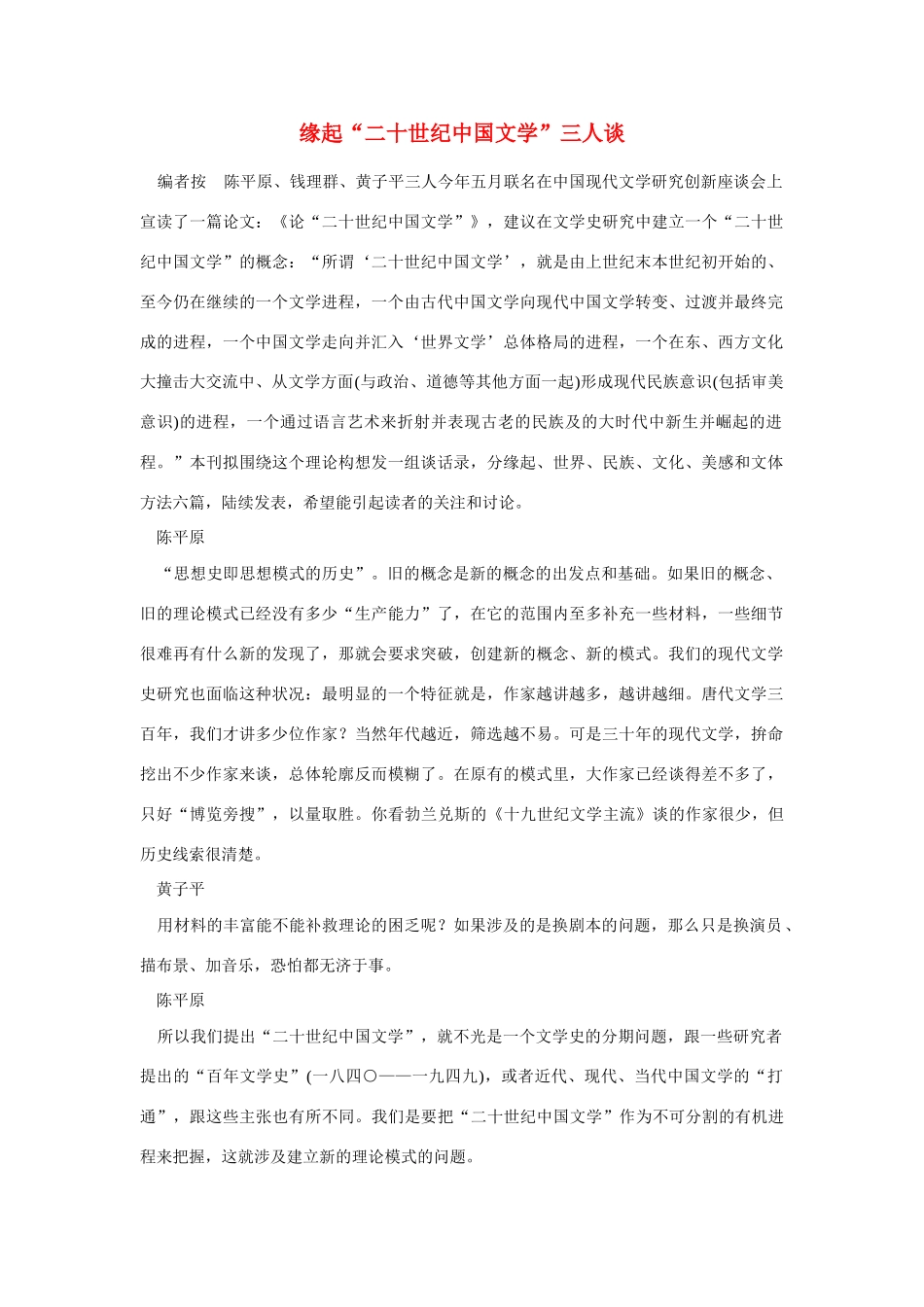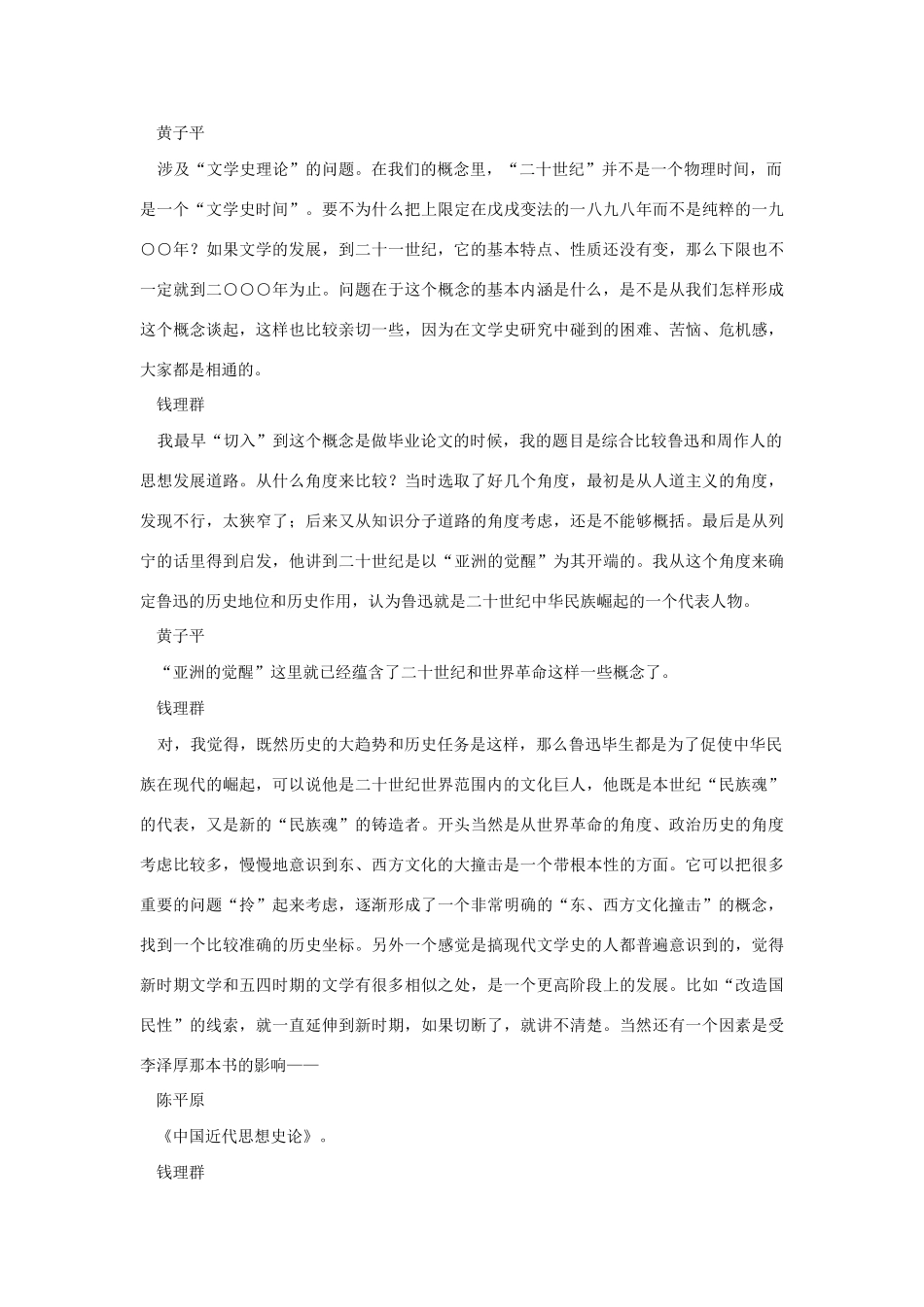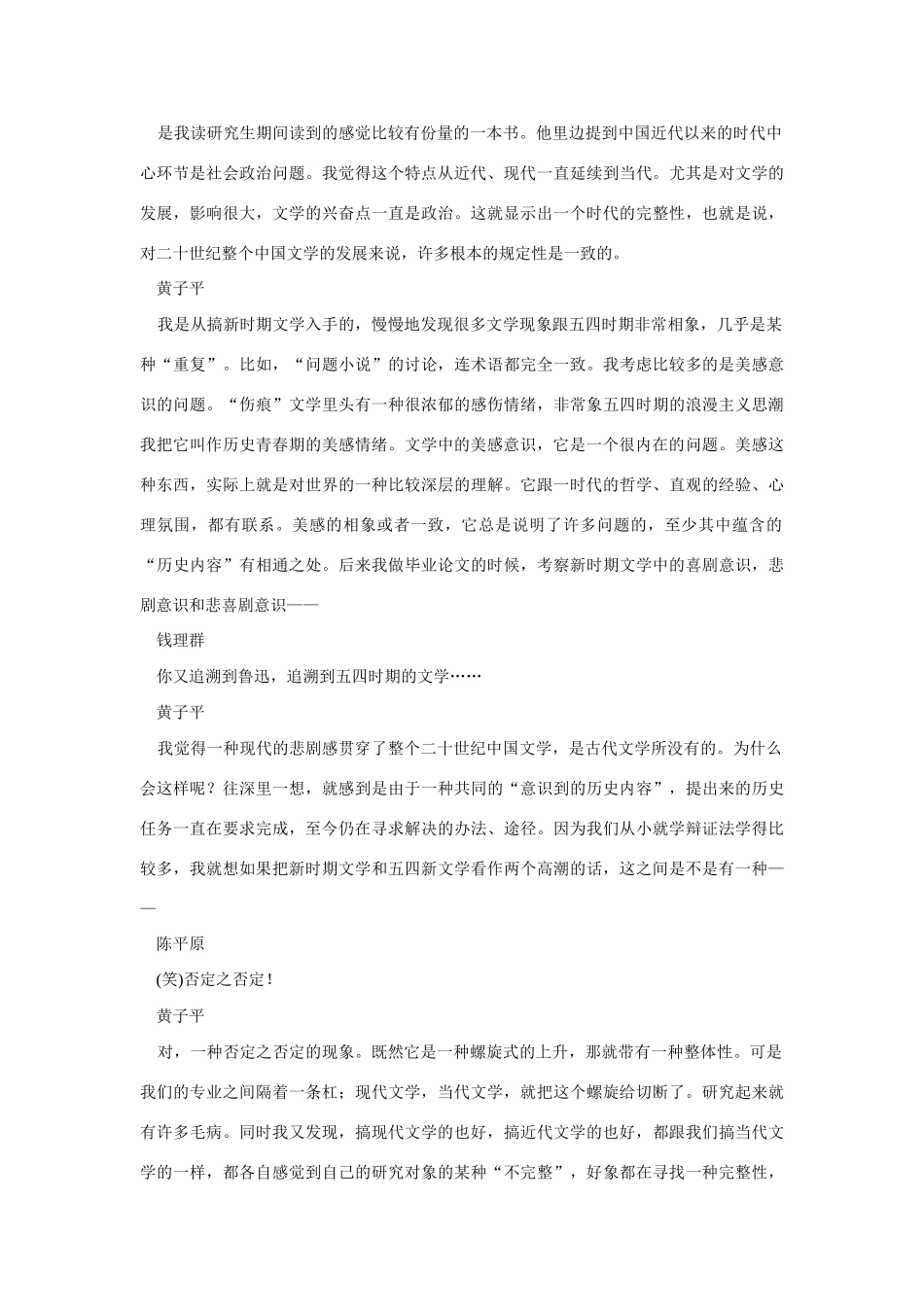缘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编者按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人今年五月联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建议在文学史研究中建立一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本刊拟围绕这个理论构想发一组谈话录,分缘起、世界、民族、文化、美感和文体方法六篇,陆续发表,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陈平原 “思想史即思想模式的历史”。旧的概念是新的概念的出发点和基础。如果旧的概念、旧的理论模式已经没有多少“生产能力”了,在它的范围内至多补充一些材料,一些细节很难再有什么新的发现了,那就会要求突破,创建新的概念、新的模式。我们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也面临这种状况: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作家越讲越多,越讲越细。唐代文学三百年,我们才讲多少位作家?当然年代越近,筛选越不易。可是三十年的现代文学,拚命挖出不少作家来谈,总体轮廓反而模糊了。在原有的模式里,大作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只好“博览旁搜”,以量取胜。你看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谈的作家很少,但历史线索很清楚。 黄子平 用材料的丰富能不能补救理论的困乏呢?如果涉及的是换剧本的问题,那么只是换演员、描布景、加音乐,恐怕都无济于事。 陈平原 所以我们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不光是一个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跟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百年文学史”(一八四○——一九四九),或者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的“打通”,跟这些主张也有所不同。我们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不可分割的有机进程来把握,这就涉及建立新的理论模式的问题。 黄子平 涉及“文学史理论”的问题。在我们的概念里,“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要不为什么把上限定在戊戌变法的一八九八年而不是纯粹的一九○○年?如果文学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它的基本特点、性质还没有变,那么下限也不一定就到二○○○年为止。问题在于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是什么,是不是从我们怎样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