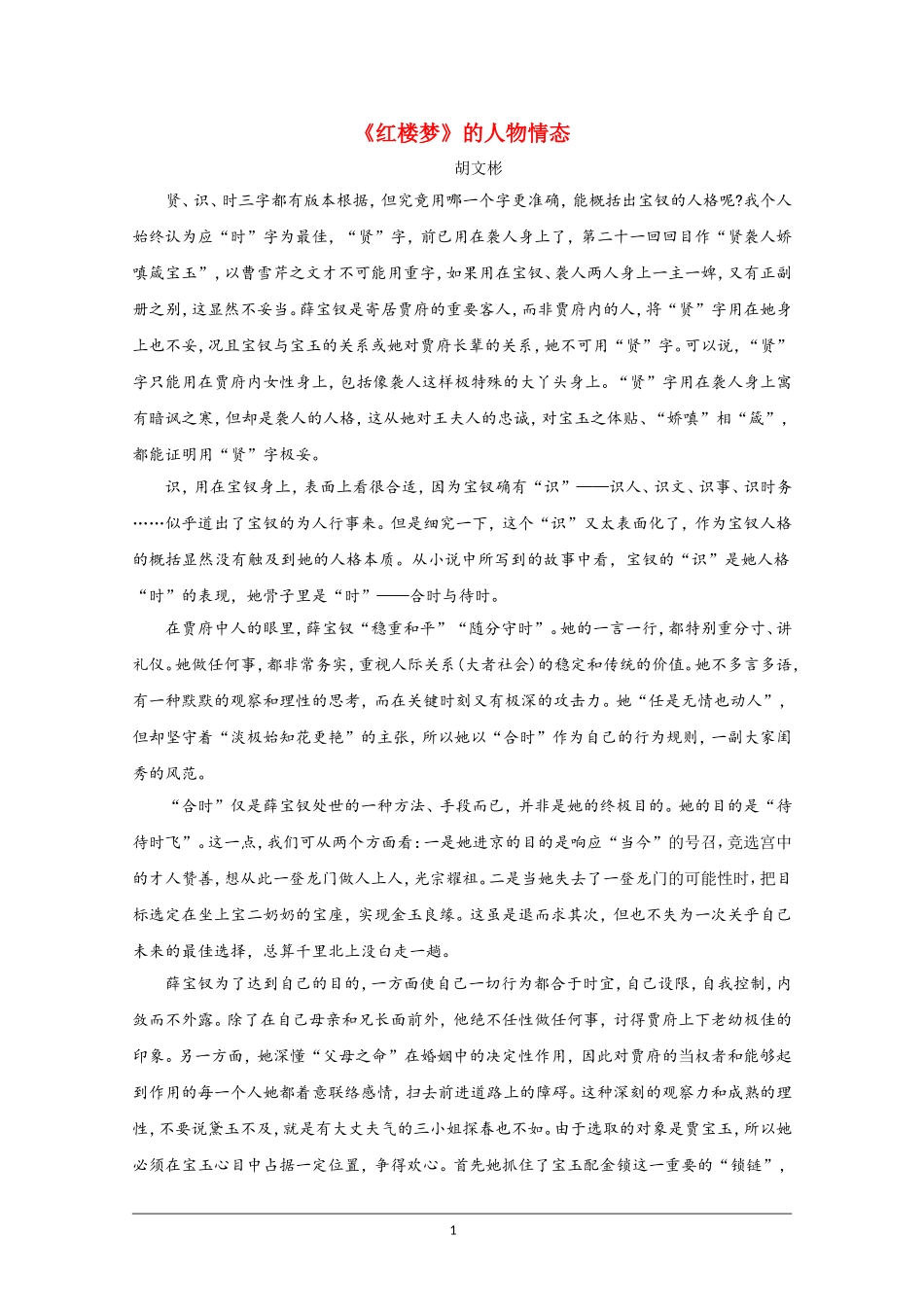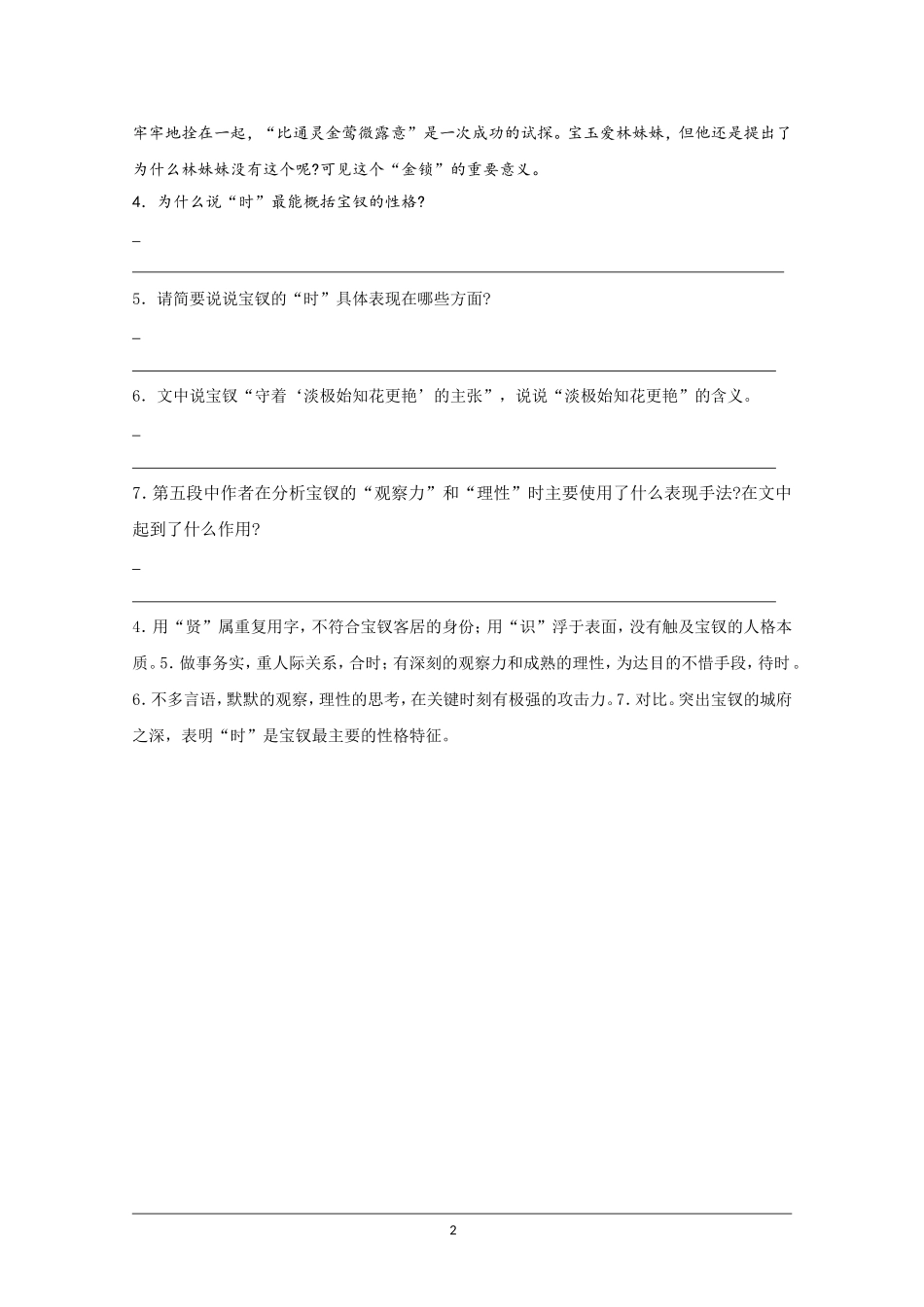《红楼梦》的人物情态胡文彬贤、识、时三字都有版本根据,但究竟用哪一个字更准确,能概括出宝钗的人格呢?我个人始终认为应“时”字为最佳,“贤”字,前已用在袭人身上了,第二十一回回目作“贤袭人娇嗔箴宝玉”,以曹雪芹之文才不可能用重字,如果用在宝钗、袭人两人身上一主一婢,又有正副册之别,这显然不妥当。薛宝钗是寄居贾府的重要客人,而非贾府内的人,将“贤”字用在她身上也不妥,况且宝钗与宝玉的关系或她对贾府长辈的关系,她不可用“贤”字。可以说,“贤”字只能用在贾府内女性身上,包括像袭人这样极特殊的大丫头身上。“贤”字用在袭人身上寓有暗讽之寒,但却是袭人的人格,这从她对王夫人的忠诚,对宝玉之体贴、“娇嗔”相“箴”,都能证明用“贤”字极妥。 识,用在宝钗身上,表面上看很合适,因为宝钗确有“识”——识人、识文、识事、识时务……似乎道出了宝钗的为人行事来。但是细究一下,这个“识”又太表面化了,作为宝钗人格的概括显然没有触及到她的人格本质。从小说中所写到的故事中看,宝钗的“识”是她人格“时”的表现,她骨子里是“时”——合时与待时。 在贾府中人的眼里,薛宝钗“稳重和平”“随分守时”。她的一言一行,都特别重分寸、讲礼仪。她做任何事,都非常务实,重视人际关系(大者社会)的稳定和传统的价值。她不多言多语,有一种默默的观察和理性的思考,而在关键时刻又有极深的攻击力。她“任是无情也动人”,但却坚守着“淡极始知花更艳”的主张,所以她以“合时”作为自己的行为规则,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合时”仅是薛宝钗处世的一种方法、手段而已,并非是她的终极目的。她的目的是“待待时飞”。这一点,我们可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她进京的目的是响应“当今”的号召,竞选宫中的才人赞善,想从此一登龙门做人上人,光宗耀祖。二是当她失去了一登龙门的可能性时,把目标选定在坐上宝二奶奶的宝座,实现金玉良缘。这虽是退而求其次,但也不失为一次关乎自己未来的最佳选择,总算千里北上没白走一趟。薛宝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使自己一切行为都合于时宜,自己设限,自我控制,内敛而不外露。除了在自己母亲和兄长面前外,他绝不任性做任何事,讨得贾府上下老幼极佳的印象。另一方面,她深懂“父母之命”在婚姻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对贾府的当权者和能够起到作用的每一个人她都着意联络感情,扫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种深刻的观察力和成熟的理性,不要说黛玉不及,就是有大丈夫气的三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