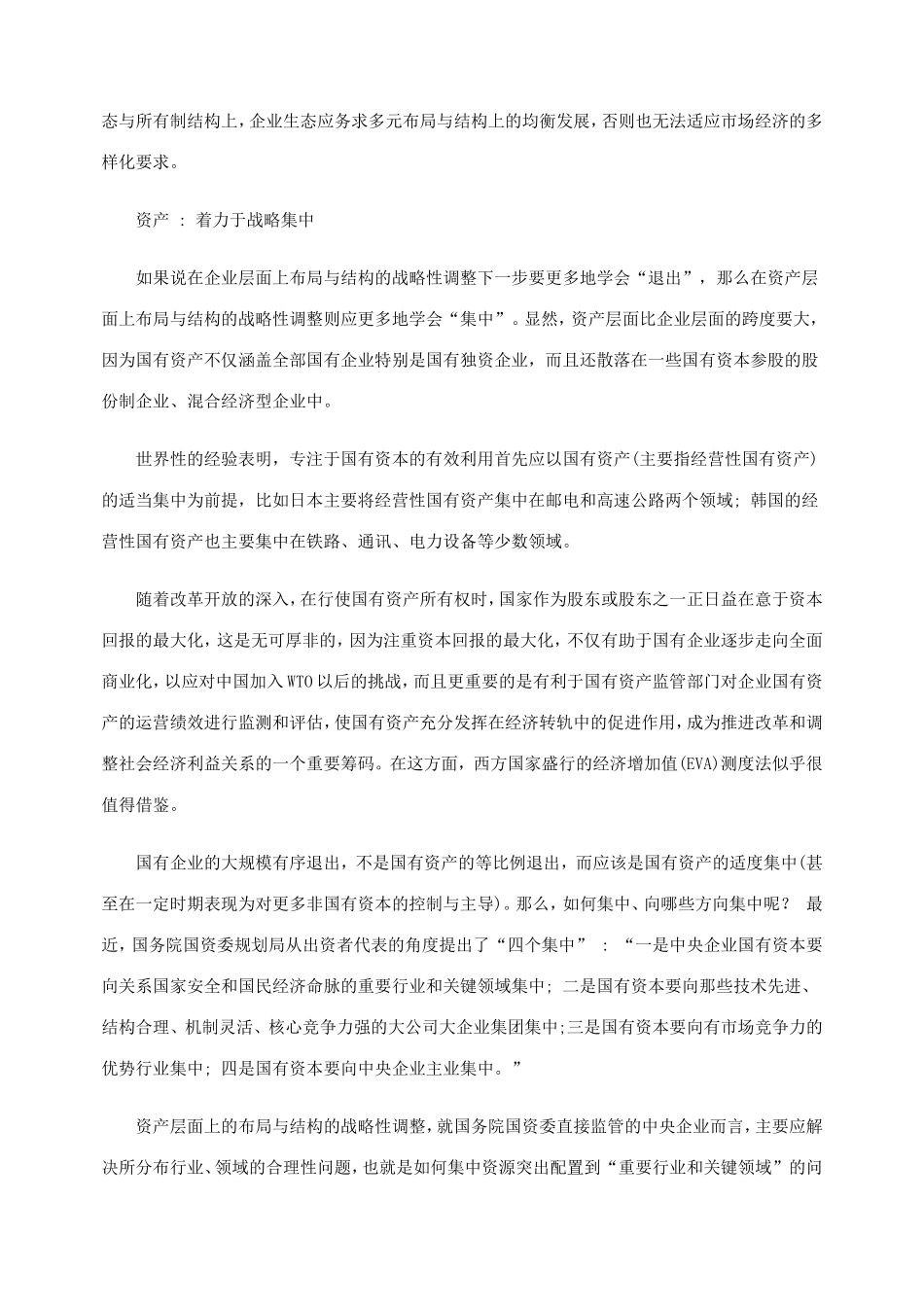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三大战略性调整2005年03月25日17:36上海国资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文从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看,如果说企业层面上要更多地学会“退出”,那么在资产层面上则应更多地学会“集中”,而明显处于最高级的经济层面,则更具有前瞻性和开放性党的十六大特别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企改革面对来自外部与内部、横向与纵向的多方面压力,出现了实质性的转折——转入到一个更加艰难但又更加逼近全胜终局的攻坚阶段,它的运行脉络越来越清晰:一是在宏观范畴内继续强力推进以存量为主的布局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二是在微观主体上稳健而又积极地加快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创新。由于宏观范畴的战略性调整同样也不可能脱离企业微观主体的市场进退变化以及资产消长变化等,因此,从布局与结构的角度来看,所谓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事实上已在而且必将进一步从企业、资产与经济这三个相关层面着力展开,并抵达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直至全面实现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企业:着力于多元构建据有关资料,截至2004年8月底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已由1998年的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按照党的十六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实现战略性调整,反映在企业层面的布局与结构上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需要由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应区别不同情况实行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这类企业的数量规模必须控制在“关键的少数”,并主要集中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二是大量的一般竞争性行业和领域里的国有企业,要“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在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也就是说,经过战略性调整,现有国有企业乃至整个企业层面的布局与结构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直观的脉络就是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将通过破产、关闭或解散特别是改制转型等途径有序退出,变成股份制企业、混合经济型企业等,从而使国有企业在总量规模上大幅度缩减。而数量空间的压缩,有助于留下“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更好地谋定自己的价值空间,即集中发挥为其它非国有企业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使相互间在总体布局安排上的角色分工更趋清晰、更具有战略意义;同时,也能让更多的非国有企业在非“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里加快成长,以增强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活力。据世界银行有关研究,举凡世界上最成功的国有企业治理体制,均为国企数量或所监管国企数量相对较少的体制(因为政府控制的企业越多,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就越低),比如新西兰仅监管16家国企、瑞典59家、新加坡约20家。它们都对国有企业实行较小的“控制跨度”,便利了国有企业的良好治理。预计若干年后,我国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约将减少到数千家这样一个总量规模,而各种类型的非国有企业则会更多地应运而生。战略性调整作用于企业层面上的布局与结构变化,生动地表明国企改革是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的一项系统性很强的根本变革,也是进一步解放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企业生产力而事关国家与社会进步的一场革命。它事实上支撑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宏观格局的基本形成。经过在企业层面的布局与结构上的战略性调整,我国企业的组织形态、所有制结构等均将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体制,进一步形成多元化的有序格局,其中尤其要以股份制企业、混合经济型企业为主体。而对国有企业而言,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要继续以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为方向,加快有序退出,不仅对那些资不抵债、扭亏无望、无市场前景、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要依法破产、关闭或解散,实行“自然退出”,而且即使是目前盈利表现尚好的国有企业,也要分门别类,区别轻重缓急,从国民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以产权重组作为突破口,使其中相当一部分实行“战略退出”。无论是官方论述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是非官方流传的“国退民进”、“中央退地方进”,尽管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或重大差异,然而一个基本的共识倾向似乎也已形成,即认定学会“退出”也是一种发展、学会多元构建也是一种发展。在企业组织形态与所有制结构上,企业生态应务求多元布局与结构上...